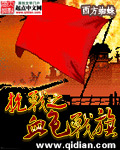性情张抗抗-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六部分:无序六题悼 词
J参加过无数追悼会。他在文化局某处当了十几年的老科员,由于他本人也不清楚的原因,至今还是个副科级。像筹办遗体告别仪式这类的事,不免时常落到他的头上。
好在他十几年前就从一本红皮书中了解到诸如“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从来就对生老病死抱着一种达观的态度。况且,追悼会其实也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悲切凄凉。当人们站在殡仪馆外的院子里等候向遗体告别时,照例聚集成堆谈笑风生,谈的什么,反正死者是听不见了;灵堂里同一只花圈的纸花瓣上,扎满了各种各样为不幸故去的人敬献挽联留下的互不相干又重重叠叠的针眼,还有小白花与黑纱,也都是本着节约的原则用了一次又一次,反正死者都是看不见的。这一切都似乎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配上电子音乐,有一点类似黑色幽默的效果。J在为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艺人溘然谢世、积劳成疾的中年艺术家早夭,还有车祸空难等意外事故操办的丧事中,从未感觉到前来吊唁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哀悼与惋惜。一切都如同空荡荡的灵堂冰冷而僵硬,那时他总暗暗在心底嘘出一口长气:唉,中国人太多啦……
不过,渐渐地J竟然从一系列追悼会的经验里发现了其中一项相当具有人情味和富有诗意的东西,那就是悼词。
虽然严格说起来,那些活着的人给予亡灵的悼词显得有些雷同、有些千篇一律,但同他们在尘世所受到的指责申斥审查以及各种流言蜚语比较,这一份实际已同他本人绝对无关的悼词,却显得那么宽容大度,那么温和体谅,那么公正公平,甚至还有点儿一半赠送一半发放的过誉的赞美与违心的吹捧……
J发现了这一点,初时兴奋,继而却迷茫困惑。他觉得悼词中对死者的评价与死者生前所受到的对待实在有太大的差距。老话说“盖棺定论”,看来应以悼词的结论为准。既然如此,此人生前定是受了天大的冤屈;悼词大概兼有替人正名的功能?可既然此人一死便人人称道,为何在他生前却不能得到承认?待到他满怀一腔遗憾离去,人们立即在他身后焚化一大堆纸扎的桂冠,那桂冠岂不是太廉价太虚伪了?
J思来想去,竟勾出更多的疑虑来:如果说一个生前被非议、被误解的人、死后尚能从悼词中获取对他已无意义的安慰,多少还体现了某种人间的正义与良知,可那些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吮吸民膏专横跋扈的家伙,生前明明遭百姓咒骂痛恨,死后的悼词却是一片歌功颂德,满篇誉美之词,悼词难道是只过滤器么?
J想得头脑昏沉,心灰意懒,莫非悼词只是写给活人看的?暗示每个人将来都能恰如其分地得到肯定?或者说悼词起草者的潜意识中是否包含这样的因素?主啊,宽恕他吧,他既已不再存在,便不再有碍于我……
想到这里,J的心里略略悟到了什么,有几分通畅起来,那份思绪连结到自己,不知哪里阵阵地有些酸楚。十几年来,他可谓是全局最忙最累的人,秋天去弄菜,过节去弄肉,春天搞基建,夏天办旅游……别人什么事儿办不成什么事儿来找他。一年有三百六十天不能同家人一起吃晚饭。可他的事办得最多,人们对他的意见也最多;干十件事有九件事受到批评,比如说他提议办一所探索影剧院,专门上演上映一些实验性影剧,结果遭到了强烈反对;他把一个前几年因受排济而调走,在外地出了名的演员设法调回来,又使所有的次名演员炉火中烧,诬告他藏有私情……混到现在,连个科长也没混上。
他觉得有些伤心伤神,呆坐良久,忽然看见桌上有一份“个人年终总结”,他沉思片刻,提笑在上头写了大大的两个词:悼词。
J某人为人正直品行端正人格高尚任劳任怨精明强干人才难得将其一生献之于改革大业成绩斐然贡献卓著为我民族之精华国家之精英殊追认为名誉科长呜呼哀哉尚飨!
不幸几日后,J在公干时受了重伤,送至医院抢救,多日人事不省。眼看危在旦夕,局里决定为他安排后事,却不料他奇迹般地死去又活来,无意中发现局里为他所准备的那份悼词,意与他本人日前所拟的一模一样,他不禁哑然失笑,病愈后一如既往,又开始张罗某人遗体走后门提前火化的事儿了。
第七部分:流行病有关肝的疾病
我们到达F城之后。事情才真相大白:F城时下确实正流行一种有关肝的疾病。
C君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她死死捂住肝区,止不住一阵恶心。背包撂在自己鞋面上,差点儿连眼神都没地方落。
她有洁癖。略略听人说起过。
据说到昨天为止,已达到多少万人了;全城的医院都住满了;病床都开上下层了;据说全城所有的公共汽车扶手、餐馆的桌椅板凳、电影院的空气,还有自来水管、煤气管道、电线或是下水道里,都密密麻麻布满了那专门同人的宝贝肝儿过不去的病毒了。以至于路上每一个迎面走过去的人,头发丝和呼吸里,都可能携带着这要命的东西了。F城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被污染了。
C君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城市。她从下车到现在滴水不沾。
我倒认为未必这样。起码F城在这之前,从来都是不同凡响的。这种不同凡响难以用语言建构。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声音、一种气氛、一种温度与湿度、时间与空间的总和。F城在我眼里永远那么精明那么细巧、那么敏感那么实惠、还那么艳俗那么时髦。F城的街道永远熙攘拥挤,迫不及待争分夺秒地流行的时尚,无论是流行时装流行发式流行家具流行首饰流行歌曲还是流行霹雳舞太空舞流行妻子加情人,在此都是应有尽有,无一遗漏。像F城那条流去又流来的护城河水,把所有的流行色都脏兮兮地搅拌到一起……
如果再加上现在这个流行性肝炎。它就十分完美了,我暗暗想。我对F城的好感竟由此有所增加。事实上,F城在这一片心怀叵测的非议与流言之下,倒显得格外轻松自在。街道依然拥挤不堪,商店依然生意兴隆,餐馆依然杯盘狼藉,行人依然风流倜傥……我拨了整整一天的电话寻找我的熟人,发现他们个个依然健在。没有什么可以表明甲肝同这个城市的关系,没有什么迹象,至少我看不出它在哪里。我甚至觉得F城比以往更显得精力旺盛,更汹涌澎湃。
何况,甲肝甲肝,听起来就像是最好的肝似的,容易使人想起甲鱼。
“你们真是一点儿没听说流行……”
“听说是听说一点,没人相信,你晓得新闻的透明度……”
“我说的是流行粗的金项链……”
“我们是出来组稿的,等米下锅,没办法,现在流行武侠小 说……”
“我不看书。我是问你,你刚过了年就跑出来,手里一定有货。”
“货?”
“不要客气,尽管直说,汽车钢材、木料还是水泥,我都要。你有多少我要多少。板兰根也行,一包换一包‘良友’……”
“我不是……”
“不是?不是你有介大的胆子,这种辰光跑到F城来?你讲价好了,成交一吨多少信息费……”
第七部分:流行病无处不在的恶魔
她根本买不到近日内回E城的票。她从车站灰溜溜回米,说那儿挤得有点像20年前知青下乡的时候。她后悔到F城来。她说整个F城看上去像—盒发了霉的饼干,长满了暗绿的苔毛。她前不久刚学过一点气功,说能测出城市上空的晦气。她毫不犹豫从街上买回一只电热杯,消毒杯子带消毒房间烧干了十三杯水烧得天下皆白。自从在F城搁浅以后她餐餐用电热杯煮面条煮面包煮苹果,不煮得稀巴烂决不进口;她只在楼下大厅上买这些东西。还买回三双尼龙手套和一瓶洗涤灵。她几乎终日戴着手套。只要一旦摸过除了她自己嘴以外的地方,她就把手套脱下来泡在卫生间的水池里。有一天她在洗手套时惊呼,说毛蚶只是替罪羊,一定是水源有了问题。兴许核电站溢漏造成核辐射或是由爱滋病毒诱发……她的嘴唇不安地哆嗦,命令我睁大眼睛观察那汩汩而流、看上去清洁透明而实际上充斥杀机的水。她说她早就认为这个世界布满危险,早就预言这个世界再没有一处安全岛。现在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个确凿的证明而已。
从那会儿开始,她的电热杯终日电流水流不断。她信不过宾馆热水瓶里的开水。她用自己的电热杯烧的水洗头洗衣洗澡洗脚。她警告我必须用凉开水刷牙,否则只要有一滴生水的亿万分之一的那么一个病毒进入我的咽喉,我就会完蛋。我不得不服从,险些没把大牙烫掉几回。那些日子她就躲在宾馆里闭门不出,从早到晚烧开水。反正她从来就对一切流行的东西深恶痛绝。组稿约稿的事一古脑推到了我头上。而当我精疲力尽地回到宾馆时,她那警惕而审视的目光,总使我怀疑她是否想把我也放在电热杯里煮一煮。
“给你多少出差费?”
“同平常一样。”
“呆!这种辰光出来,补助费应当加三倍。回去向你们领导要保健津贴。没好处的事情,现在啥人肯做?”
“哎呀呀,你怎么还穿这种大脚管裤子?老早不时兴了。”
“我晓得,我不喜欢同别人穿一样的。我人长,穿细的不大好看。”
“好看?时兴就好看!你看,我家的壁纸刚叫人来重做过,画线都拆掉了。现在时兴贴到顶,同宾馆—样。顶时兴的是做护墙板,吊灯的顶灯也不时兴了,要做到天花板里去,只见光不见灯……说句实在话,你回去介绍朋友做这个生意。保证赚一笔……”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的羔羊……”
一路都是这首歌。
满城都是。
我回到宾馆房间时,C君正对着镜子翻看自己的眼白。她说她这几天尿有点发黄。我回答说莫非以前的尿是绿的?她把眼皮放下,揉了揉,一抬眼,看见了我买回的几只粽子和一盒奶油蛋糕,她如见了一枚定时炸弹似的尖叫起来,叫我把它们扔出去。我说我吃腻了电热杯,这么吃下去我活不出F城去。粽子包着那么厚的壳,那肝炎还会像孙悟空一样钻进去不成?蛋糕是国营大食品公司里出的,即使有肝炎菌,烘也烘熟了不是?她拼命摇头结结巴巴指着蛋糕上的奶油花说。那说不定浇奶油的工人手上带菌呢,还有盒子、还有……我说那怎么就偏让你摊上?
你学过概率学没有?她说反正你得扔了去,不扔就别想进这个门儿。我说那我一个人吃还不行呀?我的肝儿馋得受不了了。她沉下脸说,你一个人吃也不行。我们同住一室,你吃了,就可能污染我,你得讲点儿公德。我回E城还得约会呢。说着就趁我不备把东西扔到了走廊里。
“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
那盒蛋糕像一轮灿灿的满月,跌落迸裂在猩红色地毯上,银白色的光泽洒射开去,散发出清肠润肺的芳香。眼前一片如玉如脂的雪地。我蹲下来,忍不住用手指去抠那白色的琼浆,然后放进嘴里慢慢吮吸。我不相信这样纯净的东西会有什么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