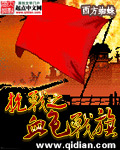性情张抗抗-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我暗哑着嗓子,一副低声下气的可怜相,“我把那只半导体卖给你吧,虽说是自己装的……”
远远传来了收工的钟声,“狮子头”的耳朵真比猎犬还灵。他麻利地戴上簇新却很脏的棉帽,套上黄大衣,就拽我往窖口跑。
“今晚食堂吃包子,快!”他三脚两步登上了梯子。
“你无论如何得想想办法……”我紧跟在他身后,忽然他鞋底掉下的一粒沙子迷了我的眼睛,疼得我眼泪也涌出来了,我只得停下。
这时,有人轻轻拍我的肩膀,接着,一双冷冰冰的手伸到我的脸颊上,很快翻开我的眼皮。那双手上有一股新鲜的白菜气息,好像是一片柔软的菜叶代替了手绢,沙子抹去了,眼睛不疼了。
我睁开眼睛,透过模糊的泪水,看见我面前站着他——那个老头。他依然弯着腰,眼睛瞅着地下,好像他的腰从来不曾伸直过。我上了梯子,没有说谢谢。
“唔……唔……”他忽然发出了一种什么声音,古怪的,显然隐藏着一种焦虑,又不敢大声。
我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斜着眼瞧我。
天哪,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好像一口深深地陷在沙漠中的枯井,干涩而荒寂。混浊的眼珠,像一潭枯井中的死水,这会儿却忽然闪出几丝善良、温和的光波。
我诧异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伸手到那油腻腻的衣襟里去掏着什么,一边呐呐地说:
“不要卖、卖半导体,留着听个歌儿,解解闷……你要钱,我,我借你……”他呐呐地说。
我愣住了,我为这突然降临的运气庆幸,表妹得救了!
他战战兢兢地把钱递过来,厚厚的一迭,是一块钱一张的,破旧而又肮脏,攥在他鸡爪似的手心里。
我刚要伸手去接。突然冷静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猛然大声喊道。那声音之严厉连自己也觉得有点儿可怕。“谁要你的臭钱?坏蛋,你做梦!快滚开!”
我气喘吁吁地爬出了菜窖,浑身激动得直打哆嗦,“狮子头”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你跟那老司头啰嗦些啥?”他随口问。
“没啥。”
“我听见了。”他狡黠地耸了耸鼻子。
我不作声。刚才那突如其来的怒火是怎么回事呢?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你真傻。”“狮子头”回头说,吹着口哨。
“不,我这点儿聪明还是有的。”我回答他,“那老头是‘二劳改’,借了他的钱,他要是利用我去干坏事怎么办?不管怎么样,这种阶级敌人……”
“狮子头”突然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你真没白拿中学里那么多一百分儿。阶级敌人?你以为个个都像书上写的、台上演的那样搞破坏、想复辟呀?!我怎么就没见着过?他凭白无故拉你去干坏事?他何苦来着!”
“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我硬着头皮说。
“本性?啥叫本性?啥人不是顺着环境变?就说这老司头,就算他以前干过坏事,可现在,乖得像猫一样,要他多听话就多听话。我就是让他把我的尿喝下去他也绝不会说个不字。”
我有点儿恶心。
“连他自己也常说,这些年他接受改造,从鬼变成人了。要不是儿子下了乡,家里没人,他也早回广东老家去了。你呀,不借白不借,傻狍子。”他显出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替你保密,谁也不会知道。你得明白,除了他,谁也不会借给你这二十块钱的……”
我俩分手时,星星出来了,雪地闪着幽蓝的寒光,天上地下都是冷冰冰的。
第五部分:白罂粟冷到骨髓冷到心里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姨父死了,表妹跪在他灵前哭……
我出了一身汗,心怦怦乱跳。醒了,再没有睡着。天刚亮,我就起床了,提心吊胆地溜出了宿舍。
我在通往菜窖的那条小路上等着他。“狮子头”说过,老司头每天要比他早上班两个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
西北风吹得我脸生疼,帽沿儿都挂了白霜。我决定接受“狮子头”的建议;这是我头一回听他的话。
老头终于来了,提着饭盆,弯着那永远直不起来的腰。
我忽然想逃开,逃得远远的。我明明憎恶他,却要利用这种憎恶去获得他的好处。我成了什么人!
他从我身旁擦边而过,目不斜视。他就要走过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机会万一失去,也许永不再来,于是大喝一声:“站住!”
他机械地站住了,慢慢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吃惊。
“昨天……昨天的事……”我语无伦次了,心里压得慌,“你……还得把那……”
他听懂了,茫然点点头,却没有任何表示。他是在计较我昨天的态度吗?不,他的眼睛虽然暗淡无光,却是和善的。
“我……”他说。惶恐不安地四下张望着。我明白,他在踌躇,然而他还是伸出手到衣襟里去掏了,掏了半天,掏出一个小纸包。他小心翼翼地揭去那张纸,把那叠钞票塞在我手里,喏喏地说:“原想寄给儿子的,先不寄了吧……”
我拿钱的手颤抖了一下,他还有儿子?他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了。竟没有提一句让我什么时候归还他诸如此类的话。
那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见过他。他上工的时候我们还没起床,他下工时我们早已上了炕。开冻化雪后,菜窖就扒晒了,剩下几根骷髅似的横梁。也不知他被调去干什么活了。表妹那里很少有信来,听说姨父的病是一点点见好了,姨妈也从干校回了城。那二十块钱,表妹的信上除了“收到”两字以外,连声谢谢都没有;我当然也不会再提。可是月复一月,竟然就抽不出钱去归还老司头。三十二元钱的工资,除了吃饭还要抽一口烟。我学会了抽烟,也能喝上二两老白干了,否则每天下了班有多无聊呢,半个月放一部《南征北战》。图书馆倒是有一个,全是《艳阳天》,我倒着都能背下来,里头有个马小辫,妄想变天……
我差不多每个月都想把那钱还上,可是每个月都落了空。我于是特别怕碰到他。我悄悄向“狮子头”打听他的下落,“狮子头”说:“春天开荒点没人做饭,调他去做饭了。如今不是又该掐瓜秧子了吧,他该回来啦。这老头,啥都能干,早先地主要雇这么个长工,家里的活儿全齐了。”
“狮子头”现在越发时髦了。毛涤裤笔挺,二孔鞋铮亮,不知哪来的。我不敢问,因为我不想得罪他。
那是一个下雨天,不出工,在宿舍里政治学习。我靠窗口坐着,心不在焉地听着念报纸。突然,我的眼睛盯住了前面不远的一个黑影,我浑身冰凉,周身麻木,好像到了世界的末日。没错,是他——老司头了,枯槁的面容,干瘦的身影,披一张白塑料布,像一个幽灵,正向我们宿舍走来。他来干什么?一定是来找我要钱了?他等急了?乖乖,这事儿要让连队领导知道了可了不得,起码得开我一次批斗会。瞧吧,我也便宜不了他。。
我蹦下地,想把他堵在门外训斥一顿。可临出门的时候,我留下心眼在玻璃上张望了一下。我呆住了——他正用铁锹在挖门前那条水沟。水沟一会儿就疏通了,堵住的脏水顺沟向东淌去,西头是瓜地。他站在雨中看水流得差不多,就转身走了,对这边宿舍,他连眼睛也没抬一抬……
我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瞒过“狮子头”的眼睛,吃过中饭他爬到我炕上来,扔给我一支握手烟,挤着眼睛说:
“怎么,你还没开窍哇?”
我不懂啥叫“开窍”。
“你还惦着那二十块钱哪?真是头傻狍子;告诉你,不拿白不拿,你不还他,他又能咋的你?没凭没据,谁能证明他借给你二十块钱?他去告你,谁会相信他?你不会反咬他个诬陷!”
我听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就算缺钱,也从没敢往这上打主意。这怎么可以呢?借钱不还,赖账,不是比强盗、小偷更坏吗?我总还没坏到这份儿上。
“狮子头”在我脑壳上敲了一下:
“你怎么不明白,他们和我们不是一回事。我们是知青,他们是‘二劳改’,这一辈子有赎不清的罪!人和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嗳,比如连长,狠吧,成天在教育我们,在他眼里,我们知青啥也不是,当我们人看?”
窗外的原野一片昏黑,雨在不停地下着。我觉得冷,冷到骨髓,冷到心里……
第五部分:白罂粟新动向的批判会
三
不久以后。连里开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批判会。老司头被押来站在头一排。他站立的姿势引起全连队男女老少长时间的哄笑。他们说那是电影里头标准的反面人物,一个孩子还上前去推了他一下。批判他的罪名,是他向菜排的一个家属介绍了用野罂粟壳煮水治小孩腹泻的偏方,让别人发现了。连长说老司头不认真接受改造,乱说乱动,是妄图复辟,要加强对他的监视,命令他去掏厕所。那个家属又哭又闹地检讨了一番,说她情愿让儿子重新拉肚子,也不再上阶级敌人的当了。
我坐在角落里,不寒而栗。“狮子头”在远远的地方向我作鬼脸,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朝天花板喷出去一口烟,周围的一切都模糊了。去他的老司头子吧,既然他欠了人民数不清的债,白送我二十块钱也算不了什么。
从上个星期天始,我一跃变成了连队里自由自在的神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暂时去替了连队的通讯员顶班,每天骑车到八里地外的一个邮政支局去取报纸信件和汇款。通讯员风里来雪里去,辛苦是辛苦,可好就好在谁也管不着。
这天下午我送信回来,跳下自行车刚要进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背对着我,差点儿把我吓了一大跳。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头看着地,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
老天爷!是他,老司头子。
比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更瘦了,微微喘息着,一只手按着胸口,好像那里头有什么重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似乎看见了我身上的绿色邮包,便伸出一只手到衣襟里去掏。
我的头皮发麻,以为那掏出来的一定是一张借据。我的脸发白了,厉声说:“你要干什么?”
他哆嗦了一下,抬起眼皮,这才发现是我,竟然呆住了,那灰暗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欢喜的光泽。
“好久、好久,没见你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给我儿子,寄……寄一点儿钱。”他回答,一边把手从衣襟里抽出来,掌心里有一个小纸包,包得严严实实。
他好像是有一个儿子的,我突然记起来了,好奇地问:
“儿子?干什么的?”
“跟你一样,是知识青年,在广东乡下……那村子穷,靠我 寄……”
“你老婆呢?”
他的头又低下去了,一直垂到胸前。
“我犯了事,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