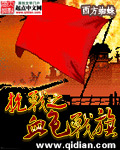性情张抗抗-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鹞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却不再打鼾,也不再哭嚎,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趁着小董去外头解手,陆德凑近了老鹞,低声问:真是你杀了薛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你可别胡说啊。
老鹞眼皮也不眨地说:是我杀了薛二,真个,这天大的事儿,我能胡说?
陆德瞪着眼半天说不出话。
陆德憋了好一会,气恨恨说:喝酒喝酒,你看你喝出这杀身之祸。
老鹞叹口气,摇摇头说:可要没有薛二和我喝酒,我也活不到今儿个。你不喝酒不知道,人喝醉了酒,那快活,真就像上了天一样……
小董进来了。老鹞把眼闭上,不再说话。陆德趴在桌上装睡,心里很是绝望,他想老鹞这样的酒鬼,走到这一步,也真是活该。
天快亮的时候,陆德突然被一阵叫嚷声吵醒了。睁眼一看,老鹞正在椅子上拼命地挣扎,用头撞着椅背,凳脚把地砖敲得咚咚响。绳子把他的脖子都勒出了血印,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暴突,整个身子不停地癫狂着就像疯了似的。
小陆子你救救我。老鹞嘴里吐出一阵阵尖锐而锋利的叫喊声:我死了,薛二他一家人可咋办那?谁来养活薛二他老婆……还有俩孩子?你去跟上头说说,别让我死,让我活……我活着才能把薛二的孩子拉扯大,作牛也成作马也成,作猪作羊我也干……我有罪,可我的命抵不了罪,死算个啥,活着抵罪可比死难多了……当初我要想到薛二那一家人,我说啥也不能依着薛二胡闹哇……
第四部分:何以解忧另一个酒鬼陆德
他的喊声嘶哑,吐出一口口浓而黏的血痰。走廊里传来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一辆“热特”在窗外发出震耳的突突声。老鹞被一群人推出门去的那一刻,陆德把头转了过去,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他听见老鹞嘴里还在不停地重复着刚才的叫喊,然后渐渐弱下去了。老鹞被拉上拖车前,突然跪在地上,冲着薛二家的那个方向,连着磕了三个头。
陆德后来听人说,老鹞到了场部后,提审中,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求领导免他一死,让他来养活薛二一家。他说活着比死更难,以活罪抵死罪,他也对得起薛二的在天之灵了。这个荒唐的请求,自然是遭到了坚决的拒绝。老鹞的死刑判决书下来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只是说,把他攒下的那500块钱,还有被褥衣物等全部家当,都留给薛二的家人。这些消息传到连队,那些坚持认为老鹞是图财害命的人,都不再吭声了。
很久以后,陆德到场部去办事,听人议论起老鹞的事。说他从县里的监狱被押解刑场时,按当地的惯例,有人递给他一碗酒。他盯着那碗酒看了一会,舔了舔嘴唇,然后把碗推开,转过了脸,头也不回地上了囚车。
很多年过去了,陆德早已离开了当年的农场。
返城后的陆德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先是开车,后来提升为机关的办公室主任。他很快发现这个主任的工作,其实主要是陪各种各样的人吃饭。当然吃饭只是一种名义,实质性的任务是喝酒。陆德上任后的第一天,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人给他敬酒的时候,他客气地声明自己滴酒不沾,对方再三坚持,他推辞不过,只得如实说明自己一喝白酒即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大家都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领导说我才不信这种鬼话呢,你喝一口我看看?领导将了陆德一军,陆德是没有退路了。迫于情势,他想今天是必得豁出去了——若是不喝下这口酒,让大家当场见证自己酒后的丑态,把他们都吓个半死,他这主任日后还怎么继续往下当呢。陆德横下一条心,抱定英勇就义的牺牲精神,接过那杯“酒鬼酒”,一仰脖子就灌了下去。
问题就在陆德把酒喝下之后,他为众人描述的恐怖情景,并没有在他身上显现。他万分紧张地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发作、倒地、昏厥等等,竟然踪影全无。他头不晕眼不花脸不红心不跳,平静如常泰然自若——这一天陆德的脸可真是丢大了,好端端的一个陆德,得了个当众撒谎不够仗义还欺骗领导的坏名声。
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陆德从那时正式开始了他的饮酒生涯。陆德惊讶甚至震惊地发现,原来自己非但不是不善饮酒,而是酒量大得出奇,几乎百喝不醉,白酒对于他来说等同白水,喝得再多,去一趟厕所回来,就挥发完了。陆德因工作需要,几乎三天两头出入于各种饭局酒局,无论遇着怎样厉害的酒徒酒鬼酒仙酒圣,一概被他喝得落荒而逃。而且陆德酒德甚好,从不耍赖卖傻;平日说话不多,喝酒时也仍是不怎么说话。喝酒时满嘴豪言壮语甜言蜜语胡言乱语的那些人,在陆德看来都是不会喝酒的。喝酒就是喝酒,说那么多话,把酒精都故意散发出去了,还算什么喝酒呢。陆德喝酒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就像在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务。久而久之,陆德在他的酒友中获得了良好的酒誉。若是哪一天他喝得身子都有些摇晃了,恰好夫人在场,在一边小声劝阻,或是用手掌捂住他的酒杯不让人再添,陆德就会横眉竖眼地对老婆大喝一声:躲开!
陆德曾对老婆说起过当年老鹞与薛二的事情。有一次他老婆生了气,就骂陆德肯定是被老鹞的魂灵附了体,所以才会在老鹞死后,变成了另一个酒鬼陆德。
但只有陆德自己知道,每回喝酒的时候,他其实一次又一次地在体验老鹞那天晚上在办公室对他说的那些话。喝酒真像上天么?哪怕就让他感受一次,也好了却了这番心思。
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过老鹞说的那种快乐。
第五部分:白罂粟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罂粟
我自幼见到的罂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罂粟。
一
十年前的冬天,快过春节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压得整个连队没有一条可通行的路。我是从雪窝里趟过去的,鬼哭狼嚎般的老北风把人的骨髓都吹凉了。我跌跌撞撞地爬上那白雪覆盖的高坡,如果不是出气口插着几束挂满白霜的高粱秸,你根本就无法找到这倒霉的菜窖。
“狮子头!”我爬下那嘎吱嘎吱的木梯子,冲着那黑咕隆咚的窖里头喊道。雪地上刺眼的阳光使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
“狮子头!”我扯着嗓子喊。
没有人答应。整个菜窖没有一点儿声音。风在头顶的旷野上尖叫着,而这里,却寂静得如同一座墓地。我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慢慢看见那狭长的地面上,堆放着的一排排整齐的大白菜。白菜显露着淡淡的绿色,散发着一种略带潮霉的气味。几盏昏暗的油灯发着微弱的光,照着木柱子的影子。我脊背上感到一阵阴森的凉意。
“狮子头!”我想起了我口袋里的电报。
过道那头,传来的响动,一个影子慢慢朝我走过来。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如果不是他的一双脚在移动,我真会以为自己大白天遇上了一具僵尸。他在离我不远的柱子下站住了,戴着一顶秃了毛的尖顶山羊皮帽,一双大棉上缠着绑腿;油亮的、肥大的棉裤,以及一件瘦小的旧棉袄裹着的弓起的背,使他的整个身子变成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形状。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使人怀疑他是否具有生命。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一直低头瞅着地上。
我的头皮不由倏地一麻,心里骂了一句:
“二劳改!”
“买脆(菜)?脆(菜)都是上好的……”他呐呐地说,依然没有抬头。
我听出来,这是个广东人。
“什么‘脆’不‘脆’,我找狮子头!”我嚷嚷着。
他微微抬起头,慌张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回转身,朝黑暗的过道走去。说实话,跟这么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呆在这四下无人的地下,真得有点儿胆量呢。这个农场的前身是个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有些人老家在城市,不愿回去挨斗,就留了下来,在农场干着最苦最累或是技术性较强的活儿。我们管他们叫“二劳改”。
他提着马灯,在前面走着,犹如一个恍惚飘摇的影子。在这个影子里是否曾经有过灵魂呢?我想。即使有过,现在大概也早已死去了……
他在菜窖的尽头停住了脚步,战战兢兢地把马灯略微举高了一点儿,仿佛害怕那微弱的光亮会照见自己的丑陋。
我听见了一阵肥猪酣睡似的呼噜声。在这与世隔绝的菜窖里,自然不怕妨碍了任何人,灯光照着地上的羊皮袄中裹着的一张胖圆的脸。
我用脚踢他。这个“狮子头”,没死没活地向连长请求来看菜窖,原来是这么个美差。让人家替他干活,他睡大觉。他学会雇工了;可雇工还得花钱呢!
他不情愿地坐起来,揉着红红的眼睛,是夜晚打扑克熬的。
“啥事?搅了我的好梦!”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和一封揉皱的信递给他。说实话,不到这种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决不会找“狮子头”的。他是我初一时的同班同学,后来留了级,我初中快毕业时,他初一的期末考试才头一回及格。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却“能耐”起来了,一夜之间戴上了手表,骑上了“飞鸽”。有一回还跟我夸耀“破四旧”时他亲手打死过一个地主婆。去年秋天我下乡到了这农场,人地生疏,也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个他,好夕也算个熟人。虽说他干活不咋的,又懒又贪,但比起那些耍嘴皮、搞小汇报整人的人,总还强那么一丁点儿。
我在他身下那羊皮袄里坐下来。刚要开口,听见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点儿的响声,好像是那老头在整理菜垛。
我有点儿不放心,努努嘴,说:“他……”
“没事,他敢么!”“狮子头”打了一下呵欠,晃晃乱蓬蓬的头发。
第五部分:白罂粟阶级敌人
我于是心急火燎地告诉他,我的表妹从桦川农村来信,说她的父亲在哈尔滨病重被送进医院,身边无人照顾,母亲去了干校,根本不让回家。她想请假回去,可身无分文。她刚刚下乡插队半年,分红才得了三块钱,实在没办法,才求我这个在农场挣工资的表哥。而我这个穷光蛋,这个月三十二元钱工资,扣除了十元钱的大衣费,又买了一顶棉帽子过冬,伙食费能否对付到下月开支还是个问题呢。
“狮子头”听着,忽然问:“她爸病了,她咋不向生产队借钱呢?”
我说:“她爸以前是公安局长,现在是‘牛鬼’。”
他又问:“她咋不向队上的同学借呢?”
“哪敢哪!谁一听这事儿都不敢借。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你不会去揭发吧?”
“狮子头”往嘴里塞着一片生白菜帮子,咔咔地咬着,懒洋洋地说:“那倒不会,咱一向够哥们儿意思,不过,这钱,可不好弄,要多少?”
“二十。”
他跳起来,往那铺着一层细沙的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说:“谁有那么多?开大银行啊?有点儿富余的,早变成老白干进了连长的肚子了……”
“狮子头,”我暗哑着嗓子,一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