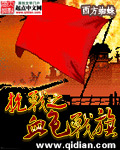性情张抗抗-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他睁眼时,车窗外已是一片灰蒙蒙阴沉沉的雪原。路边偶尔掠过一排苍郁的松林,枝上的残雪被呼啸而过的列车震落,如惊鸟的羽毛一片片脱卸,在空中飘零飞散。有几朵湿雪借着风力,猛地粘贴在肮脏的窗玻璃上,久久悬挂不去,像是一串串祭奠用的白花……
牛锛死了以后,13连的知青做过许多小白花,用信纸用手绢用白色的床单,做成一朵朵月季菊花牡丹还有百合……一丛丛一串串,悬挂在连部门前空场的旗杆上。那些白花一冬天都开在那儿,直到第二年猛烈的春风刮得昏天黑地。
马嵘木然望着窗外,那片看起来似乎是宽广宽厚又宽容的土地,在20年后却使他感到了一种疏远和陌生。虽然那口井那块草地依然常常惊醒在马嵘的恶梦中,但背景已渐渐远淡,如一幅古老的山水写意。真正令马嵘不安的,是那背景中仍旧鲜活的人物,他们似乎总是在一步步往前挪移,企图插入马嵘眼前平静快乐的日子,并且不怀好意地窥测着他,觊觎着他,使他不得安宁。
第三部分:残忍受伤最重的一个人
那一刻,马嵘突然怀疑,当初牛锛决定让他活下去,是不是为了在以后的岁月里,让马嵘独自一人来承受这种记忆的折磨呢?如此说来,牛锛的行为,岂不是有点太……太那个了么?马嵘不想说出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也许同杨泱最后说的那两个字,有一点相似。
马嵘心里很有些别扭。
列车路过一个小站稍停。马嵘抓起一团手纸跳到月台上去,把窗玻璃上的雪花统统蹭了下来。
就在傅正连被人们挖掘出来的当天夜里,杨泱就失踪了。
牛锛当然不会知道杨泱失踪的事。他自首的结果,是被工作组的人五花大绑地送去了团部。与傅正连的遗体搬运前脚后脚。
13连与此事有关的四个人──傅正连牛锛马嵘杨泱,几乎作了一次失踪的轮回。
杨泱是最后一个。
全连出动,对杨泱尽心竭力的搜索寻找,徒劳而归。杨泱那个时候就好像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单程车票。
最初那几天,马嵘想对大家说,根本就不必去寻找杨泱。杨泱和牛锛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当失踪的傅正连,被牛锛再现时,杨泱是一定会失踪的。杨泱如果不肯失踪,牛锛让傅正连失踪就简直毫无意义了。
但马嵘没有说。从牛锛在马嵘酣睡的那个时刻,决定使马嵘从这个事件中隐形失踪以后,马嵘就懂得这个从此“失踪”的自己,该为牛锛做些什么。
马嵘后来给团部的人送过许多烟酒,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单独同牛锛会见和告别的许可。有人悄悄告诉他,上头一直在怀疑他是牛锛的同伙,只是牛锛一口咬定是自己所为,是那天中午他把肚子疼得直不起的腰的马嵘,送回了连队以后自己一个人干的。上头另一种意见,也认为不要再继续扩大事态,对马嵘的追究暂时作罢。你还想看望牛锛?一边儿去吧!
马嵘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甚至很自信地对自己断言,一旦牛锛能够重新回到13连,暂时失踪的杨泱,必定会显形复出,如期而返。
那年初冬,13连的鸡不鸣狗不吠、猪不打盹马不蹶蹄。13连的人惶惶然凄凄然忿忿然;营房夜夜烛光恍惚,通宵达旦。任由豆荚苞米冻在地头、小麦烂在场院,被一场接一场的大雪压住,像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坟山……
根本无需马嵘费心张罗,13连全体,已经自动发起了一场为牛锛鸣冤请愿的“群众运动”。尽管在私下里,许多人都说牛锛那家伙实在下手太狠了,但那份申诉书,仍然写得哀婉动人却又义正辞严。众口一词,都说牛锛同傅正连并无个人恩怨、牛锛为了声张正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说傅正连长期迫害知青、逍遥法外,是可忍孰不可忍,早就该杀,杀一儆百。还说傅正连仗势欺人,上头有人偏袒他包庇他,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
申诉书被马嵘送到团部,在政治部武装部知青办转了几个来回,无人接收。那个冬天里,马嵘到过许多城市。他像一个乞丐似地在铁路沿线游荡。明明知道世界上有个地方叫作法院,但即便走遍天下,那时的中国惟独没有法院。又过了些日子,曾听说上头好像有人过问了此事,事情眼看就闹大发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不了了之。
马嵘精疲力尽地回到13连。他在茫茫雪原中绝望地想起,也许牛锛在关键的地方犯了一个错误。牛锛不该把傅正连亲笔签名的那份“罪状”,在那天中午的草甸子里,随随便便地扔给了工作组长。
13连的人得知牛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是在一场大雪过后。
13连的人都没能听见那声枪响。马嵘也没有。
牛锛作为杀人犯的代价,如他生前所愿──傅正连终于没有成为烈士。
大雪覆盖了通往公路的小道。一切都已草草收场。
风吹起雪原上干爽的雪沫,天地一片混沌。太阳出来了,像一张惨白的脸,隐没在深紫色的雪雾里。
很久以后,13连的人还是恍恍惚惚地觉得,深埋于地下的牛锛,只不过是一次暂时的失踪。他的灵魂已离开了这个地方。说不定哪一天,他还会在他们当年一起出发的那个城市里,再度与他们重逢。
所以后来他们渐渐一个一个地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了。以便不会错过同牛锛邂逅的机会。
没有人再提起杨泱。
只有马嵘明白,牛锛死了,杨泱是再不会回来了。
杨泱是受伤最重的一个人。
第三部分:残忍一个不错的结尾
但如果杨泱的失踪,是一种真正具备法律意义的失踪,那么,马嵘将永远无法完成牛锛在最后的时刻交给他的使命了。如果杨泱继续地失踪下去,那么,事情是否已完全违反了牛锛让傅正连失踪的初衷和动机了呢?还有,如果马嵘活着是为了等待一个永远不再出现的人,那么,马嵘的存在,实际上同一个失踪的人,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马嵘不想搞清这些。后来的日子匆匆忙忙,再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为这些伤脑筋。说实在的,他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比这更急迫更能产生效益的事,得真格用心思用计谋用手腕用钞票,去一个个解决。
马嵘租了一辆“拉达”,到达曾经属于13连地界的那片草场,已近黄昏时分。
他的脚一踏上松软的草甸,火车上的那种陌生感便荡然无存。昔日的营房依然远远地趴在原地,裸露着赭红色的瓦顶,静静地悄无人声。几缕浅淡的炊烟从红砖砌成的炉筒中升起,在灰色的天空里写出修长的一字形;小风掠过,那一字忽而改成个二字,又渐渐弥漫开去,散成个三字形,再散,便没了形状。一切都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一切都与20年前惊人地相似。只是,旧日的营房那儿,不会再有他认识的人了。
马嵘往草地中央走去。他用手扒拉开枯草上的积雪,在地上坐下来。
“就是这儿了。”他说,“我在哪儿,你就在哪儿。”
他点着了一根烟,然后用这根烟头上的火,又点着了另一根烟。他就那么两只手各执一根烟,轮流地吸着。
“我来看你来了。”他说,“啥也没带,就带我自己。”
“没别的,就和我一块儿吸一根烟吧!他又说。还是烟解闷。”
他一小口一小口地抽着烟,他想让那两支烟燃得慢些。
烟灰从手指的夹缝里落下,落在干草的根上,像是被弄脏了的雪。他坐了一会,觉得屁股发凉,便站了起来,掸了掸裤子上的雪末。
他那么站着,又咕噜了一句:不说悔了,不是悔的事,悔也没用。过了这么些年,再想想那事,你说值么?
一阵风吹过,他感觉有点冷,想起自己的围巾手套,忘在了车里。
喉咙里憋了一口痰,他重重咳一声,吐了。还是堵得慌。忽而就觉得嗓子眼里像是塞着许多话,是今天站在牛锛面前,才觉得非说不可的话。
“值么?我看不值。不怕你生气,如今想,那真傻。为了一个女人,为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搭上一条命。你要是活着多好,咱俩一块做生意,你下手狠,准保是把好手,一赚一个准。房子汽车早都置下了,夜夜卡拉OK娱乐城。想上哪上哪。世界上有的是快活地儿,要是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搞不到手呢?”
马嵘抽完了烟,从衣袋里摸出一瓶酒,用牙咬开瓶塞,将酒小心地洒了。雪地滋滋地响,塌下去一条缝,像是很不快乐地答应着。
荒原被纯净的白雪密密环绕着,如一座巨大的灵堂。几只乌鸦飞过,高处有了黑色,显得庄严肃穆。
马嵘环顾四周,觉得这个地方不错。他想牛锛还是会找地方的。
这地方大是大了点,弄不清牛锛究竟是在哪块草皮底下。
但也许正因如此,牛锛似乎无处不在。
马嵘的脊背忽而渗出了一层冷汗。
他愣愣地想,假如牛锛当年没死,假如牛锛活到现在,同他一起搭档做买卖,老板恐怕就轮不到自己来做了。牛锛将永远是老大,他充其量是给牛锛打工的,就牛锛那样的人,如有一天想要整治他马嵘一家伙,还不是白玩儿么?
再说,生意场上,亲兄弟也明算账呐,说翻脸就翻脸。自己若要想做手脚,牛锛抬手就把他灭了。何况现在的人,有枪不难。
如此看来,也许牛锛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更妥帖更恰当些。
马嵘心底浮上一阵庆幸,还有一丝坦然。他下意识地用皮鞋踩了踩松软的雪地,他记得当初牛锛埋得很深。无坟无墓、无字无碑;当然,牛锛是甭想再回来了。这里曾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晚霞慢慢往西边的天际滑落下去,如一匹殷红橘黄相间的织锦,被远处的地平线一寸一寸地剪断,飘入冉冉升起的黑暗中。
马嵘的眼前掠过杨泱留在炕上的那条被面,那条印着粉红色牵牛花的被面。
失踪其实真是一个不错的结尾。他恍然大悟。心里忽然涌上来一种对杨泱真诚的感激之情。如果杨泱不是这样永远地失踪下去,如果他真的娶了杨泱,而杨泱心里又始终想着牛锛,他马嵘还会有现在的好日子过么?真娶了杨泱,身边那些女人们还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么?闹不好打了离婚,他的财产还得分给杨泱一半呐……
假如假如……马嵘倒抽一口冷气。
幸亏幸亏……幸亏他没同牛锛一起死掉。
马嵘抬手看了看表,急匆匆往公路上的轿车走去。他不想在这里停留得太久。他得坐夜班火车赶到那个边境小城去签合同,这批皮货生意弄好了能赚一大笔钱,乘着车上这会功夫,还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砍价。
他边走边点着了一根烟。20年了,他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他已和牛锛两清。那个叫作马嵘的人,不会再到这个地方来了。
天暗下来。雪地黑呼呼一片,而天空洁白如银。
第四部分:何以解忧一贫如洗的薛二
那天晚上,寒风在旷野上呼号,发出警报似的尖叫。从下午开始,就下起了细密的小雪,溜进门缝的冷风,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