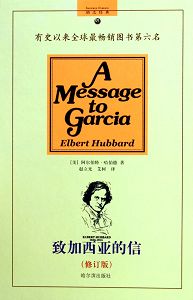失窃的信-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万一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例如,一粒手钻的木屑大概会变得象苹果一样明显。
胶接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头上出现任何不常见的缝,都是保险要经过检查的。”
“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的情况,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
“那是当然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一个细微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编上号,为的是一处也不会遗漏;然后我们仔细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个平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我们和先前一样也使用显微镜。”
“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费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是费了力,不过给我们的报酬也是非同小可。”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也比较校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一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吗?”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包裹裹;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一页一页地翻过,而不是象我们的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抖一抖就感到满足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如果装订的部分新近有人动过,要想让这种事蒙混过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我们都用针仔细地顺着缝检查过了。”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没有问题。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怕你倒是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现在,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 ”G一回答道,“我比我知道我在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能很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能!”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细枝末节。他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立即告辞,精神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从没见到这位善良的绅士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象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说:“哦,可是G-, 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下文吗?我估计你大概最后还是承认,要胜过那位部长是办不到的吧?”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吧,我象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都是白费力气,我早知道是没用的。”
“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说的?”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真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说有多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 不过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事实是,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办得到的事也都已经做过了。”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慢吞吞地拉长调子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我真地。。。。。认为,G—,你自己没有尽到力。。。。。。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我想,可以再尽一点力吧,嗯?”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挤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里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仿佛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病情。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那么,医生,你要指教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 ’ 阿伯尔纳采说,‘噢,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是当然罗。’”“可是,”警察局长说,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付出代价。我真地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迪潘回答道,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一言不语,一动也不动,张着嘴,全然不能相信地瞧着我的朋友,眼珠子好象要从眼眶里暴出来了,后来他显然有些恢复了常态,他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瞪了几眼,终于开出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署了姓名,隔着桌子把支票递给迪潘。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官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于是,他慌慌张张起来挣扎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房出,冲出了这幢房屋。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的那个时候起,他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他走之后,我的朋友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大凡在业务上必须懂得的事情,他们都完全精通。所以,当G一向我们详细地讲他在D一旅馆搜查房屋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完全相信,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他的检查是靠得住的。”
“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吗?”
“是的,”迪潘说,“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其中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一丝不苟。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这些家伙大概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的。”
我不过笑笑罢了,可是他似乎十分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一切。
“那么,这些措施,”他接下去说,“本身都是好的,而且执行得很好。它们的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能适用。对于这位警察局长,一套十分别出心裁的计策,可说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①他硬要使他的计划适合这套计策。
他处理他手上的案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都比他头脑清楚。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在玩‘单双’游戏的时候,他猜得很难,引得人人钦佩。这个游戏很简单,要用石弹子来玩。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定数目的弹子,要求另一个人来猜这个数是单是双。如果猜中了,猜的人赢一粒弹子,如果猜错了,他就输一个弹子。我说的这个男孩子把学校里所有的石弹子都赢过来了。当然,他猜起来是有点道理的,那不过是要观察和衡量他的对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对方是个大笨蛋,举着握紧了的手来问,‘是单是双?’我们的小学生回答,‘单,”他输了,可是第二次再试,他赢了,因为他自己寻思,‘这个笨蛋第一次用的是双,他那一点狡猾本事只够让他在第二次用单数,所以我要猜单,”他于是猜单,赢了。那么,对于比起先的这个笨得好一点的,他会这样来分析:‘这个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单,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大概是要采取由双到单的简单变化,像第一个笨蛋一样,可是他再想一下就觉得这种变化太简单了,最后他决定还是像先前那样用双数,所以我要猜双;’他猜双,赢了,这是小学生推理的方式,小伙伴都说他‘侥幸’……那么,归根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过是,”我说,“推理的人有设身处地体察他对手的智力罢了。”
“是这样,”迪潘说,“而且,我还问这个孩子用什么方法来做到能完全设身处地的体察对方,他所以能取胜正在于此,我得到的回答如下:‘我要是想弄清楚哪个人有多么聪明,或者多么笨,①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强盗,他把落到他手里的人放生到一张铁床上,砍掉比床长的部分,比床短就硬把这个人拉长。后人遂以此比喻生搬硬套,强求一致的措施。
多么好,或者多么坏,或者他当时在想什么,我总是要模仿他脸上的表情,尽可能学得和他一模一样,然后等一等来看,我脑子里或者心里会产生什么思想和情绪才配得上这幅神气,才装得一模一样了。’小学生的这种反应是一切貌似深奥的东西的起因,卢歇夫科①,拉布吉夫②,马基雅维里③还有康帕内拉④,都曾经被认为有这个特点。”
“而且推理的人要有完全设身处地体察他对手的智力,”我说,“如果我对你理解得正确,这要看他把对手的智力估计得多么准确了。”
“从实用价值来看,这是关键,”迪潘回答道;“警察局长和他那一帮人这么经常地失策,首先是因为没有这样设身处地想一想,其次是估计不当,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没有估计他们所对付的人的智力。他们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巧妙主意,在搜查任何藏起来的东西的时候,只想到他们自己会以什么方式来隐藏东西。他们只有这一点对——他们自己的智谋忠实地体现了大众的智谋,可是如果那个罪犯的鬼主意在性质上跟他们自己的不一样,他会使他们枉费心机的。当然罗,如果比他们自己的高明,那就老是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不如他们,那也时常会这样。他们进行调查的原则一成不变;至多,由于情况非常紧急,或者在重赏的促使之下,他们会把老一套的办法扩充或者变本加厉地运用一番,可也不会去碰一碰他们的原则。例如, 在D一这桩案子里,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去改变行动的原则呢?钻孔,用探针刺探,测量,用显微镜观察,还有把房子的表面分成多少编了号的平方英①卢欧夫科(161—1680),法国大臣兼道格学家。
②拉布吉夫,人名,余不详。
③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历史学家、政治家兼散文作家。
④康帕内拉(1568-1639年),意大利哲学家。
寸,这一大套是干什么呢?这不过是根据那一套对人类的心机的见解,把警察局长在长期例行公事里习以为常的那种或者那一套搜查的原则,变本加厉地运用起来,还能是别的吗?难道你没有看出,他认为理所当然,凡是人要想藏信,虽然不一定去把椅子腿钻个洞,至少也总要放在什么偏僻的小洞或者角落里,这岂不是跟劝人把椅子腿钻个洞来藏信的主意一脉相承吗?难道你也没有看出,这样考究的藏东西的角落只适合
![[英格丽德·里普曼_熊音_王亚明] 失窃的记忆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