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三国-第2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司马攸推辞道:“叔公虽然言之成理,但景父王已故去十年了,所谓时过境迁,现在还有几人曾记得他的功勋?攸虽不孝,却也知父命不可违,父王做何决断,攸决不相违,更无意左右父王的心思,一切顺其自然,攸绝无意强求。”
司马孚抚须点头嘉许道:“攸儿能做如此之想,我心甚慰,你放心吧,来日再进晋王宫,我自有安排。”
┄┄┄┄┄┄┄┄┄┄┄┄┄┄┄┄┄┄┄┄┄┄┄┈┈┈┈┈┈┈┈┄┄┄┄┄┄
司马昭这段时间里病情时好时坏,太医们都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司马昭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不禁是感慨万千。
司马昭的这一生,充满着诡谋和算计,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真正地站上权力的巅峰,与他的铁腕是密不可分的,固然司马昭的成功是依靠父兄的奠基,但和东吴的孙权一样,自己没有能力,终就还是无法掌控大局。
司马师去世已经是整整的十年了,在司马昭的努力经营之下,司马氏在魏国的势力已经是无人可以撼动了,整个朝政已经被司马家所统治,司马昭显露出来的勃勃野心曾经就让曹髦忿恨不已,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昭的野心,也的确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站在离真正的权力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司马昭也曾想着跨过这一步,但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内心深处告诫自己,其实做曹操还是很不错的,将江山留给后辈儿孙,让他们去将司马家的江山发扬光大吧,他此生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风光日子,也足可告慰平生了。
弥留之际,司马昭一直为立储之事左右为难,长子司马炎英明果毅,颇有乃祖之风,次子司马攸聪慧多才,秉性温纯,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各有千秋,但似乎又各有缺点,无论是选谁,司马昭都觉得很难取舍。
他的王后王元姬则是倾向于次子司马攸,她对司马昭道:“桃符性子急躁,但秉性和善,如果他能继承王位的话,必然是兄弟和睦,如果安世继位的,难对兄弟慈爱,或恐容不下他,将来手足相残,该是天大的不幸。”
做为母亲,王元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子如何来和睦相处,历史上血的教训比比皆是,身在帝王之家,兄弟之间鲜有善终者,以司马攸的性格,可以让兄弟关系维持下去,而换作司马炎,必不能容物,王元姬择嫡的立场自然是以护佑亲情来考虑的。
司马昭却不持同样的观点,他择嫡而立,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胜任晋王甚至是天子的位子,司马昭明白,自己死后,不管是那个儿子继位,都有可能效仿曹丕篡汉一般,逼魏主禅位,所以自己现在所选定的人选,将来是主宰天下的,自然地慎重起见。
司马昭拿不定主意,便请太傅司马孚、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入宫来商议,王祥和何曾口径一致,都是很明确地支持世子司马炎,而司马孚态度模糊,既不说支持司马炎,也不说支持司马攸,模棱两可,以自己耳背为借口,含糊其辞,始终也不肯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好在司马昭这几日身体还行,自然感觉还不错,所以立储之事也不再那么地迫切,既然司马孚没有表态,司马昭就决定再等等看。
立嗣是一件大事,司马昭虽然请来了三公之列的太尉王祥和司徒何曾,但他们的意见也只能是仅供参考,司马昭更看重的是自己叔父司马孚的看法,毕竟立嗣虽为国事,但也是家事,只有司马家族内部人的,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但司马孚一向难得糊涂惯了,这几年更是淡出了权力的核心,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几度废立皇帝,司马孚都置身事外,从不参与,但司马昭对他一向很尊敬,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而且一直给他高位,就算是他从太尉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司马昭仍然封他为太傅,并且加封为长乐公,如此优厚的待遇整个魏国都挑不出第二个来。
既然司马孚继续地装糊涂,司马昭也是无可奈何,于是司马昭决定过几天召集在京的所有晋王大臣,共议立储之事。
参与此次议储的,也全部都是晋王司马昭的亲信之臣,而且皆是三品以上的官员,皆称是国之栋梁,司马昭如此行事,除了商议立储之事确定继承人之外,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那就是让这些重臣来见证新王的上位,并让他们对新王保持一贯的忠诚,以利在司马昭去世之后,政权得以顺利地交接。
接到传召的诸位大臣,丝毫不敢懈怠,他们都很清楚,这是决定天下大事的一次议事,能参与其间,就是莫大的荣幸,他们皆是脱履上殿,神情肃目。
第533章异相
八月的天,正是秋高气爽,暑意全消,司马昭形容枯槁地坐在王榻之上,透过宽大的宫门,可以看到一朵悠云在碧蓝的天空中游荡着,司马昭的心绪也随着那片云变得飘忽不定。
五十而知天命,司马昭今年也已经是五十有五了,如果他不清楚知天命的话,那还真愧对那英明神武四个字。司马昭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所有的功名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一般,之所以对生死如此恋恋不舍,那是因为自己的身后事还没有交待清楚。
司马昭年轻的时候素以干练豁达称著,遇事果决,行事狠辣,从来不会拖泥带水,一次次的宫闱之变,司马昭都处之如泰山,这也是他能够站立在权力巅峰之上的筹码。但人老了,当年的锐气就不复存在了,司马昭也变得优柔寡断起来,在立嗣的问题上,始终也无法做出决断。
司马昭不得不召他的这些亲信属下进宫,让他们给自己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大臣们自觉不自觉地分列为两班,支持司马炎的炎党一派在左边落坐,支持司马攸的攸党一派在右边落坐,壁垒分明,隐隐有针锋相对的意思。
左边落坐的有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中护军贾充、散骑常侍裴秀、侍中荀勖、尚书山涛、御史大夫王沈等,皆是国之栋梁,社稷重臣。
右边落坐的阵容显然没有左边的强大,不过却也是人才济济,有侍中任恺、中郎令庾纯、河南尹夏侯和、尚书郎刘毅、黄门侍郎向雄、侍中吴奋、中书郎张华等人。
这个时候,炎攸党争已经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虽然炎党一派结党较早,而且其成员多为手握重权的朝廷重臣,其中不乏三公级别的人物,但攸党一派却是经过分化组合,以任恺、庾纯为首的少壮派锐气勃发,气势极盛。
今日司马昭请诸臣来王宫议事,其用意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炎攸两派都在摩拳擦掌,准备一争长短。
司马昭看到看人差不多都到齐了,轻轻地咳了一声,用略带疲惫的嗓音道:“孤患病久已,自知天命不祚,唯忧后继无人,今召诸公至此,便是商议一下继嗣之事。孤长子炎、次子攸,皆有不世之才,诸公以为何人可继大统?”
任恺和庾纯对视了一眼,庾纯率先而出,揖礼道:“晋王,臣以为舞阳侯清和平允,亲贤好施,能文善武,为世之楷,才识过人,名望卓著,堪为大任。”
左边阵容之中的尚书山涛当即出列道:“废长立幼,违礼不祥。”
山涛乃“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嵇康并称于世,俱为名士,不过山涛功利心太重,醉心于官场,最终和阮籍、嵇康背道而驰,嵇康曾写下千古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明心迹。
太尉王祥亦道:“废长立幼,取乱之道也,前代立少,多致乱国,汉末之时,袁本初、刘景升之事亦历历在目,愿殿下思之。”
任恺闻言立刻是举步而出,道:“山尚书,王太尉此言差矣,何为长,何为幼,舞阳侯虽为晋王次子,但因景王无子,已过继到景王门下,依法统而言,舞阳侯乃长门嫡子。殿下此前有言‘天下者,乃景王之天下,吾何与焉?’以舞阳侯继嗣,是为正统,何来废长立幼之说?”
炎党一派理屈辞穷,就是因为司马攸虽为司马昭次子,但过继到了司马师的门下,而司马氏的江山,大半的功劳要归属于司马师,当初也是因为司马攸年幼,只有八岁,司马昭才继承了兄长的大业,如果当时司马攸再年长一点,能不能轮到司马昭继位都是一个问题。
这一点,司马昭似乎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公开的场合,司马昭都几次说过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归攸的话,不管这是不是违心之言或者是用来安抚司马师的亲信部下的,总而言之,司马昭是说过这样的话,任恺此刻站了出来,旧事重提,算是狠狠地打了炎党的一把脸,你们不是说不能废长立幼吗,拜托你们先搞搞清楚,谁是长谁是幼?
短暂的沉默之后,裴秀又跳了出来,道:“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中抚军统领内外诸军,一般都是由资历深厚的将领所担任,而此刻则是司马炎现在担任的职务,故而裴秀以中抚军来称呼司马炎。裴秀这里提到的司马炎有异相,是说司马炎“立发委地,手垂过膝”,司马炎头发超长,站起来,头发可以垂到地上。有人或许会说,这算什么呢?只要蓄发的时间够长,谁都可以头发长到拖地啊。其实不然,多数人的头发只要到了一定的长度,必定会越长越稀,如果落地的仅仅是筷子一般的小辫子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第一点普通人还可以达到,而第二点就有些难度了,站起来双手下垂,竟然超过膝盖,完全是长臂猿转世嘛。可是古人就认定手长乃是大福之相,帝王之相。蜀汉的开国皇帝刘备,就是生有异相,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这一点与司马炎竟然有些相似。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也是生有异相的,碧眼紫髯,搁到后世,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老外血统嘛,可在当时,生有异相一般就可以解释为大富大贵之相,甚至可以位及九五。
当初司马炎为了拉拢裴秀,特意地示自己的异相给他看,并问道:“人有相否?”裴秀因此而归心。
而此刻裴秀当场提出来司马炎的异相,那就是有当皇帝的本钱,此后必定是大福大贵,必然可以成为万万人之上的天子。
虽然现在的司马昭比天子还是牛逼,但他毕竟也只是一个王爷,再怎么说也是在天子之下的,当然司马昭如果想要篡位,也绝对是无人敢反对的。
第534章难以决断
可即使是权势熏天的司马昭,想要跨出这一步也并不是很容易,正如当年的曹操,本来有机会自己称帝的,但最终还是没有称帝,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司马昭也是同样的心理,他欲效仿曹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是做一个权臣罢了,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承嗣大业,完成司马家族几代人的期望。
其实对于司马昭而言,两个儿子都很优秀,至于选那一个,也是令司马昭头痛不已,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实在是难以取舍。
张华晒然一笑道:“异相之说,皆多虚妄,难不成民间有许多立发垂地双手过膝之徒,他们也有资格议储而立?若为储君,德行当排位第一,舞阳侯聪慧过人,温敦纯良,可谓是仁德之主。”
司马昭沉吟未决,贾充也瞧得形势不利,上前道:“中抚军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
贾充的话,说的比较委婉,但实际上他是在提醒司马昭,司马炎在朝中在军中已经成为了众人的君主,现在已经是不可能更换了。
炎党阵营,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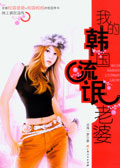
![[星际]国民宠儿.上将的农妻 作者:朝千年(晋江vip2015-03-12正文完结)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