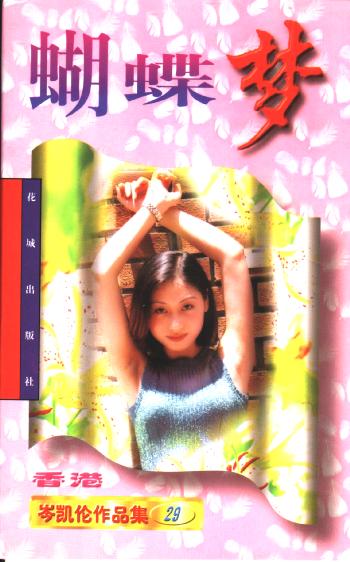蝶梦-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几日厨房闹老鼠,角落里撒着些药铺买来的砒霜!”
离春低头看那一地残渣,大惊失色:
“方才,夫人是怕他兑现承诺?这对我,简直是救命之恩!”
“离娘子不必慌张!”
“这谈何容易!难道,您当年认清那人的豺狼性情,竟十分冷静?”
房夫人苦笑:
“哪里?我比你现在尤有过之,整日担心小姐落入魔掌,又要提防表少爷遭他毒手。后来被求亲,我说怕旁人对小姐照顾不周,好像她离不了我。其实,我哪有过这般自大的想法?还不是担心大家被那人蒙蔽,出了大事后悔莫及。直到表少爷直抒胸臆,与小姐婚事粗定,我才略略安心。出嫁前,一再对小姐说,尽快与表公子成礼,家里的人一个也不要带过去,有故人找上门切莫收留。小姐虽不解真意,但听我再三嘱托,也回答记住了。为人妻后,时常想与小姐联系,却屡次耽搁。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阻挠,但我心底,也怕得知那边的消息。这实在是掩耳盗铃,宁愿相信旧日相识都过得安稳。万一证实真有变故,怕会自责一世。所以,听离娘子说她一家幸福,本想询问家仆中有没有那样一人,却不敢出口。正欺骗自己,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就看到那糕点……”
看房夫人双肩颤抖,离春劝慰道:
“以夫人所见所闻,会忧虑也属正常。但静心分析起来,那人虽从闽南追到长安,但一切种种,只为博得心仪女子的青睐。两情相悦之后,为了长长久久,才会下狠手扫除障碍。若她对他仍是不屑一顾,他便没道理铤而走险。”说到这里,语含试探,“难道您是怕,夫人真对他生情不成?”
“不!没有。”急忙否认,“小姐饱读诗书,绝非轻浮之人。”
“可据我听说,她是心肠极软的。这样的人,通常重情,若身边有一人数年如一日,对她穷追不舍,难道当真铁石心肠?”
“话可不是这样说。”房夫人正色道,“正因她情义为重,决定嫁给表少爷,必然是爱极了他。作了恋人的妻子,已是心愿得遂;再为人母,便不光情爱,更有责任。按着自己的意,一路经营至今的和美日子,小姐那样聪明,怎么会亲手毁了它?”
“人心隔肚皮,不好说的。”离春眼色诡谲,“您与她是相伴过几年,但又没成了人家肚子里的蛔虫。再者,两位夫人姐妹情深也好,主仆情深也罢,这说话时难免偏私些,怕是作不得准。”
房夫人一听,又是焦急又是恼怒,头颅左右摇摆,想再为小姐的名节辩解两句。可是,无论说些什么,也会被归结到袒护上,无奈间,索性往地下一跪,举手郑重赌咒:
“我封玉兰对天起誓,方才所言,如有半句标榜夸大,就让我……”
从她跪倒在地的一刻,房竞萧已坐不住了,大步插到中间,手臂一伸,袍袖垂下,将妻子挡在身后,不悦道:
“离娘子,我一心一意当你是朋友,你非但不坦诚,还玩起手段来。”
“哦?”离春冷笑。
“若真如你所言,你和我那姨姐有交情,以你洞悉人心的能力,还会看不出她品性如何?你心中明明已有定论,却仍对我妻子言语相逼,不知是为了哪般!”
离春也不解释,只默默自语,好像说什么“果然是同活”,而后抬头孤傲道:
“既然公子疑我不怀好意,再待下去也是无趣,那就告辞了,想二位也无意相送。不妨,来时路我还记得。”
摔袖起身,走几步出了角落,忽而扬声道:
“夫人,我忘了东西,劳您将桌上那柄扇子拿给我。”
房竞萧正要代劳,夫人见气氛紧张,不愿真的闹僵了,推开他手自己送了出去,留丈夫在原地等待。本应立刻就回,却迟迟不归,他担心向外探看时,见两名女子正低声说话,手里动作似在传递什么东西,而妻子连连点头,脸上闪动着跃跃欲试的喜色。他心中不解,等离春走后,才唤着“兰儿”打听,却只被那双美目温柔地挑过,不曾得到回答。 时间又过了两日。
这两日间,乱神馆十分清静,没有封家人上门督促,也不见京兆府过来骚扰。离春在馆中休养,甚是惬意。而与井边女尸案相关的另一处地方,却是沸腾喧闹。
大理寺门前,差官云集,戒备森严。这般气势,让百姓们不敢靠近,纷纷站在远处揣测:好大阵仗!莫非是杜大人回京了?直到丁烨押来一辆蒙盖黑布的囚车,才知道猜得不对。
囚车刚到,各位官爷的表情更是严肃,一见犯人下车,立即围成一圈,将众人的窥探阻断在外。有人议论说,这样郑重谨防逃脱,不知是怎样的悍匪!可有眼尖的,从人墙缝隙间窥见罪人身段,依稀是个女子。嘴快的于是改口:那多半是怕同伙来劫囚了!
犯人被簇拥着,投入大理寺监牢。围观者见事情已了,纵然意犹未尽,也悻悻散去了。
牢房中,管理囚徒的是狱吏,其中最高级别的是狱丞。这新进的犯人有什么要特殊关照的,自然对他说。
胡狱丞听着丁烨千叮万嘱——不得走漏消息,来探监的绝不放行,脸上唯唯,心底却不以为然:这样的重案犯,探视之人必多,还指望借此有些收益,一概拒绝岂不是断了财路?
静待丁烨走后,便怀着阳奉阴违的心思,坐等探监者到来。掌管牢狱多年,知道一般情形下,新囚进来前几日,正是访客最多的时候;等过了旺季,就无人问津了。
他料得果然不错,才不过两个时辰,第一位客人急匆匆大驾光临。这人头戴帷帽,帽檐黑纱落下遮住面容,一身黑衣阴气沉沉,身段颇为窈窕,应是一名女子。
狱卒们多不是什么识礼的货色,平时若碰到这样遮遮掩掩来看视的,态度便轻浮起来,刁难也不免加倍。但对这位可是不敢,她身周透出的隐隐寒气,令人望而却步。
胡狱丞打消了调戏蒙面人的想头,问明来意,打着官腔将丁烨的告诫重复一遍,露出爱莫能助的模样。这一番听似无转圜的表示,只期望对方能明白“道理”;看她自袖中摸出一块银色的亮物,果然是明白了。
打通了关节,那女子却站在原地,看着狱丞咬银子,并不移步,被催促后反问道:
“怎么?这样就可以进去了?”
“废什么话?我说能,你还不信啊?”
对方悠然一句:
“出尔反尔,确实令人很难相信。”
“你!”
狱丞大步上前,面目狰狞,要以气势压人。那女子却缓缓撩起面幕,一分一寸,现出左边脸上的赤红胎记,直吓得面前人膝盖一软,“扑嗵”一声跪在地上。前后动作串连起来,倒好像他早已认出了来人身份,忙不迭扑跪到人家脚下似的。
见他双手颤抖,张着口却发不出声音,离春提示道:
“叫馆主!”
胡狱丞照样称呼一遍,压低着头不敢仰视,耳边传来冷冽之声:
“大人您怎么也是从九品的官职,对我一个平民行此大礼,未免太客气了!”
“您折煞小人了!”态度更加惶恐,“小的怎么敢让您称呼‘大人’!刚才的事,请您听我解释,我如此作,并非发自本心,也是迫于无奈……”
“难道你要告诉我,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小儿嗷嗷待哺?莫非杜大人是个贪官,把你这下属的俸禄都污了不成?”
“小的绝没有这意思!小的该死!”
刚才只是跪拜,现在已磕头如捣蒜。离春冷眼旁观了一会儿,嫌那“咚咚”声吵闹了,阻止道:
“行了!真把地上砸出个坑来,还要费力修补!说些正经事吧,今日来的这名女犯,你可知她的身份?”
“听丁大人讲过。她名叫红翎,是封门血案的疑凶。”
“被捕之后,她可曾说过什么?”
“不曾!自从归案,始终一言不发;丁大人尝试审问,可惜她牙关紧咬,怎么也撬不开!”
“撬?!”离春眼神一闪,“用刑了?”
听得语气尖利,胡狱丞再次额头触地:
“没有!杜大人平日时常训诫,遇到骨头死硬的囚犯,均暂时收监,不得用刑。”
“好!”声调和脸色一起和缓了,“我要进去看看,和她说上两句话。”
“您快请!”十分殷勤。
“等我与她谈过,前脚离开,后脚又有人来,你待如何?”
“就算他捧出金山银山,也要挡在门外,不让他瞧见犯人一根头发!您尽管放心!小的已知错,以后再不敢了!”
“如此甚好!”离春沉声道。
“可……”胡狱丞为难地望着方才匆忙丢下的银两,捡了还回去,怕再触怒了瘟神;就这么扔着不管,又不成话。正不知如何是好,离春开口了:
“银子你留下,永远记着,这是你最后一笔不义之财!”
向监牢深处走出几步,又回身补充:
“若真是生计艰难,这管监牢的一众兄弟,难道就帮不得你?再说,五监九寺之中,数你的顶头上司脾气最佳。遇到燃眉之急,不妨向他求助!”
胡狱丞摸过去,将银子捏在手里,依然跪在地上,心里不知什么滋味,只呆望着离春背影。她停在红翎的牢房前,面前轻纱微微起伏,大约是在说话,只是距离远了些,听不清内容。但这寥寥几句,却引发了一件奇事:
红翎原本抱膝蜷缩在牢房角落,表情呆滞,毫无生气。这时却如梦初醒,连滚带爬到木栅前,把脸极力塞到缝隙间,泪流满面。一手胡乱拭着泪水,一手极力伸出,想揪住离春袍角。终于够不到时,伏地放声大哭,撕心裂肺地喊道:
“夫人,红翎对不起你!!夫人!夫人……”
离春正与红翎隔栏交谈时,乱神馆接待了井边女尸的另一位贴身丫鬟。
红羽见了苑儿,直言要寻离娘子说话。苑儿虽是头次见她,但此女事迹已耳闻不少,未免心中不喜,冷淡地告知:
“我家馆主出去了!”
“出去?她不是说,近些日子要闭关吗?”
“这,馆主怎样决定,自有她的道理。说不定,又是为封府的事情奔走去了。怎么?你有何贵干,可说出来由我转告。”
“其实,也没什么正事,只是顺路来瞧瞧,为我家夫人招灵的事,到底进行得如何了。”
红羽用词谨慎,婉转表示小公子已等到心焦了。来意已大致说明,苑儿也露出逐客的意思,她却仍是不肯离去,说既然出来一趟,定要见了本尊,得到确切答复,才能回去的。
客人磨蹭着不走,主人也不好硬赶。两名女子就在厅里枯坐,等待离春回来。无奈,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影。馆中二人面面相觑,虽彼此看不顺眼,却同样有时光待消磨,只得被迫亲近,共同找些事情做。
前两日那张棋秤,一直摆在厅中未曾收起,苑儿眼神落在那上面,红羽心领神会,两名下女相视点头,便对弈起来。苑儿是个生手,只略懂得规矩,可以提子时,就一路追杀,与对方打劫到底。这样自然错失了许多良机,让红羽执的黑子占到了兵家必争之地,往后就翻身乏术了。
一局终了,独叶茶也品过几盏,离春仍是没有露面。经过一番熟悉,已不似先前的生疏,两人试探着寒暄几句,就算是攀谈上了。
“离娘子闭关许多天,招灵一事应大有进展吧?姐姐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馆里伺候,想必知道得极详细了。”
“说来惭愧,这我并不清楚。馆主做事向来高深,经常连我也蒙在鼓里。你们那边许久得不到音信,会不安也是自然。不过,她既答应了,就一定作得到,还请不要怀疑。”
“离馆主的法力,我们都是深信的。吸引夫人魂魄上身,对她应只是举手之劳。大概已成功试验过几回了呢。”
“若是这样,夫人也许会借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