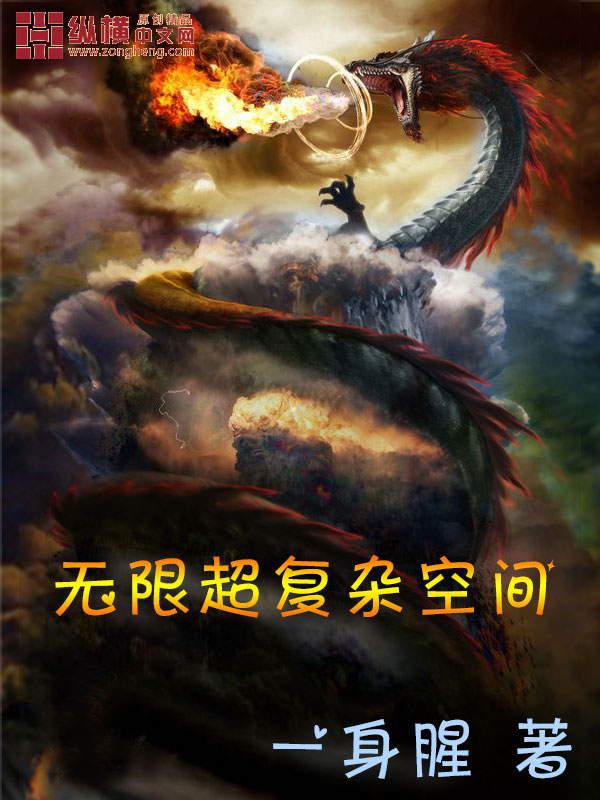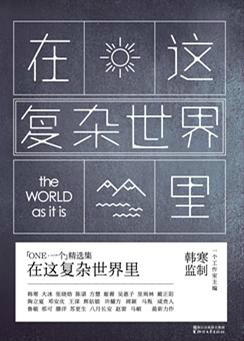复杂-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会议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听到他对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大谈他最近的一些想法。
有传闻说,曾经有人听到他对一个复印机修理工解释他在理论生物学上的一些观点。如
果他身边没有别的访客,他很快就会对离他最近的同事不断解释他已经重复过一百遍的
东西。没完没了,不厌其烦。
这已经足以使他最好的朋友都大喊着受不了,落荒而逃了。但更糟糕的是,这使考
夫曼因过于自我中心、唠唠叨叨和缺乏安全感而著称,尽管有些同事回过头来会说,他
们还是非常关心考夫曼的。他们会非常愿意告诉他:“确实,斯图尔特,这个想法大妙
了。你真是非常聪明。”但不管大家对考夫曼的真实感受如何,考夫曼都无法自控。这
二十五年来,他一直被一种景象所控制——这个景象如此强有力、如此不可抗拒、具有
如此震慑人心的美,他根本就无法不被它所紧紧吸引。
最接近对这个景象解释的英文词是“秩序”。但就是这个词也无法抓住考夫曼所说
的意思。听考夫曼谈论秩序就像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语言谈论某种原始的玄学。对考
夫曼来说,秩序就是对人类存在的奥秘的回答,它解释了在这个似乎是被偶然因素、混
乱和盲目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宇宙里,我们怎么会作为有生命的、会思考的生物出现并
存在的。对考夫曼来说,秩序告诉我们,人类确实是大自然的偶然产物,但又不仅仅只
是偶然的产物。
确实,考夫曼总是急忙补充说,达尔文完全正确:人类和所有其他生命体无疑都是
四十亿年随机变化、随机灾难和随机生存竞争的产物。我们人类并不是上帝的发明,或
太空外来人。但他会同时强调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法也并不是人类存在的故事的全部。
达尔文并不知道事物存在自组织的力量,即:将自己组织成日益复杂的系统的持续力量,
尽管事物也像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那样,同时也存在永远趋于解体的持续力量。达
尔文也并不知道,秩序和自组的力量创造了有生命的系统,就像创造了雪花这种形式,
或一锅沸腾的汤的热汤分子对流的现象。所以考夫曼宣称,生命的故事确实是一个偶然
现象和偶然事件编织而成的故事,但这也是一个关于秩序的故事:它表现了一种融于大
自然的经纬之中的深刻的、内在的创造力。
“我喜欢这个故事。真是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这个故事的一幕幕的
呈现。”
秩序
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所的走廊上,你会很容易就透过一个办公室敞开的门
看到墙上贴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画像:爱因斯坦裹着一件大衣,心不在焉地走在普林斯顿
大学的雪地上;爱因斯坦神情专注地凝视着照相机镜头,破旧的毛衣领子上别着一支自
来水笔;爱因斯坦咧开嘴大笑,对着全世界伸舌头。这个相对论的创立者几乎是大家共
同的科学英雄,是深邃的思想和自由的创造精神的象征。
在五十年代初,爱因斯坦当然是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名叫斯图尔特·考
夫曼的男孩心目中的英雄。“我极其崇拜爱因斯坦。不,不能用崇拜这个词,应该叫热
爱。我热爱他把理论看作是人类心智自由创造的思想,我热爱他视科学为对造物主秘密
的探究。”爱因斯坦用OldOne来比喻宇宙的创造者。考夫曼对1954年第一次接触到爱因
斯坦的思想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才十五岁,读到一本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雷奥波德
·英费尔德(LeopoldInfeld)合写的一本关于相对论起源的普及读物。“当时我为能
够看懂这本书,或我以为我能看懂这本书而激动万分。爱因斯坦巨大的创造力和自由驰
骋的思维使他能够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我记得我当时想,有人能这样
做简直太美妙了。我记得他去世的时候(1955年)我哭了。我感到就像失去了一位老朋
友。”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考夫曼即使不是个引人注目的学生,也一直是个不是拿A就是
拿B的好学生。但在这之后,他的热情被点燃了,倒不一定是被科学点燃的。他不觉得
他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爱因斯坦的脚步走。但毫无疑问他感到有了一种与爱因斯坦同样
的想洞容事物内部秘密的欲望。“当你观看一幅立体派油画,看到上面隐在的结构——
那就是我想探索的。”事实上,他对此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兴趣根本就不是在科学方面。
少年时期的考夫曼热衷于当个剧作家,探测人类灵魂里的黑暗和光明。他的第一部作品,
和他高中时的英语教师弗莱德·托德合作写的一个音乐剧本简直“糟糕透顶”。但他对
被一个真正的大人很当回事地来对待而激动不已。那时托德二十四岁,与托德的合作是
启发考夫曼的知识觉醒的很关键的一步。“尽管那不是一部很好的音乐剧,但如果我十
六岁时就能和弗莱德合作写出一部音乐剧来,那还有什么不能做到呢?”
所以当斯图尔特·考夫曼1957年进入达特茅斯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个剧作家了。
他甚至还抽烟斗,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剧作家的话,你就必须
会用烟斗抽烟。当然,他继续写剧本:他与他大学一年级的同屋、高中开始的小伙伴麦
克·迈格雷合作,又写了三部剧。
但很快,考夫曼就发现他创作的剧本的问题:剧中人物发表许多武断的意见。“他
们喋喋不休地探讨生命的意义和怎样才算一个好人。他们只是谈论这些,却没有行动。”
他开始意识到,他对剧本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他剧本中的人物想探索的思想要大。“我
想寻找到通往某种隐在的强大而神奇的东西的通道——虽然我说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
当我发现我的好朋友狄克·格林将要去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时,我感到非常懊恼。我希望
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我当然只能做一个剧作家。放弃做一个剧作家,就意味着
放弃我正在为自己设想的身份。”
他回忆说,他思想斗争了一个星期才想透彻:“我不一定非要当一个剧作家,我可
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所以在后来的六年中,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
当然,他从伦理学开始学起。作为一个剧作家,他想弄明白善与恶的问题。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能学点别的什么呢?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又喜欢上了别的东西。他
的兴趣转移到了科学的哲学和思维的哲学上来了。他说:“对我来说,它们似乎是深透
之所在。”什么是可以用来发现世界本质的科学?什么可以用来了解世界的心智的科学?
在这股求知热情的驱使下,考夫曼在1961年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
继而又获得了牛津大学1961年至1963年的马歇尔奖学金。结果,他没有直接去牛津大学。
“在必须到牛津报到之前我有八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做了唯一的一件理性的事情:我买
了一辆大众车,开着它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我有奥地利圣·安东最尊贵的地址,波斯
特旅馆。我把车停放在旅馆的停车场,整个冬天都使用那个旅馆的盥洗室。”
他一到牛津就发现这儿的环境非常适宜于他。他至今仍然能够数出他这一生中最使
他激动的三个学术环境,牛津便是第一个。“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周围的人都比我聪明。
美国人在那里也是人才济济。有罗德奖学金获得者,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其中有些人
已是很知名的人物了。那时和我们一批的莫德林学院的(Magdalene)戴维·苏特
(David Souter),现在供职于最高法院。乔治·F.威尔(Geofge F Will,美国著名
新闻评论家及专栏作家)和我曾经总是去吃印度餐厅,逃避学院的伙食。”
对科学与思维的强烈求知欲使考夫曼在牛津选择了哲学、心理学及生理学课程。这
些课程不仅只包括传统哲学,而且更注重当代对视觉系统的神经分析和对脑部神经联系
的更为广泛的模拟。总之,这门课致力于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思维的运作。他的心理学
导师名叫斯图尔特·苏瑟兰德(Stuart 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又一位很有影响的
人物。苏瑟兰德喜欢坐在他的书桌后面,连续不断地把问题抛给他的学生,让他们做思
考体操:“考夫曼!视觉系统是怎样区分投射到视网膜相邻的两个锥体上的两个光点
的?”考夫曼发现他喜欢面对这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发现他有能力当场想出各种方
案,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嗯,眼睛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在轻轻移动。所以,也
许当你刺激多个视网杆和视网膜时……”)确实,他承认这样即兴建立模型使他养成了
一种习惯。从此以后,他一直在或这样或那样地即兴建立模型。
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不无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可以即兴建立模型的能力使他放
弃了哲学,趋向某种更为切合实际的方向:医学院。
他笑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的
论点是:我永远也不会有康德那么聪明。而除非你能像康德那么聪明,否则成为一个哲
学家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应该去读医学院。你会注意到,这不是一个推理。”
当真地说,其实是因为他那时对哲学感到厌烦了。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热爱
哲学了。而是我不相信哲学中的某种轻浮性。当代哲学家们,或起码是五十年代和六十
年代的哲学家们,总认为自己是在检验概念和概念的意义,而不是在检验这个世界的现
实。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论点是否中肯、是否得当、是否连贯等等,但却无法发现你是
否正确。这最终引起了我的不满。”他希望做深入现实的探究,希望洞察造物主的奥秘。
“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做爱因斯坦,而不做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
地利籍著名哲学家)”。
更重要的是,他不敢信任自己身上轻浮的弱点。“我始终非常擅长于概念性的东
西。”他说。“往最好的说,这是我性格中最为深刻的一面,是上帝赐予我的天赋。但
往最坏的说,这是圆滑取巧,是肤浅。因为我有这种焦虑,所以我对自己说:‘去读医
学院吧。那些坏脾气的女人生的儿子们是不会让我光耍嘴皮子,到处卖弄知识的。因为
我不得不照顾病人,他们会迫使我去了解大量的事实。’”
事实确实如此。但不知为什么,医学院和病人并没有改变考夫曼喜欢玩思想的习惯。
其实医学从来就不曾真正有机会改变考夫曼。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读过任何医学预科的课
程,所以他就安排自己于1963年秋季去柏克莱大学读一年的医学预科,然后再进入海湾
另一端旧金山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于是,就是在柏克莱,他修了最初的发育生
物学课程。
他被这门课程强烈地震撼了。“这里有绝对令人震惊的现象。”他说。“从一个受
精卵开始,然后这东西逐渐发育,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新生命,然后又变成一个成熟的
生命。”不知为什么,单个的受精卵能够分裂,
![[hp] 复杂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