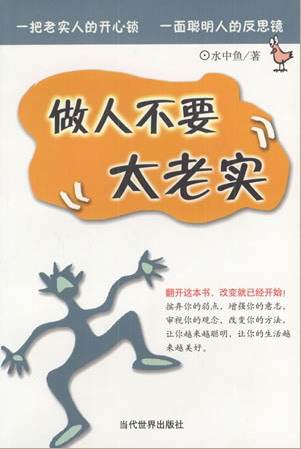曲终人不见--屠隆和他的昙花记-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费振钟其人其事万历十二年,岁在甲申。—道论疏,送到年轻的万历皇帝面前。上疏的是刑部主事俞显卿,目的为论劾礼部主事屠隆。疏中指称屠隆淫纵,说他“翠馆候门,青楼郎署”,言辞不仅有失文臣体面,而且其中媟语还牵涉到勋戚闺帏,万历看后极为恼火,不仅将屠隆贬斥,连同上疏的俞显卿也一起削职。此时屠隆由县官调任京职才一年多,而俞显卿刚中进士授官只有几个月。这次论劾事件,在京城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无论屠隆还是俞显卿,都不过是小小的六品文官,他们的落职对政局绝无任何关联。就两个当事人来说,他们似乎运气不好,正在张居正去世两年、万历皇帝尚有心政事时,如果迟过几年,万历皇帝厌恶朝政,这样的小事,才懒得去管呢,而他们也许不至于两败俱伤。 当时的舆论,似乎有点倾向屠隆,因为俞显卿的论劾,完全属于私人报复。俞显卿未中进士前,是松江的举人,那时屠隆亦在松江青浦做县官,俞有事干谒屠隆,大概屠隆的名士气太大,没有把俞某放在眼里,且言语颇为轻侮。因此俞显卿对屠隆怀恨在心,想不到时间不长,两个人居然同朝为官,这就给了俞显卿—个机会,小人心情,原是睚眦必报的,因此俞一命职刑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击屠隆。本来纠弹官员是监察御史或者是各科给事中职责范围内的事,但俞顾不得了,立刻想借皇帝的权威,要置屠隆于身败名裂。如果这单是“秀才争闲气”,就没有多少深文大义了,也不会对屠隆以后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明朝,情形却又比较特殊,那是个道德政治时代,道德的标准往往被用来代替政治标准,文官体系上下的矛盾,通常都表现为道德上的冲突,这是明代政治的特点。俞显卿为刑部官员虽然几个月,但作为执法者,他是深知这种道德政治的法律威力的,他攻击屠隆的口实,即在于屠隆的个人行为违背了士大夫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这就等于宣布了屠隆政治上的违法。可惜,俞显卿在夸大屠隆的道德过错的同时,缺乏策略,做得太过火,自己不小心也在道德伦理上犯了忌,所以连带着不清不白,遗人笑柄。 诚然,俞显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但屠隆确实也经不起这种道德的打击,不但失去政治前途,终身都不再能振作有为,而且由于此次打击留给他的精神负担十分沉重,屠隆后来一直处在一种道德的阴影当中,直到晚年,犹带余恨和自我忏悔之意。也许,他后来回忆往事时,并不能全怪小人俞显卿的报复,而是要对自己过去的形迹作主动积极的检讨和反省。 像那个时期最容易放纵的文人一样,屠隆在青浦任上过着极为轻松佻达的名士生活。实际上所有关于他为官清明、受民爱戴的记录,都说明屠隆符合士大夫诚心正意、仁民爱物的原则,然而屠隆是极富才情的文人而非只一个良吏,尽管青浦小民百姓一致认为得到了他数年的恩惠,可他们并不了解这位“明府”的真实生活态度和思想情趣。正如屠隆在《出青溪记》中写他当年离任赴京,青浦士民数百人尾随送别至太仓。感动之余,他对送者说: “我在邑无状,何从得此?”屠隆讲的是真话,“无状”当然指他自己公务之外的个人行为,或者说他追求的—种与为官作吏职责无关的个人生活。根据一些野史材料的叙述,屠隆在青浦期间的生活,虽然未必放荡不检,然而却也不是仅仅与当地文人雅士诗酒唱和。他的声名既高,却喜欢与声伎伶人往来,征逐歌舞,甚至不惜籍身其中,尽情享受世间生活中的声色之乐。这种超出一般礼法规范的行动,虽说已在士大夫阶层蔚然成风,但对于屠隆却仍然意味着个人性情对于世俗欲望的沉沦。 从颖上迁官江南青浦,直到万历十年初冬离开,短短五六年,屠隆在这块温柔乡里,最得意最快活的事情,也许真的要算在戏曲上。那时婉丽妩媚的昆曲,已经占据了坊间和缙绅的院堂,青浦与昆山一水相连,应是昆曲搬演最繁盛之地,听曲自是屠隆日常生活重要的内容;不仅是听,还要编传奇,以屠隆的才情也是当仁不让, 《紫毫记》就是那时的作品,据同代人讲,这出传奇里的主人公李太白青莲,即为作者自况;不仅是编,自己还要演角色,“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大概屠隆太喜欢炫耀自己戏曲艺术方面的才能了,所以不惮常常脱了官服扮做优伶。这样的爱好,如果仅仅在江南一隅,那他最多也就是个风流县令,但屠隆几年后又将自己的这份爱好带到了京城,那就不能不引起士林侧目了。 礼部主事屠隆,到京城时间不长,就屡屡在达官贵人的私人堂会上粉墨登场,本来也就为一逞才情,谁知他的即兴串演,得到了一位侯爵夫人的注意和兴趣。她是第十代西宁侯宋世恩的夫人,年轻的夫人有色有才,而且精于戏曲音律。每当屠隆演剧时,宋夫人总是坐在帘箔后面欣赏,有时候乘休息的空儿,让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茗,表达她对他的关心和倾慕。由于侯爵夫人身份特殊,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在当时环境气氛中,多少总有一点暖昧色彩。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种才子和才女的情愫,但是这种出于艺术上的相知相交,却也未必一定表现为男女私情,他们完全可能是清白的。然而世情汹汹,屠隆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士大夫圈子里瞩目的风流人物,何况对方又是一位侯门深宅里尊贵美貌的女性,种种猜测和臆想,出现在像俞显卿一类人嘴里,是可以预料的。对此,屠隆没有作过公开的解释和辩白,也许以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即使在京城这样褒贬最重的地方,也不会放在心上,他心目中的楷模李白,曾经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歌词,杨妃当着皇帝的面亲自磨墨,何曾有过什么忌讳,他自己不就是当世的李白吗?可这是明朝,礼法仍然是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屠隆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睛,西宁侯宋夫人却因这种不同寻常的交往而受到了诽议和伤害。一些情节被夸大渲染了,有关他们的绯闻,在上层社会、缙绅阶层悄悄流传,侯爵夫人带上淫荡的名声,甚至连宫中亦有所察觉。不知在这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中,屠隆是否仍然能保持与这位为艺术爱好而牺牲名誉的女性密切关系,不过随即发生的俞显卿论劾,将事情公开化后,屠隆恐怕想如此也不行。万历十二年的斥逐,使屠隆无法再在京城呆下去,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舞台上与宋夫人眉目传情,在台下品茗谈艺了。一段情愫,一段难得的艺术之缘,因为小人从中作梗,也因为道德政治的威严,不得不被迫中断,从此间关万里,红颜知音难再,屠隆的内心说不清郁结了多少人生的惆怅。 后来十多年,屠隆怎样度过,且省略不问。大概万历三十年晚近,杭州西湖的桂子弥漫浓香,六十岁的屠隆一夕设席招待一班友人,席间令家中蓄养的声伎演出他刚写成的新剧。新剧名《昙花记》,形式上为流行的神仙故事,但其中寓意甚为曲隐,如果不是深知屠隆的人,很难破译。当时在场的有文坛晚辈沈德符,他是万历甲申年屠隆、西宁侯夫人绯闻的知情者,但他也听不懂《昙花记》。小沈问屠隆的老友冯开之:屠年伯《昙花记》曲中的主角木泰清指称谁?冯说,那是宋西宁,老屠想到当年连累了宋夫人,所以作《昙花记》,此曲是老屠的一篇忏悔文也。沈德符恍然大悟,于是在《万历野获编》中,专为《昙花记》的始末作了记叙。 但屠隆忏悔了吗?假如《昙花记》真是为了西宁侯夫人而忏悔,那么这也只能说明屠隆一生中最难忘最珍重的,恰恰是他与一位艺术女性之间那一段艺术情感,所以与其说屠隆是在忏悔,不如说他是迷恋,曲终人不见,但遥远的京城有一双仍然年轻美丽的眼睛,在关注着他,这使晚年的屠隆更加沉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