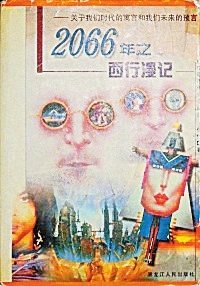3366-绿色安息日-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在附近,我们可以看到绿色丛林里那栋竹子编造的黄色竹屋。我爱这个地方,爱这个河谷!在这可以得到热忱招待的荒野中,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快乐过。绿叶之间充满各种让人身心松弛的元素。我们可以确定,这熟悉的环境仍然是整个生物时钟运转的一部分,自然依旧是主宰。但是,在轻帆船和商用帆船抵达之前,我们必须留意潜伏在周围环境中的不知名的疾病。
我们的小屋就在那里,旁边是没有墙面的厨房,地面仍然泥泞不堪。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地面没有脚印。
但是———多么大的改变啊!
里芙站在我身边,一大片蚊子在我们四周围绕,我们快步走到屋前。正面的墙壁,有一部分已经被冒出头的巨大香蕉叶与其他重新长出的植物遮蔽。这丛林开始以令人难以想像的速度,夺回被我们清理出来的空地。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发现万物好像都要从土里弹出来似的。我们到底是才离开一阵子,还是已经一年了?
里芙用喊叫声响应我,她也注意到我正在注视的东西———我削尖的四根支撑厨房屋顶的柱子,竟然也长出树枝和叶子了!
我试着推开房门,但整个门框已经弯曲。让人吃惊的是,我试着推了一下那面美丽的金黄竹墙,竟然可以穿破,仿佛它是用纸糊成的。我向里头探视,破碎的东西从倒塌的顶端垂挂下来,吊挂得满屋子都是。进入屋内,只见蜘蛛和蜈蚣爬满整片墙壁。竹子的粉尘再度出现,如果我们摸到脆弱的墙壁,粉尘就会掉到头上,像一层层雪花或沙漠中的沙粒,覆盖着我们手工制作的家具、躺椅,以及收藏在屋内的石器、石像和骷髅头。
没有人进来过,我们的考古学和动物学标本都安然健在,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房子可住,只剩下这片丛林盖顶。
我们把那箱头盖骨和其他财产从倾倒的屋里拉出来,希望墙面完全倒下时,这些东西不要被发现。我们在岩石间找到一个干燥的贮藏处,把它们藏了起来。我们祈求此时不要下大雨,以便让我们在屋前的空地上,赶紧用树枝搭成一个粗糙屋顶,上头再盖上伞形叶子。然后,我们很小心地张开那具旧蚊帐,躺在一层厚厚的羊齿植物铺成的席子上。接着,大雨倾盆而下,打在我们四周的黑暗里。
第三部分放弃丛林
清晨来临时,我们全身湿透。雨已经停了,泥泞和蚊虫仍围绕在我们四周。这栖身之所毕竟只是暂时的。我们开始在旧址建造新的竹屋,但同样的事情仍会再度发生。此外,一直待在此地的泥沼中也很危险。我们的腿可能会再染上那种叫“fe…fe”的疥疮,而蚊子也会夹带象皮病的病媒———丝虫———前来。
里芙建议:“我们应该像岛民一样放弃丛林,住到海边,因为那里的风会把蚊子驱散。”我同意了。但是我们必须逃往另一个河谷,因为岛民有很多疾病,我们无法住到海边的村子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们向派奇奇求助,将我们的困扰告诉他。但他只坚持着———他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提欧帝似乎了解我们的心思。他说,如果我们想逃离蚊子,就必须试着翻过陶奥乌何山脉。在这个岛的另一侧,从东边吹来的季风比较强,昆虫会被赶到河谷浓密的灌木丛里。
不管是提欧帝或派奇奇,都不曾翻过山到另一岸去,但是维欧却去过。他向我们确定,那两座山是陶奥乌何山和纳马纳山(Na-mana),彼此相连成一堵巨大的墙壁,把多风的东岸河谷与受屏障的西海岸隔开。哈纳瓦维河谷和哈纳胡瓦(Hanahoua)河谷之间如针孔般狭小的道路已经不通,惟一可使用的通道在中央高原,那里有一条古径曾经切入悬崖地区,一路下达欧维亚(Ouia)。欧维亚是另一岸最大的河谷,山崩虽然把通道冲掉大半,但只要小心行走,还是可以下山。
除了欧维亚,另一岸已无人居住。因为所有部落都已灭亡,所有河谷都空无一人……除了一位还住在欧维亚的老人,他叫泰特瓦(TeiTetua),和养女孤寂地住在一起。维欧见过那位老人。泰特瓦曾经是四个部落的酋长,但是族人和十二名妻妾都已经过世,只有他幸存至今。他在欧摩亚的亲戚把一个叫塔希雅纺纺罚═ahia…Mo-mo)的小女孩送给他做伴。
提欧帝解释:“泰特瓦是过去那个时代惟一还活着的人。”维欧点头同意。老人是祖先辈的人物,是吃过人肉的原住民中至今尚存者。
我们都知道,五十年前,这里还有食人的风俗。1879年,一名瑞典籍木匠曾在希瓦瓦被吃掉。这个岛最后一次的食人记录是1887年,在波茂河谷的一项仪式中执行。泰特瓦已经是老人,他的河谷也被远远隔离在这个岛的另一侧。然而,即使是过去的食人族,孤单时也期待有人做伴。从各种角度考量,另一岸没有别的河谷可以选择,欧维亚是我们惟一可以到达的河谷。没有人能从那里再走到其他地方,因为所有的河谷都被难以翻越的悬崖隔绝。
维欧告诉我们,这个岛的另一岸比较干燥。云层会在陶奥乌何山脉聚集,下雨前会先飘到我们这边。此外,蚊子也比较少。
提欧帝和派奇奇机灵的儿子帕荷(Paho),自愿随我们翻越那座山脉。但是维欧不愿意去。他是我们的朋友中惟一知道路的人。而且即使拿我们从希瓦瓦带回的东西当礼物,也无法诱惑他。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理由。
帕荷突然出现在我们废弃的竹屋前。他说,如果我们送他从希瓦瓦带回的礼物,他会拿去和另一个人分享,那个人知道翻越山脉的路。他没有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名字。
天黑之后,我们跟着帕荷,带着所有财产下山,来到派奇奇的木屋,睡在地板上———一张露兜树皮编成的席子上。
第三部分寻找新世界
当派奇奇叫我们起床时,天空还是一片漆黑,太阳并没有升起的迹象。村子还在沉睡中,我们只听到海浪规律的低沉吼声。朋友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上马背。
提欧帝警告我们,别让人知道我们要搬去哪里。他谁都不相信。我们小声向派奇奇和他热情的家人道别,然后跟着提欧帝和帕荷走。两匹驮马紧跟在我们后头,我们悄悄走到海边。几只狗懒洋洋地吠出声,我们没有看到半个人影。
我们从前往高原的那条熟悉的小径出发。我们在那里碰到了第三位同伴,我们曾见过这个年轻人,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等到我们的马走过去之后,才跟在我们的行列后方。
那天早晨,太阳没有升上来,云层由黑转灰。我们绕着弯曲的小径,穿过熟悉的中央高原上的狭谷与丘陵,能见度才慢慢转好。一到达那里,我们的向导终于走到队伍前头,然后几番犹疑,找到由主要道路岔出去的一条茂密小径,领着我们朝最高的山峰向东而去。我们依循的这条路线,地面经常潮湿松软,难以行走。有一阵子我们穿过一座山林,倒下的树木不时阻挡前方的通路。下午,我们碰到一处竹林,像堡垒般挡住通道。竹茎有粗有细,有黄有绿,有时交叉混杂在一起,一旦被砍倒,像刀刃的边缘就如同刺刀般顶着我们。
提欧帝砍倒一根粗壮的竹子时,被滑下来的竹竿刺中手掌,伤得不轻。里芙坐下来照顾他流血的伤口,用叶子和粗树皮做成绷带为他包扎。她看了一下他的右脚踝,十分震惊,然而她没有停止包扎,只是用眼睛偷偷暗示我。我也看到了———提欧帝虽然穿长裤,但一只裤脚却是撕开的,以便让肿大的腿和脚踝有充裕的空间。他右腿的象皮病症状已经开始扩大,而他一直想要遮掩。我们站起来,继续跟在这位乐天派的教堂执事身后向东走,为这悲惨的发现感到不安,也因此更加了解,远离那一群会造成感染的蚊虫,是多重要的事。
东风猛力吹着,我们抵达一处笔直陡峭的悬崖,下方的深渊是另一个地底世界:欧维亚。马儿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于是我们把它们拴在树干上原地放牧,我们自己则靠着双脚前进。我们砍断马儿拖曳的杆子,把行李背到肩上,开始向上攀爬。岩壁几乎是垂直的,但古人已经在左侧刻了一道狭窄的栈道,我们只有踩在上面才能站稳脚跟。有一部分老旧的栈道因为腐蚀和松动已经坏了,不过向导早有准备,预先带了一支坚固的竿子架在悬空的地方。
我们彼此都坦承十分害怕,但却别无选择。帆船已经离开,我们被送上岸,来到这个没有足够食物的高原,而我们在欧摩亚的家,已经被甲虫和蚊子占领。情势很明白,我们必须克服严重的晕眩,以离开这个悬崖。我们开始向下爬。
下山之前,我们的另外三位同伴,因为即将见到吃过人肉的族人而兴奋。吃人肉对他们多神教的祖先来说是最可怕的罪行,但是他们似乎有共识:吃了不洁之人才有罪,因为会接收被吃者血液中的邪恶。当时所有的人都是多神教徒,而且也都不洁,而人们认为,如果有像基督那样圣洁的人,吃掉他就不会被玷污。提欧帝这位新教的教堂执事因而有段艰难的日子,他曾经说服其他两人(甚至包括派奇奇的儿子),教堂里的耶稣像所以憔悴,只是一种象征,是神爱世人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们来到深邃漆黑的河谷,垂直陡峭的深渊从三个方向包围着我们,我们沿着湍急的河流,穿过一处杂乱的木槿花丛。地面被更多混乱的卵石覆盖,我们必须在没有小径可依循的情况下,尽快前进。途中,整条河流突然消失到地底下。随着我们的前进,地面的石头逐渐比土壤还多。河流突然又在河口附近出现,从岩石之间冒了出来。我们沿着在卵石之间涌动的河流,朝海边前进。
帕荷沿河跑到最前面。远处低沉的猎犬吠声说明,不用再走太远,老人的木屋已经到了。
河谷慢慢变宽,很快就明亮开阔起来。波光粼粼的海面旁,厚厚的树丛围绕着一个椰林海滩。太阳再次冒出头来,我们深吸了一口从辽阔大海吹来的清爽海风。就在右边,高耸的椰林之间,我们看到一排被太阳晒得焦黑的低矮木屋,那是利用木材和茅草搭盖的老式波利尼西亚建筑。我们也看到了那位老人。
老人泰特瓦奔跑起来像年轻的山羊,肌肉结实,身手敏捷。他看来饱经风霜,全身被晒得黝黑,身上什么都没穿,只在腰间系上一个树皮制成的阴茎袋。他似乎只有实际年龄的一半大,露齿而笑,脸上充满了快乐活泼的神情,他的牙齿像我们床下藏的那颗骷髅头的牙齿一样健康。我向他伸出手,说了一句土语:“你好!”他抓住我的手笑着,局促不安,像个害羞而说不出话的孩子,整个人压抑的能量几乎要爆发出来。经过多年的孤寂,他似乎无法表达想说的话。
最后,他大声宣布:“吃猪!猪吃完了,我们就吃鸡。鸡吃完了,我们就吃更多的猪!”
第三部分在食人族河谷
泰特瓦像个孩子般左蹦右跳回到木屋,对着他驯养的长毛半野生猪大声吼叫。在帕荷的帮忙下,他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