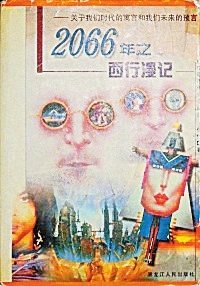3366-绿色安息日-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能过得比我们更富有、更美好?拿任何城堡和我家交换,我都不愿意。新鲜的竹子日渐成熟,菠菜色的竹墙变得如诗如画,墙面的绿色中出现一点点金黄色,如同变色龙一般,像生活中使用的艺术壁纸。我们打开竹窗,欧摩亚谷地的所有景致呈现在眼前,好像一座皇家花园。
没有手表,就没有那种一小时、一小时过日子的感觉。时间是靠太阳、鸟叫声和我们的肚子来判断。时光并没有离我们而去。日子很漫长,或许是因为处于这个对我们而言全新的环境中,我们不时在改变。我们永远都不觉得无聊,因为每一天都充满新的观察和体验。
日后,我回想起在法图希瓦岛度过的日子,相较于“正常的日子”,那一年好像有二十年那么长。
第二部分天堂的滋味
引人入胜且色彩斑斓的马克萨斯杜鹃鸟,在昏沉沉的丛林中醒来,发出响亮的长鸣,那一刻,正是一天的开始。其它鸟类也开始欢乐大合唱,没有片刻休止。鸟儿从河谷各个角落一只只加入,发出不同的音调,诉说不同的爱情故事,让我们不得不快乐地起床,接收这充满旋律的晨间曲目所传达的信息,就像是歌剧院里灯光为了演出而渐灭时所演奏的序曲。黎明突然温和地降临,仿佛不想立刻叫醒我们。逐渐明亮的阳光穿过敞开的竹窗,赶走昨夜冷冽的晚风。当阳光完全照射进来,温度随即从冷冽转为宜人。穿过整个山谷的如黑龙般的山峰原本很壮观,在黎明时分却转为通红,如同从火焰里跃出来似的,也像晨曦中的一朵鸡冠花。有时,丛林的歌者会让歌声节奏转强———我们屋外空地上的各种昆虫很容易被鸟儿察觉,许多鸟儿似乎受到诱惑,叫声变得更为清脆。长得像鹦鹉的杜鹃鸟,身体蓝得如天空,交杂着鲜黄与青绿色,它们偏爱我们窗外那棵面包树的嫩叶;椰子树上,则充满娇小而聒噪的歌者,那是聚在一起为数颇多的金丝雀。
晨曦开始沿着竹帘移动,这一天,没有任何时刻能和清晨的第一个小时相比,此时的大自然最为安详、灵活,而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稍后,所有生物因为太阳逐渐上升而变得懒洋洋的,太阳正用它的光芒为这热带森林的皇冠赐福。天气并没有热得让人难受,从东方吹来的季风带走了迟滞不动的热气,使大地变得清爽。正午时刻也没有热得让人没有活动力,这和气压有关,因为某种力量移走了所有不必要的热能。在欧摩亚谷地,热,并未让我们感到困扰。
当黎明音乐会的声音渐渐减弱,我们起床走到泉水边。我们经常被一头美丽的野猫惊吓,它可能是本地种的远亲,习惯和我们一起享受这股泉水。我们坐在池塘里,有时对水深不察,让水浸到眼睛,使得周遭景物看来格外美丽。我们意识知觉的波长似乎变得不同了,而且接收得更清楚。我们用鼻子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时,就好像是孩子们正在见证奇迹。有些事每天都会发生,例如一片绿叶上的露珠正要滴落,我们让水珠溅到手中,看它们如宝石般在晨光中闪耀。没有任何一颗人工琢磨的宝石,像这颗阳光中的液体宝石般明亮而可爱。我们是富有的,可以用手捧接它们,让它们从指缝间化为千万颗小水滴,然后消失不见,再从岩石间不断流出。在我们脚下韵律舞动着的溪流,也是一颗宝石,它引诱我们摘下粉红的木槿花,让花朵在水中漂流,在卵石之间翻动,再跳进一道小小的激流中。它们是前往大海的信差,像是魔术师的大锅,孕育所有的生命;也是源源不绝的清净器,清洗河口那个丑陋的村庄,再把水送上天际,回到我们这道隐秘的泉源。
享受过泉水的沁凉后,我们把脚放在薄薄的沉淀黏土上,伸进柔软的泥沼,或是踩进干硬而温暖的土块中,那种感觉真棒!我们这些来自寒带地区、正在打扰此地热带岛民的白种人,身上穿的衣服就像湿透的纸张,紧贴在太阳曝晒过的肌肤上。这里气候宜人,我们舒服得想脱光衣服,就像丢掉鞋子一般,这让我们感觉很愉快。我们的鞋子从泥泞走到尖锐的火山熔岩,从石子路走到小径,经常需要修补。脱掉衣服和鞋子,我们顿时感到自由与热切之情倍增。我们新生的身体起初很柔弱,像爬虫蜕去外壳后,躲起来等新皮肤变硬。然而这座丛林也慢慢收回魔爪,当我们经过时,感觉叶子和柔软的树枝正友善地拍打我们。感受微风、阳光,接触森林,比起不管走到哪里都穿着衣服的感觉好得太多了。我们从冰凉的草地踩到灼热的沙地,感受脚趾间挤揉的烂泥,然后到旁边的水池中冲掉,那种感觉,比一直把脚套在同一双袜子中来得好。我们被包裹在整个宇宙中,只觉得富裕,毫不感到贫穷和赤裸。我们与万物,都属于自然。
第二部分丛林美食
我们住在这个河谷最富裕的地带,周遭的富裕反映出人们已经成功驯服了荒野,不必试图清理环境,就可以得到广阔整齐的农园。没有用处的树木已被各种有效益的物种取代,散布在位置与土壤都适合的地区。耕种者已经不在了,他们所驯服的丛林则残存下来,但那不代表打败敌人的荣耀,而是一种对人类努力的纪念。这里的原住民已经死去,并非死于和大自然之间的战争,而是死于白人想让原住民接受的文明。
我们两人———被城市豢养的动物———要在丛林里存活下来的机会很小,惟有靠着岛上先人的赐福。这里的土壤不断供应食物,除了昆虫和动物,甚至没有人会来收成。我们背后的森林,有一部分是由大量的香蕉树和红山蕉组成。这两种植物很难区分,除非长出果实。它们都是翠绿植物,树干多汁,像大型花卉的茎,直径相当于一个大盘子,也都有高高成束且如皮革般的叶子,像椰子树般探向天际。不过红山蕉靠近根部之处,很明显地带有一点红色。而从果实来看,香蕉成束的果实呈绿色或黄色,吊挂在树干顶端,像是树木的装饰灯架;红山蕉成束的果实则向着天空竖立,好像圣诞树上的星星。
如提利尔卢所料,大溪地最珍贵的红山蕉或山芭蕉,几乎都生长在难以接近的悬崖上;而在法图希瓦岛,我们家的四周却到处都有,成了我们最喜爱的主食。它们在尚未成熟的时候不能吃,可以先在炭火上烧烤,再以磨碎和挤压过的乳白椰汁沾着吃。椰浆是我们仅有的烹调用油,有多种用途,可以用于厨房烹调,也可以当化妆品。制作方法很简单:使用锯齿状的贝壳来研磨它的外壳,然后放在一把椰子纤维里加以扭曲,把椰仁碎屑挤出来。黄绿色的红山蕉沾了椰浆,比烤香蕉还要甜,风味绝佳,让我们百吃不厌。除了红山蕉,这森林还提供我们七种不同品种的香蕉,有小而圆的品种,有像小鸡蛋而带有草莓香的品种,还有大得几乎像手臂的马儿蕉,烤过之后的味道像烤苹果。
要找到一串吊挂在树上的熟香蕉,是十分难得的事。我们寻找的时候,常常像是在捏一只中空的手套:因为香蕉已经被一种吃水果的小老鼠吞食,或是被爬虫和黄色的小香蕉果蝇侵蚀掉了。不过,我们可以采食的香蕉数量很多,只要在香蕉快变黄时摘下来,再随意挂在窗前的面包树上,等几天让太阳把它们晒熟即可。与因应经济需要而栽种的香蕉相比,它们的味道无与伦比,前者为了防止在运送期间变坏,往往提前几星期采收而影响风味。
香蕉太高,摘取不易,不过,至少我不必爬到滑溜溜的香蕉树干上。虽然看来像长着硬皮叶的大型椰子树,香蕉树其实只是巨型的草,有着男人大腿般粗的茎,但却柔软得像洋葱。我用弯刀一砍,树干就立刻倒下,成串香蕉落地。而剩余的树茎看起来就像切割过的葱,几天后树茎环状内层就会长出来,其他内层也会慢慢向上长。两周之后,残余的树茎看来像是绿色的花瓶,中央长出一段细长的叶卷,像人一般高,绿色的卷叶伸展开来后,就像是一面旗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株全新的香蕉树会把残余的树茎塞满,一串新生的香蕉会出现,等着人们再次采收。
新的香蕉树从原来的旧干上再生长出来,速度看来很快,却不显眼,然而,只要过些时候再观察,必定让人大感惊讶,甚至害怕。人的肉眼无法看出植物的成长。在自然界,成长速度的定义往往介乎自然与奇迹之间。靠这些植物维生几个月之后,我开始把大自然当作魔术师,而时间就是魔杖。但是,当时间神奇的支配力不再加诸我们身上时,魔杖也消失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到底是什么幻术在困惑我们。每天早上我打开竹帘时,仍可以看到被我亲手砍伐过的某棵香蕉树干还在同一个地点,但树干内部似乎有看不见的心在吸收和输送养分:从地下吸收黑色土壤,再反地心引力把它推送到天空,重新定型,变成一棵巨大的植物,然后在树顶悬挂一串沉重而可食的香蕉。香蕉很快就会再长出来,高挂在我们头顶上方。
我对那些在店里卖香蕉给我的人,从来不抱感恩之心,却对这棵活生生的植物产生了感情。它很努力地从树干上供应我一整串免费的香蕉,如果我砍下它,它随时准备再长出新的。香蕉在被我视为智能的发现之前,只是一种经过卫生包装的可口食物,随时可以剥去外皮送进嘴里。
在每天的餐饮中,椰子几乎和香蕉、红山蕉同等重要。马克萨斯群岛的椰子树据说是世上最高的,而且大多高得让我无法摘取椰子,幸好它们总会自动落到地面。我所需要花费的力气,不过是用木橇扭开坚硬的外壳。如果椰子掉到地上没人管,几星期后就会长出一棵小椰子树———从壳里冒出头来,就像小鸵鸟从蛋里探头出来,而它的根会反向试图寻找土壤。这并非奇迹,而是染色体和基因造成。同样的土壤可以让树干长出香蕉,让一旁的小椰子变成高耸的椰子树,真是耐人寻味。
一整年里,大多数可食用的植物提供给了我们坚果和可食块根。而果树中的柳橙、酸橙和柠檬还开着芳芬甜美的小白花时,也会并生成熟的金黄果实和未熟的绿色果实。只有巨大的面包树是特例,有一定的生长季节。这种重要的树木由于树干太粗壮,使我无法攀爬,除非先爬上比较低矮的树枝。它的果实大得像孩子的头,掉到地上后会变软并散发出香气。如果想要食用面包果,我会用竹竿摘取。岛民通常把面包果贮藏在地下洞穴,等到非结实季节,再把发臭的果肉拿出来研磨成生面团,那种味道几英里外都可以闻得到,不过却很好吃。我们比较偏好把新鲜的面包果拿到篝火堆上烤,直到它坚硬的外壳迸裂开,再用手指把白色的果肉剥开,吃起来的感觉像综合了吐司面包和烤新鲜马铃薯的味道。
我们的厨房是一个石砌的灶,上方有椰子叶搭成的防雨屋顶,由四根柱子支撑着。里芙可以在这里烤一种叫芋艿(taro)的山芋,那是种可口的植物块根,由前人引水注入沼泽种植,现在就在皇后泉的下方湿地上野生野长。大型的心形叶让我可以辨识出哪里长了芋艿。混在它们之中的,还有一些叶子更大的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