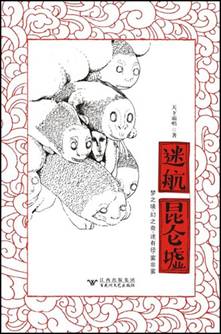鲜花的废墟-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来我们又有几次听过弗拉门戈;每次都有所感触,也都多少获得了那种幻觉。但是无论哪一次都取代不了科尔多瓦的印象。内行的人指点说,上一次你看的是baile,这一次你见识的是cante。以后,你还会遇到真正的pena。
我们打听拜尼亚(pena)。
人们告诉我们:拜尼亚,是一种弗拉门戈艺者圈内的,艺术家自娱和交际的内部聚会。一般来说不相干的人是进入不了pena的;但是,如果你的运气好,他们一旦开门接受了你,那么你就能看到与商业演出截然不同的弗拉门戈。pena哪里都有,他们常常在门上挂一个标志。但是要注意,弗拉门戈的现状也和其它东西一样,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宰富骗人的赝品到处充斥着,很难遇到一处真的。
果然很难进入。去格拉纳达前曾有朋友拍胸脯,说给我们介绍。所以满以为会在一些拜尼亚里谈个水落石出呢,但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这样转到了加的斯。一天傍晚,正沿着海边散步,突然看见一栋房子,门上钉着一个蓝色小牌,写着pena。
敲了好一阵门,但没有回应。
对弗拉门戈的研究汗牛充栋。多少带有官方气味的书上说:它的渊源不易穷究。但可能它与印度的一脉;也就是与吉普赛人的艺术有着关系。但别的著作却反驳:为什么遍及欧洲的吉普赛人都没有这种东西,唯独西班牙﹑而且唯独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才有弗拉门戈呢?可见源头不在吉普赛,而在安达卢西亚。吉普赛人是到了安达卢西亚以后才濡染风习,学会并发展了弗拉门戈的。如下的观点大概是公允的:“安达卢西亚和吉普赛,是载着弗拉门戈的两个车轮。”但是把吉普赛人说成弗拉门戈起源的观点,总使我觉得含有政治目的——若是德国荷兰起源说立不住脚,那就印度起源、哪怕中国起源也没关系。反正别让这块西班牙的招牌,又刨根刨到见鬼的阿拉伯那儿去。
这样的心理,潜伏在西班牙的弗拉门戈研究的水底。“吉普赛”、“印度”,都是一种中性暧昧的说法。它可以在弗拉门戈的东方特质上虚晃一枪,然后再甩开纠缠不已的阿拉伯文化。吉普赛至少还算基督徒,印度至少不是穆斯林——如是煞费苦心的观点,遮掩不住西班牙的官方学术,面对八百年安达卢斯穆斯林文明时的,那种深刻的自卑。
于是我开始想象。
我所做的,只是一个以想象为主、兼顾其它的下里巴人考证。
被我东拉西扯当做根据的,有一些因素就不多赘述了:比如弗拉门戈歌手演唱时的耸肩膀﹑拖长调。须知,前者的味道和维吾尔人的音乐表演如出一辙;后者则与蒙古草原的歌曲处理非常近似。再如家族性、小圈子,还有它的咏叹歌与北亚游牧民族在唱法上的相似,等等。
弗拉门戈一语的词源,也不容易弄清楚。
学者们使劲把这个词说成一个天外来物,甚至猜它是一种鸟叫的拟音。我总觉得这种考证不怀好意。因为传统会留下古老的印迹,其中称谓就是一个深印。究明这个词的含义不该太难,难的无非是不能断言。里奥斯?鲁易斯(M。RiosRuis)著《弗拉门戈入门》记录了明快的解释可能: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felamengu,即“流浪者”一词的读音接近。日本人永川玲二新著《安达卢西亚风土记》支持这个倾向,把这个词解释成“逃奴”:“弗拉门戈一词,与阿拉伯语逃亡奴隶一词的发音近似。”
阿拉伯语动词“逃亡”的词根far…,确实可能派生出许多这一类词汇。但是,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阿拉伯人对地中海以北没有主张文化著作权的兴趣。所以对这一阿拉伯语词的判断,得不到他们的权威认识。虽然这个词汇提示着——弗拉门戈可能与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悲剧有关;但就一种可能性而言,猜测只能到此为止。
当我听说,最初的弗拉门戈,是一种只在家庭内部﹑或者处于半地下状态的艺术——我便留意,不轻易放弃自己的预感。
为什么只在家族内部?为什么处于半地下状态?难道它传到吉普赛人手里以后,不就是为了公开和演出么?还有那主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才需要这样一种几乎绝对的“苦歌”(gaxiūdaō)?……
还有神秘的pena,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拜尼亚不是演出团体,拜尼亚是一个内部的圈子。什么是内部的圈子?它的封闭习惯,会是因为伤痛得不愿示人么。我感到深深的兴趣。以表演弗拉门戈著名的多是一些家族,也许这暗示着它的某种血统纠葛。这种内部传统吸引着我,我直觉这不是为了给艺术保密。pena,它会不会就是“半地下时代”的现代版呢?或者多少继承了那时秘密圈子的遗风?拜尼亚的原型,古代的拜尼亚,它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隐瞒自己排斥外界的、少数族众的圈子?如宗教组织、如秘密团体一样?
在圈子里举行着秘密的仪礼?或者这圈子干脆就是为了闭门大哭嘶吼而设立?……
抑或都不是;它就是要诱人烦恼走火入魔,它就是要隐去真事取笑后人?或者它完全没有那么神秘,它不过是吉普赛的吉他手和刚达斡尔们一起喝喝咖啡、度过轻松时光的聚会而已?我提醒自己:愈是对它的重大内涵留意,就愈是要注意它的完全相反的一面。或许不过如此:吉普赛人来到西班牙,创造了弗拉门戈。它异色异香,专门演给外人观看。Pena只是区区一种行规,并无什么神秘可言……
——这样写过,我就不用为夸张自己的感觉而不安了。我把多数者的通说告诉读者,留下一点疑问自己暗中咀嚼。
只是一种旧式的行规么?还是一种隐秘的仪式?
无论如何,摩尔人的音乐,包括吉他——曾把西班牙领上了一个高高的音乐台阶。先是奢华的装饰和绚丽的色彩,是女奴造成的诗歌风习,是科尔多瓦的巅峰感觉。后来,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走遍安达卢西亚几省,也找不到当年杏花如雪、女奴踏花吟诗的一丝痕迹了。如今在安达卢西亚能遇见的,只是“弗拉门戈”。它在莫名其妙地、空若无人地嘶吼。一句句地叠唱,单调得如同招魂。
Pena,pena……Diosmio痛苦……痛苦……我的主啊
Tengoyounagrandepena我有一个巨大的痛苦……
虽然我不过只是猜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但我想,弗拉门戈的摩尔起源,将会被证明不是一种无稽之谈。逻辑还引导我进一步推测——它的圈子与摩尔人内部结构的关系、它的歌词与特殊念辞的关系。考据它的细部将很费事,但推翻它的逻辑同样困难。我想,虽然还不能逐一实证,但提示已经足够醒目。
这些提示人人皆知;只是,人们大都喜欢遵循旧说,而不去反省自己的思路——过去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今天还是迫于恐怖的压力——不过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本来只打算写写对弗拉门戈的感受,结果却陷入了对它源头的纠缠。都是由于它那古怪的魅力,它揪扯着人不由自主。说实话我真是被它迷住了,甚至幻想——没准儿从这里出发,能探究到歌的某种本质。
第四章 自由的街巷第14节 自由的街巷(1)
(1)
那个老外瞪圆了眼,好像我的摩洛哥日程是缺心眼儿和变态。“你不去菲斯?你没听说过菲斯?那么你为什么要去摩洛哥?”但不管她怎么瞪眼,我虽惭愧也只能坦白地再说一遍:“哪里是菲斯?我真的不知道。”
如今回想着,自己在哑笑摇头之外,依然琢磨不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实在不容易。菲斯?中国人谁都知道,既便是摩洛哥,大概我们也顶多在中学的世界地理课上听老师念到过一次。或者听相声演员的顺口溜里念叨过。它是不毛之地还是富比英美,它是白人还是黑兄弟——我们中国人一概不知。仗着一部美国电影,不少人耳际有了一个“卡萨布兰卡”的曲子在缭绕;但情迷卡萨布兰卡并不意味着知道摩洛哥在哪儿,更何况莫名其妙的菲斯。
我没有这个雄心。除非改造中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否则没办法讲清楚菲斯。谁能在一篇小文里,既有大西洋地中海的形势,又有罗马帝国和阿拉伯的历史;既有情调浓烈的生活,又有它在民族之林中的位置?
这事还是留待未来。
有趣的是,当我将信将疑地,把路线改向菲斯,并且真地去那儿转了一圈儿回来以后——我几乎马上就盼着再去一趟。虽然面纱仍然对我遮着,我对它的了解和老外朋友瞪眼时差太多——但我已经被它迷往。它如一块有魔法的磁石,吸引着人心想念它。身体没有向它靠近是由于国界的障碍;灵魂因为响往神秘和美,所以控制不住地倾倒于它。
(2)
顶多说说这城市给人的感觉。不,也许我的意思是说说建筑。也不,我是想说说那些魔法建筑组合以后的外观,它们的平面布局。还不,我像一切浅薄的游客一样,只是被它那错综无限、百徊千转的天方小巷弄得迷迷糊糊,像吃了蒙幻药,像醉在那摄人的阿拉伯情调里。
我被凭空扔进了深渊。阿拉伯的平顶屋彼此拼砌嵌挤,那真是“栉次鳞比”,夹缝处自然出现了一条小巷,又一条小巷。
我的眼睛因为目不遐接疼痛了;蜿蜒变幻的小巷两侧,每一个洞开着望着我的都是铺子。每一栋小屋小楼,每一个门面窗口,都是铺子,铺子,铺子。
夺人眼目般闪烁的是金碧辉煌的镶嵌细工。紧排其次的是挂满四壁的彩画陶盘。炉火旺处香气四溢的不知是什么佳肴小吃,还有香料、毛皮、绸缎、富士胶卷、经书、木器、摩洛哥袍子、麦当劳、铁器、染坊、银行支店、小学校、经学院、清真寺、美丽的双眼皮大眼睛、沿单行线踱步的毛驴、瞟着你的银髯老匠人、三两交谈的阿拉伯姑娘、不可思议地在小巷里飞奔穿梭的下了课的儿童——唉,世间的众生万物,都在这无法辩认更何从记住的、纠缠叠加恰好如文字所谓“一团乱麻”的密巷小街之中,像河水分流注进了无数的沟渠,喧嚣着,流动着,生机蓬勃地活着……
我被这流水般的巷子冲涮裹胁,顺流而下,仅一会儿功夫便完全迷失了方向。我的脑海是白茫茫的,不会思想,只会兴奋。这么奇妙,这么不可理喻!要知道这不是一小块残留的老城区,整个菲斯古都原色原形式地维持着这种中世纪风貌。来前知道了它是世界文明遗产之一;但我没有想到,这处文明遗产不像中国那些已经彻底变成“遗产”的名胜古迹——菲斯旧城包括人们今天熙熙攘攘的生活本身,都一同被列入人类文明的奇观,被列入保护的名单之内。领路的摩洛哥青年(幸亏有这么一个朋友!他是木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我的兴奋表示满意,但他强调说:“要知道最不可思议的是:旧城在今天仍然是商业中心。”
我跟着他一拐弯,又进入一个七八条小巷汇聚的芝麻大小的广场。眩目的铜器在灯光下晃闪着,飞窜的小孩背上的书包在一掀一掀。铺子,铺子,铺子,只有你的筋疲力尽两腿酸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