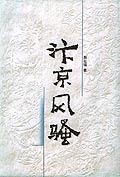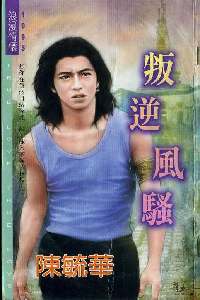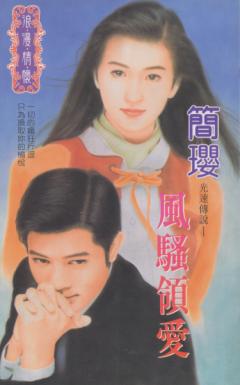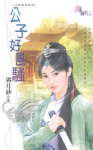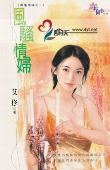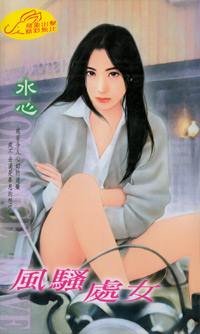独领风骚-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段多么悲壮的行程呵。
历史更需要“从头越”。往前看,依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里没有一览众山小的灵透豪迈,只是茫茫的山海和血红般的落日。
山海茫茫,茫茫谓之浩阔。浩阔征程且看路遥知马力。
落照殷殷,殷殷谓之悲壮。悲壮革命应是疾风知劲草。
面对未来,诗人的感受,竟如此深邃而又遥远。
面对未来,诗人的联想,竟如此沉着而又回环。
第三部分青山作证(1)
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
在同斯大林会谈时,他说起中国红军艰苦奋战的情形,使用了一句中国成语: “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翻译不解其意。毛泽东补充说: “就是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来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似乎是听懂了,他小声对翻译费德林说:“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在西方人的眼里,长征中的毛泽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熟读《圣经》的西方传记作家说,他很像《圣经》记载的那位 “摩西”。
摩西,古代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奉上帝之命去埃及带领希伯莱人脱离奴隶之境,法老却给他设置了数不尽的障碍。他带领人们一路与敌人作战,在漫漫旷野上跋涉,走向上帝耶和华给他们指定的地方—迦南。于是,在后人的想象中,摩西成为带领人们脱离苦海,走向幸福和光明的人。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很有些像一部划时代的“神话故事”。
在这一点上,东方中国的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确有些像摩西。他们率领红军走向中国的“迦南”—延安途中,遭遇的困难和挫折,一点也不比摩西少。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没有上帝的庇护,他们所依靠的,仅仅是自己的信念和意志,还有让整个世界惊叹的生命力。
更不同的是,中国的“摩西”还在长征途中写诗。
长征中的毛泽东,最真实的形象是什么?
如果还是借用西方人的观察,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风度细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
这位战略家手中的地图,画满符号的地名,似乎总是山。
在中外历史上,带领一个政党、一支衣衫褴褛的军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生死攸关地在崇山峻岭穿行的诗人和战略家,是异常罕见的。
1934年10月从江西出发以来,一路上,总是山连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雄,一山更比一山险。
山,几乎成了红军官兵生活的一部分,成了红军官兵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实在的敌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也成了诗人毛泽东的灵感源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这三首以“山”为题的《十六字令》,不是具体地写哪一座山,是一种虚写,写诗人在长征中对各种各样、各姿各态的山的总体感觉。
诗人感觉到山的高耸。剽悍神速地打马越过之后,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座山离天才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诗人感觉到山的壮阔。在对山的一种横视中,仿佛连绵起伏的巨浪奔马。这不正是对“苍山如海”的一个形象注脚吗?
诗人感觉到山的陡峭。陡峭不是一般的高,而是险挺,是尖锐,尖锐得像利剑一样刺破了青天。
追日月,“马作的卢飞快”。
射天狼,“弓如霹雳弦惊”。
无论是高耸、壮阔还是陡峭,都是诗人在马背上飞驰获得的感觉。
通篇未写一人,但处处皆人。不正是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国革命赖以支撑的擎天巨柱吗?
山,成了跳动的火焰,成了离弦的响箭,成了奔涌的狂澜。
一路上,毛泽东偶尔是“马上低吟三五句,灯前速记六七行”。诗人的气质,将军的风骨,长征的内蕴,就这样融进了对群山的感觉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后,随红一军团行进的毛泽东,先后翻越了二十多座大山。
在江西境内,有大庾山脉的支脉雷岭。
在广东境内,有五岭山脉的支脉苗山、大王山、小王山、大盈山。
在广西境内,有湘桂间的要隘永安关和瑶族地区的白茅隘。
第三部分青山作证(2)
在贵州境内,有娄山关和五岭山支脉紫金关。
在四川境内,有入川的主要隘口小相岭、大相岭,彝族扼守的冕山、雪山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以及荒无人烟的拖雷岗、腊子山,高原草地分水岭。
在甘肃,有朵扎里、岷山、六盘山。
穿行在这崇山峻岭之中,绝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在诗人笔下,那些像战阵,像利剑的山峰,虽然被看得不在话下,可事实上,每一个当事人在这些自然山水的阻隔面前,决不会有亲近可爱的感觉。
当红军借助明月或打着火把,在若明若暗的夜色中跋涉的时候,盘根错节的乱石,或令人战怵的悬崖峭壁,都仿佛张着血盆大口在寻找机会吞噬这支奇异的军队,更何况还有那些前堵后追,比陡峰深谷更凶恶的敌兵。
毛泽东后来在解释《忆秦娥·娄山关》时,还说了这样几句话:“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心情。”
这里说的“以下诸篇”,就是《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有意思的是,这几首,都是写的山。
毛泽东对山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
在《毛泽东诗词集》收入的67首作品中,以山为题和写到山的,就有三十多首。他的代表作,大多是以山为题材。
因为他这时期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人们称他为马背诗人,就是这个意思。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辉煌,是从“山里”起步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是靠着对山的跨越和曲折前行而走向成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随后,分左右两路北上。
但是,分裂的危机又开始逼近这支“摩西”率领的队伍。
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坚持南下。在无法说服张国焘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率领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9月12日,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甘肃俄界把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随后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了岷山。
革命老人吴玉章曾回忆说:过岷山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我们很快登上了岷山的山顶,从山顶远望山下的田野,牛羊成群,农民在田间辛勤劳动,大家很愉快地像潮水般涌下山去,到了大草滩宿营地。在回、汉族人民的热诚欢迎中,我们很快进入了村子。”
这正是毛泽东后来说的,过岷山以后拥有的那种“豁然开朗”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心境。
翻越岷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毛泽东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读到一张报纸,意外地发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和面积不小的苏区。那里离这里只有七百多里路程。毛泽东当即决定:到陕北去,实现北上抗日、创建根据地的目标。
长征的落脚点这才最终定了下来。
这对一年多来饱尝艰辛、且战且走,选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落下脚,不免有四顾苍茫之感的红军来说,有什么能比这个消息和决定更让人高兴呢?
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文中这样回忆:
“一天,我们从甘肃环县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便遇到刘志丹同志派来给主席送信的人。主席看过信,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了!……’主席的话还没有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同志们高兴地笑着、跳着、互相搂抱着、欢呼着,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
中央红军的长征就要结束了。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诗来记述这一年多来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第三部分青山作证(3)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不用雕琢,只是拿红军长途跋涉的脚印,把万水千山串在一起,就构成了一首诗。
虽只有五十六个字,虽只有一年的跨度,记录的时空内含,却有着世界历史上最罕见的沉重和遥远。
这首《七律·长征》,除山之外,还写了两条“水”—金沙江和大渡河。
长征中的红军曾飞渡过近二十条江河。谙熟历史的毛泽东选择金沙江和大渡河入诗的时候,头脑里或许闪着两个令人难忘的名字—诸葛亮和石达开。
在《三国演义》里,金沙江被称为泸水。这一带,即使在春天便已酷热难耐。毒气聚于江水之中,泅渡或饮用,都会中毒。诸葛亮在四五月间南征时,部下马岱率军渡泸水,不知此情,折损了一千多人马。后来在当地老乡指点下,才在夜静水冷之际安全渡过。
毛泽东和红军过金沙江,正好和诸葛亮的南征是同一个季节,于是便有了“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感觉。
说起大渡河,人们自然要想起石达开。就在红军抢占大渡河的7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人马,在这里全军覆灭。于是,蒋介石的飞机也向红军撒下了“毛泽东将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
令毛泽东和红军自豪的是,大渡河的历史也没有重演。
惊天地、泣鬼神的漫漫长路,文字已无法记载它的艰辛和悲壮,无法尽数它的残酷和凄凉。
那里有爬不完的大山,渡不完的大河,还有似乎永远走不到头的草地,永远看不到顶的雪山。
长征是什么?
红军官兵靠野菜和皮带充饥。
多少战士被敌人的机枪打下了万丈深渊,打进了湍流翻滚的河谷。
沼泽吞没了他们的躯体。
风雪把他们凝成了永恒。
长征是什么?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
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尼笔下,长征是“前所未闻的故事”。
在艾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
这就是长征,两万五千里路的长征。
它需要何等惊人的智慧和毅力才能走完?!
红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跨越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