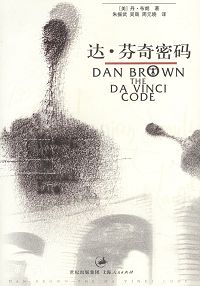哈克贝里·芬历险记 作者:马克·吐温-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后我走了回来,坐下来说:
“别嚷啊,就这样静静地坐好,要象个男子汉一般对待这一切。我得把真相告诉你,你呢,得鼓点儿勇气,玛丽小姐,因为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叫人难以忍受的事,但是事已如此,是无可奈何的了。你们的这些叔叔啊,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叔叔——他们是一伙骗子——地地道道的大流氓。啊,如今已经把顶可怕的事端了出来了,——其余的话你便能受得住了。”
不消说,这些话对她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不过我呢,仿佛鱼游过了浅滩,我便继续说下去。我一边说,她眼睛里发出的光越来越亮。我继续把这些为非作歹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她,从我们第一次遇到那个搭轮的年轻傻瓜讲起,一直讲到她怎样在大门口投进国王的怀抱,他吻了她不下十六七回——这时她跳将起来,满脸通红,仿佛烧得象落山的太阳。
她说:
“那个禽兽!来——别再耽误一分钟——一秒钟——我们要给他抹柏油、撒羽毛,把他扔到河里去。”
我说:
“那当然。不过,你难道是说,在你到洛斯罗浦家去以前便动手么?——”
“哦,”她说,“你看我在想些什么啊!”一边说,一边又坐了下来。“别见怪我说了些什么——请别见怪——如今你不会见怪,不会了,是吧。”她把那柔滑得象绸子一般的手搁在我的手上,这份情意就是叫我去死我也是愿意的。“我从未想到我会这么激动,”她说,“好吧,说下去,我不会再这样激动了。我该怎么办,你尽管说。不论你怎么说,我一定照着办。”
“啊,”我说,“那可是一帮穷凶极恶的家伙啊,这两个骗子。我事已至此,非得跟他们一起走一程,不管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至于是什么原因,我暂时还不能对你说——你如果告发他们,那这个镇子上的人,倒是会把我从他们的爪子下搭救出来,可是这里还牵涉到一个你不知道的人。他可要遭殃啦①。唉,我们得搭救他啊,不是么?当然是这样。这么说来,那我们还不必告发他们。”
①诺顿版注:指黑人杰姆,参看24章末了的记叙。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生一计。我想到了我和杰姆怎样摆脱掉那两个骗子,并且叫他们在这里便给关进牢狱。不过我不想在大白天就划木筏子,因为这样的话,除了我,就没有别的人在木筏子上回答盘问的人,因此我不愿意把那个计划在今晚深夜以前就开动起来。我说:
“玛丽·珍妮小姐,我会告诉你我们该怎么办——你也不用在洛斯罗浦家耽那么久。那里离这里有多少路?”
“四英里路不到些——就在后边那个乡下。”
“好啊,这就行了。现今你可以到那边去,耽到今晚九点,或者九点半,不要声张,随后请他们送你回家——对他们说是你想起了什么一件事这才要回去的。要是你在十一点以前到,在窗子上放一支蜡烛,到时候我如果没有露面,等我等到十一点,随后如果我还没有露面,那就是说我已经远走高飞啦,已经脱身啦,已经平安无事啦。随后你就可出场了,可以把信息在各个方面传开来,并且把这些败类关进牢狱。”
“好,”她说,“我会照着办的。”
“万一我没有能走掉,跟他们一起被抓住,你务必挺身出来,说我是怎样把事情的全盘经过在事前就告诉了你的,你务必竭尽你的全力站在我的一边。”
“站在你的一边,当然我会的。他们决不会动你的一根毫毛。”她说。我见她说的时候鼻翼微张,眼睛闪着光亮。“要是我走成功了,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说。“不会在这里为这些流氓并非你的叔叔这件事作证。如果我到时候还在这里,我也无法这样干。我能宣誓证明说这是些败类,是痞子,我能做的,仅此而已。尽管这还是有点儿价值的。可别的人也能这么干,并且干得比我更强——他们这些人一出场就不会遭到怀疑,和我有所不同。我来告诉你怎么找到这些人。你给我一支笔和一张纸。就这样——《王室异兽》,勃里斯克维尔。把这个藏好,别丢了。一旦法院要弄清这两个家伙的事,让他们派人上勃里斯克维尔去,去对镇上人说,你们已经抓住了演出《王室异兽》的家伙,要他们前来出场作证——哈,不用你一眨眼的工夫,全镇的人会涌来作证,玛丽小姐。而且他们准会怒气冲冲地赶来。”
依我看,我们已经把事情一桩桩一件件都安排好了。我因此说:
“不妨让拍卖就这样进行下去,不用担什么心。拍卖以后,人家在整整一天之内,不用为了买下的东西付现款,因为通告的时间太局促了,他们在取到钱以前无法付款——依照我们设下的方案,拍卖不会作数,他们也就拿不到钱。黑奴的事和这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买卖,黑奴不久也就会回来。哈,黑奴的钱,他们是到不了手的——他们可陷进了最糟的困境啦,玛丽小姐。”
“好啊,”她说,“我如今先下去吃早饭去,随后径直往洛斯罗浦家去。”
“啊哟,那不成啊,玛丽·珍妮小姐,”我说,“这绝对不行啊。吃早饭以前就走。”
“为什么?”
“依你看,我要你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玛丽小姐?”
“嗯,我从未想过啊——让我想一想。我不明白啊。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因为你可不是那种脸皮厚厚一层的人啊。要是我念的书能象你的脸一样,那该多好啊。人家一坐下来,就读到粗黑的铅字体,看得清清楚楚的。依你看,你难道能够见到你叔叔,你叔叔来亲你,说声早安的时候不露——么?”
“对,对,别说啦!好,我在吃早饭以前就走——我乐意的。难道让妹妹跟他们在一起?”
“是的——根本不用为她们担什么心。她们还得忍耐一会儿。要是你们都走了的话,他们说不定会起疑心。我不要你见到他们这些家伙,也不要见到你的妹妹,或是这个镇上的任何别的人——要是今天早上一个邻居问起你叔叔,你的脸啊,会说出点儿什么来。不行,你还是径直去吧,玛丽·珍妮小姐。至于其余的人,我会一个个安排好的。我会让苏珊小姐替你向叔叔们问候的,还让她们说,你要走开几个钟头,好小小休息一下,换一换环境,或者是去看一个朋友,今晚或者明晨就会回来的。”
“去看一个朋友,这样说是可以的,不过我可不要向他们问候。”
“好,那就不问候。”对她这样说一下,那就够了——这样说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小事一桩,不会惹什么麻烦。可往往只靠一些小事,便能清除人们深层里的障碍。这样一件小事能叫玛丽·珍妮小姐感到舒服,却又不用花费什么代价。随后我说:“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那袋钱的事。”
“啊,他们拿到了手啦。一想到他们是怎么样搞到手的,我觉得我是多么傻啊。”
“不对。你可不知情哩。他们并没有搞到手。”
“怎么啦,那么在谁手里?”
“我但愿我知道就好了,不过我并不知道。钱曾经在我的手里。因为我从他们那儿偷了过来。我偷来是为了给你们的。我也清楚我把钱藏在什么一个地方,不过我怕如今不在那里了。我非常难过,玛丽·珍妮小姐。我实在难过得无以复加,不过能做到的我都做过了,我都做过了,这是说的实在话。我差一点儿给逮住了。我不得不随手一塞塞好,拔腿就跑——
可塞的不是个理想的地方。”
“哦,别埋怨自己罢——光埋怨自己,那太不好了,我不准许这样——你也是无可奈何嘛,这不是你的错嘛。你给藏在哪里啦?”
我并不愿意让她又想到自己的烦恼。我仿佛张不开嘴来对她说些什么,以致叫她仿佛见到棺材里躺着的尸体,肚子上放着那个钱袋。因此,我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随后我说:
“我宁可不告诉你我把钱放在哪里的,玛丽·珍妮小姐,如果你能不追问我的话。不过我可以为了你起见,把这写在一张纸片上。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去洛斯罗浦家的路上拿出来看。你看这样行么?”
“哦,行的。”
我就写了下来:“我把钱袋放到棺材里了。那天你在那儿哭的时候,也就是在当晚,钱还在棺材里。当时我躲在门背后,我也替你非常难过啊,玛丽·珍妮小姐。”
写着写着,我眼里也流了泪,我想到她怎样深夜只身一人哭哭啼啼,可就在她自己家的屋檐下,这些魔鬼正住在那里,叫她丢丑,掠夺她。我把纸片折好递给她时,看见她眼睛里也热泪盈眶。她用力握住我的手说:
“再见了,——你刚才对我说的话,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会照着做。要是我再也见不着你了,我也永远不会把你忘掉,我会一次又一次,无数次地想你,我会为你祈祷。”——
说过,她飘然而去了。
为我祈祷!我看啊,要是她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的话,她就会挑另一件和她更般配的事去干。不过我敢打赌,话虽这样说,她还是为我祈祷的——她就是这么一类人。只要她打定了主意,她就有胆子甚至敢为犹大祈祷哩——我看啊,她身上没有软骨头。尽管你爱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不过据我的看法,她是我见到的姑娘中最有胆量的人了,她浑身是胆。这话听起来仿佛是过于奉承的话,其实并非如此。要是说到美——以及善——她就比人家高出一头。自从我亲眼看到她走出这道门以后,我就从没有再见到过她了,不过我想念到她的次数啊,我看恐怕有千百万次了吧。还不时想到了她所说的要为我祈祷的话。要是我认为,为了她祈祷会对我有点儿用处的话,我死活也要为她祈祷啊。
是啊,依我看,玛丽·珍妮是从后门溜走的,因为并没有人见到她走开。我见到苏珊和豁嘴时,我说:
“你们有时候全家去拜访的河对面那家人家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们说:
“有几家哩。主要是普洛克托斯家。”
“正是这个名字,”我说。“我差点儿把这忘了。玛丽·珍妮小姐要我告诉你们,她急急忙忙到那里去了——有人病了。”
“哪一个?”
“我不知道。至少是我忘啦,不过我想是——”
“天啊,但愿不是汉娜?”
“真对不起,”我说,“恰恰正是汉娜。”
“天啊,——她上个星期还身体好好的嘛!她病得厉害么?”
“是叫不出名字的病。玛丽·珍妮小姐说,人家陪了她整整一个晚上,还深怕她拖不过多少时间了。”
“到了这么个地步啊!她究竟得的什么病呢?”
我一时间想不出什么一种合理的病,就说:
“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别瞎扯啦!得了流行性腮腺炎,也不致于要人整夜守着啊。”
“不用守着,是么?你不妨打个赌,对这样的流行性腮腺炎,人家是要整夜守着的。玛丽·珍妮小姐说,这是新的一种。”
“怎么新的一种?”
“因为跟别的病并发的。”
“什么些别的病?”
“嗯,麻疹、百日咳,还有一种非常厉害的皮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