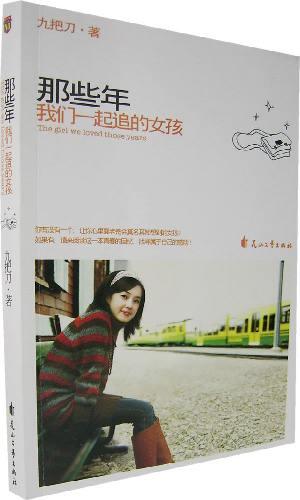这些年,二哥哥很想你-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蛮感伤的啦,不过…
「爸,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养狗?」我忍不住。
「爸爸考虑看看,如果你们成绩好,就有商量。」爸说。
真是千篇一律的烂答案啊!
父母拥有各式各样的筹码,但最喜欢小孩子拿来交换筹码的东西,就是成绩。
想要那套漫画? …家里那套百科全书都看完了吗?拿出漂亮的成绩单吧!
想要新脚踏车? …旧的那辆已经不能骑了吗?拿出漂亮的成绩单吧!
想要跟同学去南投玩? …去八卦山难道就不能玩?拿出漂亮的成绩单吧!
总是这样的。
很不幸,我们三兄弟的特色,就是成绩非常的烂。
烂到什么程度呢?
先说我好了。
上了国中,我就与数学结下不解之恶。
国一共六次月考,数学没有一次及格,全校排行总在倒数一百名内,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我非常不用功,将所有的时间都投资在画漫画上面罢了。
大哥的功课也是烂到化脓,烂到我无法只提一次。
二哥哥很想你5
成绩佷烂的我哥
哥大我两岁,当我正忙着把成绩搞砸的时候,他也不遑多让。
他在高中联考时拿了诡异低的分数,低到在彰化完完全全没有一间学校可以念。
哥的表现狠狠吓了大家一跳,因为亲戚大人们都觉得哥是三兄弟里最聪明的一个,读彰化国中三年,也算连续拿了三年的好成绩…现在可好,联考搞到没有学校可以填,谁会相信?
爸在地方上算是头脸人物,大哥那张算是白考了的联考成绩单把家里的气氛弄得很低迷。妈很沮丧,还被外公打电话骂,骂她怎么会让聪明绝顶的我哥考成那个样子。爸则非常生气。
哥每天都躲在楼上房间不敢下楼,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会逼不得已出现。我也不想被台风尾扫到,非不得已才会下楼。
算是为了处罚大哥,爸几乎每天都命令大哥洗他的裕隆牌吉利青鸟,每次都要冲水、淋泡沫、再冲水,最后用专用抹布仔细揩干车身每一寸,直到整台车闪闪发亮。
而成绩同样很烂的我也得帮手,非常无奈。
「你现在怎么办?要去考五专吗?」我擦着轮胎圈。
「我不想念五专。」大哥蹲着,拧抹布:「我想念高中,考大学。」
「去念五专不行吗?」我没概念。
「念五专的话,以后想读大学还要绕很大一圈,我不要。」哥叹气,将抹布浸在水里,不自觉又拧了一次:「有时候我想干脆去重考算了。凭我的资质,再考一次一定可以上彰中。就算是台中一中也没有问题吧!」
大哥有重考的念头,但爸认为搞砸了联考的大哥根本没有重考的资格。
三年都可以混掉了,多一年又能怎样?
还不是照样混。
我永远记得那天中午,天气很热,热到让人从心底慌了起来。
那天,爸原本要带哥去见私立精诚中学的教务主任说项,请精诚中学能提供多余的名额让哥进去念。但距离爸说好要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的中午时刻,愠怒的爸却躺在店面后的椅子床,将湿毛巾放在眼睛上,一言不发,完全没有即将起床的迹象。
没有人敢去叫他。
怎么办?到了最后关头,妈示意大哥自己走到床前,叫装睡的爸爸起来。
自觉罪恶深重的大哥拉着我,我们一起走到爸的跟前。
「爸,时间到了。」大哥小声地说。
「…」爸没有反应。
大哥用手肘顶我,我只好小声地说:「爸,时间到了。」
「什么时间到了?」爸慢慢说道。
「去精诚的时间到了。」大哥鼓起最后的勇气。
「去精诚做什么?」爸的声音很慢很慢。
「去…帮我讲入学的事。」大哥的声音在发抖。
「自己做的事,自己要负责。」爸粗重的声音不加掩饰他的愤怒:「自己想念书,就自己去说。如果没有学校念,就去当兵。」身子连动—都—没—有—动。
听到当兵,大哥虎躯一震,我也傻了眼。
看样子,爸这次是百分之一亿没脸为大哥说项了。
大哥跟我头低低地上楼,连妈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现在怎么办?如果不快点说,就来不及注册了。」
我打开冰箱吹冷气,逼退刚刚瞬间冒出的大汗:「你真的要去当兵吗?」
大哥像是下定了决心:「你帮我说。」
「我帮你说?」我吓了一跳。
「对,你帮我开个头,接下来我自己说就可以了。」
「找谁?」
「教务处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就去那里。」
「真的假的啦!」
「我现在就只剩下这个方法了。」
说着说着,我们已经骑着脚踏车,跨过烈日下的中华陆桥,往精诚中学前进。
只是大哥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只是个即将升国二的学生!
「喂,我们回家啦,我怎么知道要说什么?」我渐渐后悔。
「拜托啦,你不帮我,我就要去当兵了啊。」哥看起来一副快被抓去关。
「可是我自己的成绩也很烂啊,那个教务主任还教过我最烂的数学,完全就知道我很差劲,唬烂不过他啦!」我快崩溃了。
「那个不要紧啦,最重要的是,诚意!」哥说归说,也没有自信。
终于来到暑假期间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务处,所幸教务主任还在里面办公,我鼓起勇气,走向教务主任自我介绍,大哥则彬彬有礼地跟在我后面。
教务主任平时就一脸严肃,现在看起来,更是略带杀气。
但没办法了。
「主任好,我是美术一年甲班的柯景腾,导师是郭焕材。」我鞠躬。
「嗯,有什么事吗?」教务主任摸不着头绪。
「我的哥哥叫柯景怀,今年刚从彰化国中毕业,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只是联考失常考坏了,现在没有学校念。我想请主任给我哥一次机会,让他来精诚读书。」我背出刚刚在脑中写好的稿子:「我相信我哥在精诚中学里,一定会表现得很好。」
「考坏了?考几分?」主任问。
但他的表情更像在问:怎么就只有你们兄弟?
身为事主的大哥再怎么孬种,此时当然得挺身而出。
「主任您好,我是景腾的哥哥,虽然我的分数不够,但我很想念精诚…」
大哥用很有家教的语气,滔滔不绝开始了属于他的入学谈判。
就这样,以严肃著称的教务主任听着我们兄弟接力完成的恳求,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平淡,到最后哥说完了他的自我期许,只能用「漠然」两字形容教务主任五官的排列组合。
「你家人知道你们来这里吗?」教务主任叉着腰。
「知道,只是今天我爸妈正好有事,所以我们兄弟自己过来。」大哥说。
「这样啊…」教务主任若有所思。
仿佛隔了很久。
「我们的自然组已经满额了,如果你想念自然组的话,就没有办法。」教务主任的语气出现松动。
「没关系,我可以念社会组,之后再想办法转班到自然组。」哥毫无犹豫。
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了教务主任的口头承诺。
大哥即将进入精诚中学的高中部!
只不过我们兄弟成绩这一烂,养狗的梦想又过去了…
二哥哥很想你6
家教老师家楼下的贱狗
话说人真的很矛盾。
明明我很想养狗,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怕狗的人。
只要在路上远远看到流浪狗,我就会提高警觉,只要它走右边我就走左边。
我什至绝对不介意多绕一大圈,只为了避开与流浪狗的眼神交会。
有几次我因为太害怕而拔足逃跑,反而引起流浪狗的野性,对我暴起直追…如此一来我当然只有更加害怕的分。
国二的时候,为了拯救快要跟我绝交的数学,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我都会到一个数学老师家上一对一或二对一的补习。
有句话说得很刻薄:「人要是穷,就不要生有钱人的病。」转个意思就是,人要是笨,就不要发聪明人的梦。我们家负债一堆,但我爸妈做了一个我们三兄弟都有好学历的梦,烧掉的补习费跟中元普渡烧掉的一样多。
补习费很贵,贵到没一次我敢缺席,话说数学老师住在彰化女中对面的小巷子里,有两个非常漂亮又极为聪明的女儿,跟一个喜欢只穿内裤跑来跑去的儿子。
大女儿跟我同岁,经常会跟我一起上课算题目,每当我连一题都没算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解完十题以上开始发呆,严重对比出我的蠢。
有时候连小我一个年级的二女儿也会过来一起上课,她听完了可以直接演算题目,但我还在那里红着脸假装有听懂一些。
…这段的重点是,数学老师家住在公寓四楼,但一楼邻居喜欢在楼下铁门拴上一条叫「豆豆」的混种大狗。
那只豆豆,很贱,非常喜欢从喉咙深处,对我发出充满敌意的低吼。
如果豆豆正好被它没良心的主人带出门散步,我就会开开心心跑上楼补习。如果豆豆在楼下张牙舞爪,我会得在豆豆的恐吓声中冒险逼近对讲机,向楼上的数学老师求救。
「老师,我不敢上去。」我强自镇定,假装这种事理所当然。
「喔!没问题,你等我一下。」老师总是善解人意。
等到老师下来扯住豆豆脖子上的链子,要我赶快从旁边走到楼上时,豆豆就会装出一副温良恭俭让的表情,仿佛我的害怕完全是我自己孬种。真的很贱。
「景腾啊,豆豆不会咬人啦。」老师拉住狗时,总是这么微笑。
「…真的吗?」我讪讪歪着身体。
有时,是老师的漂亮女儿按下了通话钮。
「请问找谁?」甜美的声音。
「呃…我是来补习的柯景腾。」我恐惧地看着豆豆那快要发狂的狗眼。
「喔,快上来啊。」
「可是…」
「可是什么?喔!你是说豆豆吗?」
「嗯,它想咬我。」
「哈哈哈它不会咬你啦。」
「…」
「好啦好啦!我下去喔,你等我你等我。」
然后大女儿就会下来,似笑非笑地拉住豆豆的颈绳,制住它。
「你看,它只是想跟你玩啦,它根本就不会咬人。」她拍拍豆豆。
豆豆正舔着她的手,温顺到了极点。
我百口莫辩,只能微笑鬼扯:「大概是我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里或多或少都有阴影吧。」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什么事都归咎给童年时期的创伤效应,真是太方便的逃避。
只是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真的很赌烂。
老师的大女儿要是很丑也就算了,但她实在很漂亮,被美女在补习课上重创我的智商也就罢了,还在胆子上胜我一截…这叫每个礼拜定期收看《魁男塾》的我情何以堪?
有一次周日补课,豆豆不知怎地被拴在楼下更前面的地方,让我连靠近对讲机的机会都没有。
我只能远远看着豆豆匍匐在地上,像一把涨满凶煞的弓,酝酿等我靠近,便一鼓作气将我的大腿咬爆的力量。
「喂,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贱。」我很气,在脚踏车上不敢下来。
「呜…吼…」豆豆蓄势待发。
「只会凶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种你见人就咬啊!」我的背脊全被冷汗湿透,而我的怒气也越来越盛。
「呜…吼…」
没有丝毫进展,我们就这样持续对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它恐吓,我发抖。
「好,你完蛋了,我不补习都是你的错!」
终于,我气急败坏,骑着脚踏车掉头就走。
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一脸大便,疑惑说:「田田,老师刚刚打电话给我,问我你怎么还没有去补习,我就说你已经去了啊,应该一下子就会到了…」
「都是那只贱狗!」我将背包重重放下,完全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它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