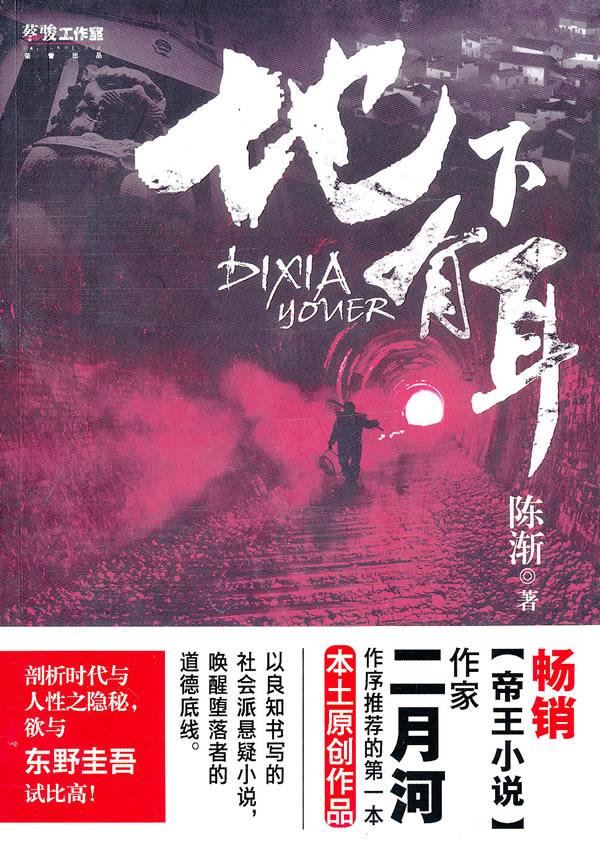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是不是把家属接到您这里来比较好些呢?真的,斯特罗卡奇同志,您把这件事安排一下吧。关于飞机,我会下命令的。费多罗夫同志,您对这样的决定觉得满意吗?好,就这样吧……您去准备袭击。什么都不要忘记。”
我们就这样分了手。
两天以后,我在中央飞机场上见到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女儿。
带便说说,她们肯定说,虽然我已骇人地变了样,还穿着不可思议的游击队员的皮袄,可是她们早已在飞机的窗洞里便认出了我。她们还说,踏出飞机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右颊颤动的象个电报键。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值不值得相信她们。
不久以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了莫斯科。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切尔尼多夫地下省委的一年半的工作和我们游击联队的战斗活动的报告。
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员会决定把我们的联队分成两个部分,派一部分到西部乌克兰去从事大规模的袭击。
第一章 向西前进!
一九四三年三月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接见了我和联队政委德鲁日宁,我们的谈话是最后的临别会谈。我们街道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简单、扼要而又确切地指示了我们今后若干月中的任务。
这道命令的要点是这样的:
联合游击队司令员费多罗夫同志、联队政委德鲁日宁同志、侦察队副指挥员索洛伊德同志、巴列茨基同志、卡瓦连柯同志将飞往敌人的后方,在游击活动地区着陆。万一飞机不能降落,须跳伞着陆。
……到达工作岗位后,立刻着手准备队伍在德涅帕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发动袭击,为此将实行下列措施:
甲、由最优秀的成员来组织一支队伍,并须留下必要的人员在切尔尼多夫省工作。
乙、留在切尔尼多夫省的工作人员要在尼·尼·波布特连科的指挥下,组成一支独立的游击队。
……在司令员费多罗夫同志、政委德鲁日宁同志、参谋长尔凡诺夫同志指挥下的游击队组成后,应立即开往德涅泊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发动袭击……而后的目标就是进军沃伦省地区。
游击队司令员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德涅泊河涨大水之前把部队带到右岸去。
……部队到达沃伦省地区后:
甲、在布列斯特-科维里-鲁茨克、霍尔姆-科维里的这两条铁道干线上,组织有系统颠覆敌方开往前线的列车,并在布列斯特-科维里的公路上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装备。
乙、要和在沃伦省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因此须组织派遣侦察组和侦察员……
丙、应进行瓦解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工作。
丁、组织独立自主地活动的游击队。
德鲁日宁和我都已经知道,我们的联队预定要分成两个部分,同时我们也已知道,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会派遣我们向德涅泊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袭击。不久以前,伏罗希洛夫和我谈话时,曾建议要以我们联队的力量来牵制敌人后方的一处重要的铁道枢纽站,不让敌方的军车开往前线。现在这道命令就是要我们开始行动了。说实话,我到现在才全面地认识到党所指望我们游击队打击的范围和勇敢性。
赫鲁晓夫是在旧广场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座大楼里接见我们的。是一个冰寒的日子,窗玻璃上挂满了霜花。窗外看不大清楚的树顶上堆满了积雪。但是赫鲁晓夫谈论的却是春天的事情,并且警惕着我们不能完成任务的危险性。
“到达目的地后——马上就进军,气象学家曾预测春天会来得早一些。当德涅泊河开冻涨水时,就不容易渡过了。一天都不要延迟。党现在在你们游击队员身上寄托着重大的希望;党非常信任你们。”
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在和我们谈话之前不久,曾经参加过国防委员会的会议。
“你们不仅是去袭击,”赫鲁晓夫同志继续叮咛道,“有些人已经接到,另一些人很快就会接到与此类似的命令。这一春天,有好几支强大的队伍要出发到我们祖国西部的边境去。所以不用害怕鼓励了。这是一种特殊的袭击,过去的游击运动是从来不知道这种袭击的。这样的袭击也许可以更正确地称之为我们游击军的突破。在靠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森林地区和山岳地区,正在建立广大的游击区。斯大林把你们游击队员叫做我们的第二战线。把这道战线转为攻势的时期已经来到了。今后党和统帅部不仅要估计到游击队的力量,而且要把它列入总反攻的作战计划中。”
我对德鲁日宁看了一眼。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和我自己的感觉是一样的:“原来这道命令的意义是这样的!”
作为游击队司令员和地下工作者的我们,在不久以前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什么是攻势,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部队是应该深入敌占区呢,还是更靠近前线,以便经常有可能援助红军部队,从后方打击敌人。我们只知道一种游击攻势的形式——袭击。游击队竭力避免和敌人进行有预计的战斗,而只给予出其不意的打击。猛袭一下就马上走开,一直隐藏到下一次袭击。我们的运动和袭击几乎经常都是被迫的。当敌人对我们集中起扫荡部队时,我们就即使退走;当探悉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时,我们便卷土重来。杰尼斯·达维多夫的游击队员们曾经这样作战过,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波尔人曾经这样作战过,我们的前辈——红色游击队员们——在国内战争时期也曾经这样作战过;这种战术是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
但是时间在改变,战术也在改变。组织性、目标的一致、统一的指挥——这就是今天游击运动的特征,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德寇占领区进行斗争,党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把从人口稠密地区崛起的零散的大小支队联系起来,并且掌握了它们的领导权。现在党派遣自己游击军最精锐的部队去进攻了。党要以新的装备来武装他们,而且在他们面前规定新的战略任务。
“费多罗夫同志,您到过西部各省吗?”赫鲁晓夫问道。
“没有。”
“那么您呢,德鲁日宁同志?但是,我记得,战前您曾在铁尔诺波尔工作过。这很好。您的经验曾帮助您了解那边的情况。在切尔尼多夫的支队里十分通晓沃伦、罗温什那的人,恐怕连十个人也找不到——而这些地方正是你们现在所要去的。”
“我们将会吸收当地的居民来帮助我们,”我说。
赫鲁晓夫思索了一下。
“这样是对的,”他慢慢地接着说。“不过当地居民须要你们帮助更迫切得多。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赫鲁晓夫看了看手表以后补充道:“我不再久留你们啦。除了你们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听到的一切,除了你们接到的各种指示以及命令而外,我只想补充一点:你们行动的时候要密切联系群众,不可脱离群众。德寇正在企图利用乌克兰劳动人民对波兰小贵族的世仇。占领军当局在布里巴夫分子和本杰罗夫分子以及其他狐群狗党的协助下,已经建立了民族注意派的组织,并且挑起了兄弟的自相残杀——唆使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或者唆使波兰人反对乌克兰人。这就是德寇为什么在那里感到自身相当安宁的原因;这也就是德寇为什么取道科维里铁道枢纽站一昼夜能向前方运送达七十列车军火、装备和人员的原因。我们要给当地居民指明,他们的敌人在哪里,而把乌克兰和波兰的游击队都组织起来,并且跟他们在一块儿,依靠他们来切断敌方的供应线——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同志们,祝贺你们成功……”
在我们居住的莫斯科大饭店的两个房间里,逐渐地积累了不少武器和弹药。那儿还有一箱子勋章和奖章,最高苏维埃委托我把这些勋章和奖章授予我们联队著有功勋的游击队员们。
我们一分钟也没有撤去我们房间门口的警卫人员。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还得经过我的或者德鲁日宁的许可,才能让外人进来;甚至连收拾屋子的也不许进门。我们总是自己打扫。总之,建立了游击队的秩序。
可是自己人,就是游击队员们——游击队医院里快要恢复健康的队员们、游击训练班的同志们、其他联队派遣到莫斯科来的代表们——却聚集得很多。
一到夜间,我们的房间便异常嘈杂起来。不过,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已习惯于夜间作战,习惯在黑暗的掩护下转移。夜间是游击队员的同盟者。月亮是游击队员的太阳。
而在这儿莫斯科大饭店里,我们经过一天的奔波之后聚集在一起,刚开始谈话,就有人敲门:“不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同志们请离开这里吧!”
叫他们退到哪儿去呢?游击队医院是在列宁格勒大道上,要是步行到那儿去,至少也得一个钟点。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把夜间通行证发给我们。只好对值班管理员解释说,这里是我们的游击地带。不用说,我们是不随便听从莫斯科大饭店的管理处的。
这层楼的值日员旋过身去,一面走一面嘟哝道:“你们到什么时候才飞走啊?!”
这不过是他们生气的时候才这样做的。一般说来,他们经常是很殷勤地招待我们,并且很关心我们的。
关于“什么时候飞走”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比莫斯科大饭店里的那些职工还要关心得多。三月三日,我们终于应该起飞了。可是飞机场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天别想乘飞机动身了。我们还是坐了汽车上了飞机场。我们想用这种手段来感动航空师的指挥官们。不济事,我们回到了旅馆。职工们已在我们的房间里举行了大扫除,虽然天气很冷,却把窗户都打开了。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飞走以后,我们房间里的黄花烟味经过好几个月才消失掉。
三月四日,我们终于接到了通知,说是有飞机了,同时气象预测员虽然不很乐意,但还是允许我们起飞了。这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急忙布置了临别的午餐,和经理处告了别,跟一些严厉执行旅馆纪律的人也和好了。甚至有几位服务员还到飞机场去给我们送行呢。
我们坐上飞机,起飞了,在莫斯科上空盘旋了一圈……又着陆了。
他们给我们解释了好一会儿,说是北极风刮到了某地,又说是“在我们应该飞行的航程上的明度不够……”
这些话能使我们安静吗?我竭力沉住气问气象学家:“小伙子,您能不能保证正是这阵北极风延 在德涅泊河开冻呢?”
气象学家觉得受了委屈,说他并不是一个小伙子。这并没有改变情况。飞行还是延期了。
神经已经再也忍耐不住。我记得,由于烦闷,我曾经斥责过给我们送行的一位很好的同志。他过去原是我们的一名游击队员,是位指挥员——起先是支队的、后来是中队的指挥员。而现今留在莫斯科,接受了新的任务。的确,他不太健康,虽然两脚受伤以后在医院里已经治好,可是他的一只耳朵仍然在化脓,一条腿有些瘸——腿还有些痛。可是我认为,而且并不是凭空地认为: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