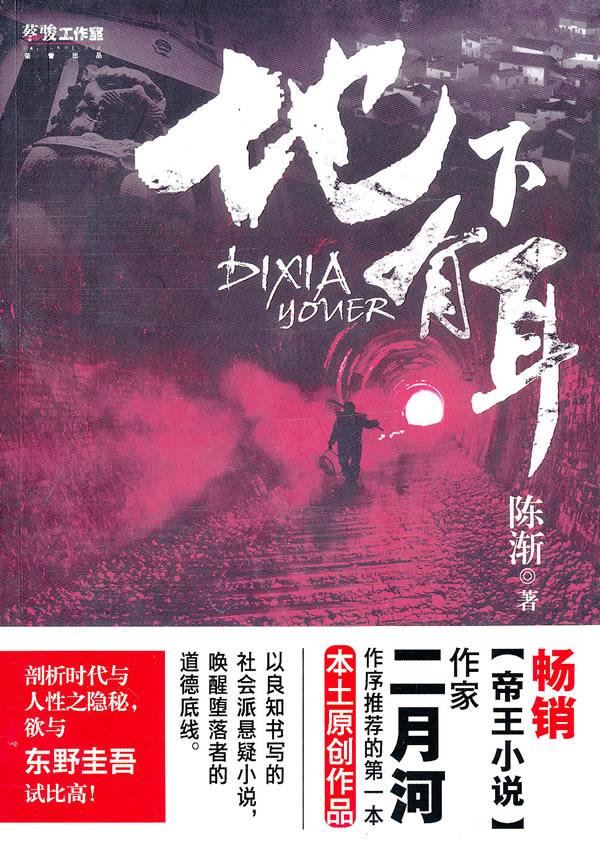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九四二年五月和六月中,我们的破坏工作人员翻毁了二十六列军车,其中巴利茨基小队却干掉了十一列。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们在一九四二年的破坏战不过是小小的、学徒式的企图而已。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组织,到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情形就不同了。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按照图表来行动,在一天之内翻毁了军车将近十列。可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强有力的打击。
然而,我们的破坏工作人员毕竟做了不少工作。三月里,这时积雪还未融化,他们便从叶林诺森林出发到离营地几十公里的铁路道基上去,在冬季的艰难情况下,一连等上好几昼夜火车。那时因为大雪,交通几乎完全停顿了。破坏工作人员不得不执行自己所不喜欢的工作——他们管它叫“粗工”的爆破作业桥梁、铁道路基和涵洞等工作。
但是,这也使侵略者的经济遭到重大损失。在三月里和四月初,我们的弟兄们炸毁了五座铁道桥梁和三百多公尺的铁道路基。当然,这四百公尺并不是全在同一个地点,而是一小节、一小节地在不同的地点。
五月里,我们驻扎在兹林卡和诺夫兹勃科夫森林时,离开铁道比较近,能够干得更多。这时冰雪消逝了,火车也正常地来来往往。每天经过哥美里——布良斯克铁道线开往前方去的火车多至六十列。而我们破坏工作队出动以后,德寇不得不完全取消了夜车的运行;日间也开始只开八列,最多不过十列。
飞机开始给我们投送茶褐炸药和硝氨炸药以后,支队里对“爆炸工作”的嗜好更加厉害了。现在支队攻击任何大小的居民点时,我们的爆破手们便把工业企业、动力战和安置在石头建筑里的仓库破坏得一干二净。
在戈尔捷耶夫卡区中心的历时不过半小时的战斗中,当其他中队和分队进行战斗时,破坏工作人员炸毁了酒精厂、炼油厂、发电厂、粮食仓库和几辆卡车和拖拉机。
在科留可夫卡,破坏队的弟兄们也在一次作战中完全摧毁了火车站。他们拆断了二十四处铁轨,破坏了所有的岔道和转辙机、通讯和信号的设备,炸毁并烧光了锯木厂、木材堆栈、燃料和饲料的仓库。
从飞机飞到我们这里来的那时起,洁净的纸张变得十分珍贵起来。有些同志甚至同意出让一撮足够卷一支纸烟的黄花烟来换一张信纸。同志们写了许多信,希望总有一天会降落一架飞机来把邮件捎走。
现在大家拿全部空闲时间来写信。可是飞机却没有降落。许多人积了成束的信,就象整本的书一样。我读过几封这样连篇累牍的信。我选出了我们勇敢的破坏工作人员之一的华洛佳·帕伏罗夫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讲到自己初次跟小组出去爆炸火车的经过。
华洛佳那时还不满二十岁。他战前在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一年纪读书。你要知道,他在我们这里也研究一些运输问题;然而不是研究铁道建设,也不是研究铁道管理,而是加以破坏。
现在,帕伏洛夫是苏联英雄,转到原来的学院的五年纪去了。他很快就会造桥了。
我在下面摘引的这封信是从华洛佳那里挑出来的。他在信里报道了太多破坏工作上的“技术性”的详细情节。当然,现在这封信已经没有军事秘密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四日
我亲爱、宝贵的妈妈!
我不知道哪天会给你寄出这封信,或是就这样一直搁在口袋里……记得你向来喜欢详情细节,要我描述环境状况。我是在帐篷里写这封信的;不过,它不是象你在军营里或儿童团夏令营里看见过的那种普通的帐篷。我们的帐篷极矮小,你在里面站不起身来,甚至当你坐着的时候,脑袋也还碰得着檐顶。我和华洛佳·克洛科夫俩住在一起。他是个好少年。事实上他是位工程师,不是庄稼汉。他比我大好几岁,但是快乐、机智、生气勃勃,而主要的是勇敢。他待我直率,没有谦让殷勤。这叫人很痛快。他有许多可以供人学习的地方。再说,他不叫弗拉季米尔,而叫伍谢夫洛特,可是这里大家都叫他华洛契加,于是我也这么叫他。
妈,你别埋怨我这样东拉西扯。我思想不容易集中。弟兄们正坐在我身边起劲地玩着纸牌呢。不过请你别以为是在赌钱。赌钱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我们根本一文不名,同时绝对不需要钱用。
现在我要开始跟你谈谈帐篷。它是这样子做成的:一张降落伞的绸子撑开在几根木柱子上,而在绸篷的顶上盖上几张冷杉皮。我们是这样来剥树皮的:这一个弟兄站在另一个的肩膀上,用快刀割开一道深深的切口,几乎一直割到下面,然后在树顶和树根周围割破一圈。我们把所有的树枝都齐根削去,削得很光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皮连里皮一起剥下来——你知道,下面便是那滑溜溜的纤维了……这时脱了下来,结果树皮好象一张弯曲的胶合板,上面留了些树节的窟窿;可是我们把窟窿都塞没了,然后把树皮放在绸帐上。任何大雨也透不过这样的房顶。帐篷是故意给做得很矮的。我躺着在写信……
……现在,妈妈,我想把第一次到远方作铁道手术的情形告诉你。你们医生们把手术叫做借重外科刀子的干涉。我们也切断铁道路基,但是不用刀子,是用炸药……我先前只参加爆炸桥梁和德寇汽车。我还曾受命敷埋地雷来爆破作业敌方的有生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敌方的步兵。但这是简单的,你在半小时以内就能学得头头是道。
我动手作第一次铁道手术,不是以爆破手的资格,而只是以战士的资格去的。费多罗夫亲自给我们送了行。不过这一队的队长,它的指挥员,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他是个十分勇敢的人,一个真正大胆无畏的硬汉。他只担心一件事,怕人家总有一天怀疑他是个胆小鬼。除了我们以外,这一队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位姑娘,还有一位出色的向导员——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潘科夫。他认识这儿所有的森林和所有的达到,认识小路,认识兽迹,象“皮袜子”一样。你记得范尼莫尔·库彼尔吗?
当我们给送出去作战的时候,姑娘们都哭了。为什么呢?妈,这是因为她们比男子多情善感的缘故。
潘科夫说:“姑娘们哭起来就跟打喷嚏一样容易。”
当我们离开营地大约四公里时,巴利茨基命令大家坐在草地上,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意味深长地静默了好一会儿,接着嘱咐我们留神听他讲话:“我预先通知你们:谁要是没有自信,谁就回营地去,过后就迟了。我们对于一切困难不能有任何废话,或者任何抱怨。要勇敢、有纪律,要无条件地完成我的一切命令!明白吗?要有丝毫违犯,胆怯萎缩——就地枪决!我不是在嚇唬你们,而只是预先通知你们,假若没有这些条件,你决不能去搞破坏工作。谁要是这么样的,尽可请回去:谁也不会强求你们,谁也不会讥笑你们。”
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尽管巴利茨基保证决不会有人讥笑,实际上,在我们营地里胆小鬼却正引起普遍的鄙视甚至憎恨。他回去就等于自认是个胆小鬼,为此他甚至可能在墙报上被痛骂一顿。
我们站起身来,顺着小路穿过森林。总共得走二十五公里光景。在有些地方,我们倒退着走过公路和村道。我们特地学过这样子走路。为了走成正常的步子,我们必须走得很快,一步不停。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德寇见了我们的足迹,会以为我们是向相反的方向去的。
有一次,我们一直等到德寇的卡车驶过的时候。卡车是整整的一队,载着不下于一个连的士兵。我们没有卷进去跟他们打。我们有别的任务。
我们个人轮流携带炸药,要不然就是地雷,有点儿重——十二公斤。可是游击队员都不喜欢手里拿东西。人人都竭力想把全部重荷分成多少份,好挂在背上或是腰带上;两只手非空着不可,以便随时能够射击。我们也不象红军战士那样背着冲锋枪。我们的枪是挂在左肩上的,就在手边,枪口对着前方。
游击队自造的地雷不过是一木头匣子,大约四十公分长,宽高各二十公分。匣子里放着一种跟芥末颜色相仿的东西,但不是粉末,而只是块茶褐炸药。为了使你不害怕,我要告诉你,它本身是不会爆炸的,甚至把它用火烧、或者给子弹打中了也不会爆炸。它是用雷管来引发的。在炸药上挖上一个或方或圆的窟窿,这儿在装置地雷以前插进一枝爆管,也就是雷管;然后安上弹簧、撞针、信管……你没有图解是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的,再说,你也不须要了解。你未必有一天会利用这些玩意儿。
我们在距离铁道大约六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这儿离开卡明村不远了。卡明村有我们的自己人,我们支队的一名通信员在那边的伪警部队里服务。我们的制度是这样的:破坏队在到指定地点去的路上,无论如何不应走近居民点,因为可能碰上一些坏蛋,他们会跑去报告德寇,说游击队开到哪方面去。
但是一两个侦察员是必须走进村子里的。这一回潘科夫去了。他从伪警那里,也就是我们的通信员那里打听到,在兹林卡—查科培齐区段里,现实相当安定,没有大批德寇。同时他还探明怎样万无一失地潜近铁道。
潘可夫的消息使巴利茨基十分懊丧。原来新近有一列装汽油的火车向布良斯克方面开过了。你要知道,妈,我们炸毁的是哪一种火车,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固然,即使一列装着任何不重要物品的火车碰上地雷而翻毁了,那么这短铁路也要停运好几小时;但是我们用炸药是很节省的,每公斤都得计算计算。炸毁一列运兵的或是装坦克、卡车、飞机、汽油的火车才算是件体面事。这就是巴利茨基懊丧的原因。他心里想,既然开过了一列装汽油的火车,那么另一列就不会很快就开来。
我们十分顺利地到了路基跟前,这儿防卫很差。森林距离铁道线约两百公尺。我们伏在森林边上的草丛和灌木林里隐蔽起来。巴利茨基叫我们个人离开十公尺,以便如果必须射击时,可以一下子包围整列火车。
你要知道,炸毁机车和颠覆车厢还是不够的;必须毁灭所载的辎重。如果开来的是德寇的兵士,那么就尽可能多杀死他们。机车由于爆炸一出轨,列车就停止了,我们便一齐向车厢开火,最主要是向后部的一节车厢开火,特别如果是一列货车的话。警卫队通常总是堵在火车尾巴上。
你现在大概在莫斯科为我熬受吧,像我自己一样,在第一次是不是丢了脸呢。倘使我是独自一个人,那或者会暗暗害怕的。可是所有的弟兄都是好人,大家兴高采烈地走着,还开了许多玩笑。
妈妈,要是你能瞧一瞧你的华洛佳就好啦!我现在完全不象个城里的大学生,正如大熊不象羔羊一般。我有了豪迈的外貌。穿着是按照游击队的时髦式样:一件匈牙利的皮背心(就是所谓‘马扎尔卡’的);一双靴统向下摺的高统靴,上面垂着一条宽大的、用德国毛毯做的酱色裤子;头上带着有红色宽带的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