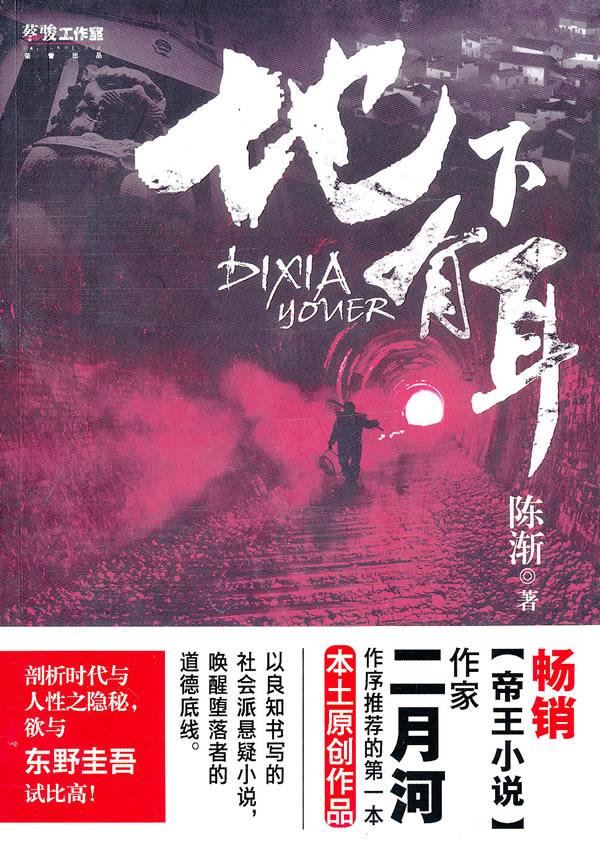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错,”斯捷潘答道,“正是这样。此外,他还说,我们的那个家伙要亲自到司令官那里去对他奉承一番,好象是个对法西斯秩序表同情的富农。对不对,伊凡?”
“完全对!”
“我们七个人聚在一起,开始互相劝说:你去吧,斯捷潘;你去吧,伊凡;啊,那么你去当村长吧,谢尔盖·瓦西利耶维奇!大家都拒绝了,”老汉吸了口黄花烟,接着意味深长地不作声了。
“是的,”我慎重地指出道。“这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困难的工作。必须玩弄把戏,使德寇相信。要不然就会被活活绞死!真是危险的工作!需要一个十分勇敢而且能够自我牺牲的人。”
“您说需要哪一种人?”
“需要一个能够自我牺牲的人,我说。那种原为人民牺牲的人。”
我把博契科的事迹简略地告诉了老汉们。我讲到这位列索沃耶伪村长助理的生活、工作和英雄般地牺牲。
我的谈话使老汉们深深地感动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斯捷潘说:“您说得一点不错。如今死神不用大镰刀而是 着德国的冲锋枪走来走去。送命是容易的。难的是不白白地牺牲。那位去当伪村长助理的博契科同志是有原因的。他好象被查出是开除了党籍的,这种人可以接近德寇的工作。这就是说,他是智勇双全的。但我们是另一回事,司令员同志……”
“我看,”斯捷潘的同伴插嘴说,“您以为我们都是些胆小鬼吗?不,那不是事实。德国人决不那么傻,会让随便什么人担任职务。他们要调查,要研究。所以我们也要象德寇那样来重新审定自己人。我们农庄里还留下多少男人呢?噢,叶利麦脑子不健全,用不着把他计算在那。瓦西利·科茹赫也在名单上划掉了。因为他爱酒如命。除了他们这些神经不正常的人以外,还有四十二个人……”
“老乡们还不错。都是赞成苏维埃制度的好人,有些人坚强些,有些人软弱些。所以我们要支持他们。司令员同志,倒霉的是……”
波布特连科又微微一笑。老汉们不往下说了。说瞅了波布特连科一眼,摇了摇头。他从地下室走了出去。
“他笑些什么?”一个老头儿说。“我看,还是您的态度比较严肃。”
“听下去吧……因此我们几个人便和我们劳动组合的前任主席聚在一起,开始审查这些人,看哪一个而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好象凭记忆力来填写每个人的调查表一般:他合德寇的奴才资格吗?他们会相信他的忠心呢,还是会识破他、吊死他?”
“我们最初想要亚历山大·彼特连科。!”
“他是个头脑绝顶聪明的人,而且又年青,年纪还不到四十岁。”
“他主持过集体农庄的监察委员会。在这以前,十五年以前,他是共青团的领袖之一,支部委员,或是什么……”
我打断了老汉们的谈话:“这个人太出名了,同志们,使不得。这马上要垮台的……”
“我们也那么说呀。使不得,无论如何使不得!我们试试另一个人——安德列·希辛雅克。他当过国家借贷委员会的主席。而且顽强地参加过没收富农财产的斗争。我们否决了他当代表。
接着想到了捷赫特连科。他是个温和的、年纪很大的教徒,理解力还好。他回到答:‘我要捍卫人民。我,要是你们要我做,不拒绝。不过有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呀,帕维尔·斯皮里顿诺维奇?’他答道:‘那个障碍就是我的大儿子梅科拉,是红军上校,我的二儿子格里戈里在维尔纽斯城的党的区委会里工作,而我的女儿瓦尔娃拉·帕夫洛夫娜,你们自己也知道,是基辅电车托拉斯的副经理……呶,现在你们自己来判断吧,我,他们的父亲,配当村长吗?”因此我们决定他也不行。”
“是的,情况困难,”我不得不同意说。
我已经开始明白波布特连科发笑的原因,也忍不住要笑。
“不,请您等一等,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找着格拉辛·克柳奇尼克他是个闷闷不乐的汉子,眉毛象个帽檐。他的相貌的确会使德国人喜欢。于是我便和伊凡一起到他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我们问他老婆:他在哪儿?她说:‘不知道’。我们刚从屋里出来,就看见他正背着包穿过洼地向林子里走去。我们喊:‘格拉辛!’他转过身来,‘干么?’‘格拉辛,你为人民服务服务吧。你在整个苏维埃时代始终不声不响,既没说过‘拥护’,也没说过‘反对’。你当村长正合适。你闭着嘴做事,对德国人不说什么,对我们也不说什么。假如必要的话,你就处罚几个人,好象是由于破坏德国的秩序的缘故。主要的是要瞒过人民的机密,不让德寇知道。假如有个游击队员来了,或者有个当过战俘的儿子回到母亲那里来了:不让德寇瞧见他……’格拉辛想了一会儿,搔了搔后脑壳,回答道:‘我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就是办不到!你们为什么要来纠缠我?要是可能的话,我是很高兴干的。’他又不响了。‘但是,格拉辛,请你告诉我们,咱们是自己人啊。’‘唉,得啦,我告诉你们!你们认识索谷连科吗?’‘哪一个索谷连科?咱农庄里没有索谷连科……’于是伊凡和我互使眼色了:他干么想起索谷连科呀?这位索谷连科在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总是给各报登载些关于我们农庄里的事儿。在区报和切尔尼多夫报上,甚至在基辅的报上,都登着有这个索谷连科署名的小品文。如果有人盗用公款,或者主席搞得不好,或者再有什么岂有此理的事情,正合适——一篇小品文。而且他还写打油诗,就是那位索谷连科。格拉辛对我们来说解释说:‘你们真是些古怪的家伙,那位索谷连科便是我呀!索谷连科是我的笔名。明白吗?我能当什么样的村长呢?我自己只有一条路——动身上游击队!’”
“所以,司令员同志,”斯捷潘接着说,“不管我们想找谁,他一定是苏维埃政权下的:那位是区苏维埃的代表或者村苏维埃的委员,这位是斯塔哈诺夫工作者,而那位是工作队队长……不管你转向哪里,所有的人都不合格。”
老头儿不做声了,带着责备的目光瞅了我一眼。他们俩站了起来。可是我忍住了笑,请他们重新坐下。
“你们要明白。同志们,”我说,“你们谈的话简直精彩极了……”
“那有什么精彩呢?德国人会向我们提出彼德尔·戈罗赫,或者更糟的是伊凡·索洛明纳。这家伙是个扒手。他是这样的一个无赖:不仅别人家的,连自己的玻璃窗也要打……那个家伙会去当村长的。他会投靠德国人。”
波布特连科回来了。
“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我们向这两位同志贡献些什么意见呢?”
“请你们派远方村子里的无论任何人来吧,”老汉们开始请求道。
但是他们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分配村干部的职务毕竟不是我们的事情,同时又同意,德寇未必会批准外地来的人当村长。我们考虑了好久,得出的结论是找不到比索谷连科再合适的候选人了。更正确地说,不是索谷连科而是克柳奇尼克。况且事实上克柳奇尼克已经在昨天来到了森林里,已被编进了一个中队。
值日员把他叫来了。这是个五十一、二岁的集体农庄庄员,大脸、很忧郁,低着头看人,嘴唇闭得紧紧的……
“您白白暴露了自己的笔名,克柳奇尼克同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谁也没有您担任村长的职务来得合适。”
他点了点头。
“您认为您对他们暴露过笔名的那些人不会出卖您吗?”
“司令员同志,当时只有我们两个啊!”老汉中的一个高声说。
“嗯,这么说,他们不会叫您上当。”波布特连科说。
克柳奇尼克又点了点头。
“那么您同意这是必要的工作,而且除了您,没有谁可以托付的了。”
“现在明白了。”
“那么祝您一路平安!去好好干吧……最要紧的是别让人家逮住了……”
到此我们便道别了。几个月之后,当铅字排印的游击队报纸开始出版时,报上经常登载了以索谷连科署名的关于农村生活的短评。谁也不知道这些短评的撰稿人就是德寇批准的古塔农庄的村长。
流离失所、苟全性命的居民在全省四散奔走。他们在小车和自造的橇车上载着小孩和行李。数以百计的家庭一路慢慢地前进,到亲戚、朋友那里去,要不就是到好心人那里去找个安身地方。这样的被破坏的家庭一来到,全村的人便跑拢来请他们讲讲。
这样的‘会议’,德寇司令官和村长都不予禁止,甚至还加以鼓励。占领当局大概是这样想的:“让他们听听,惊嚇惊嚇吧。这样会使他们屈服。”到后来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明白了苏维埃人不论在哪里集会,不管从哪里谈起,它的结语一定是要报复,要消灭德国混蛋。
但是并非所有流离失所的人都是来找亲戚朋友的。有成百上千的人逃进了森林。游击队员们打趣道:“我们的哨所上就象在通行证室里一样排着队呢。”在白天战斗以后的当夜,来的人特别多。司令部无论什么人值班,都收容这些新人。据卢森堡的估计,这些新人都是些真正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只要德国人的军靴一响,他们便嚇得胆战心寒的。他们随身带来了手枪、手榴弹和子弹。当时每一个自愿的人都能在发生过战斗的林中旷地上找到自己的武器。每个前来的人都带来了自己愤激的经历。那些经历,他们首先在哨所上讲,接着在司令部里讲,再后在地下室里或篝火边对新同志们讲。
从马依布敦雅村来了一个叫托夫斯东诺克的集体农庄老庄员。我们有些人早就认识他了。他常给游击队各式各样的帮助,常给我们的侦察员和通信员避难。他认得到营地来的路线。有一天清晨,他带着三个姑娘来了。有一个姑娘随身还牵了一头母牛。
我被叫到哨所去了。老头儿要求会见首长本人。
“你就是费多罗夫吗?”老头儿一面问我,一面向我伸出手来。“我听得人家说,你的队伍的名誉很好。你的弟兄们常到我家里去。很不错,他们都是好人。可惜,我没有儿子,要不然我会提他们祝福之后送到你这里来……我自己也想来,可是到底上了年纪,觉得浑身没有劲儿。”
我听着他说话,却不能不瞧瞧那几个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都是长得脸颊菲红,身体结实。年纪最大的是二十二,中间的是十八岁,最小的一个则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手里握着一跟系在母牛脖子上的绳子。母牛在摇着头,把姑娘拖到一边去。
“罗兹卡,”姑娘对它低声说,“你安静些吧,罗兹卡。”
“你的罗兹卡在着急呢,”我说,目的想吸引这几个年青人加入谈话。“它不习惯冬天在林子里闲逛。”
我说了这几句话以后,姑娘们的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脖子。
“不要紧,”她垂下了眼睛喃喃地说了一句。
“司令员同志,你说我这些女孩子漂不漂亮?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一个是我的大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