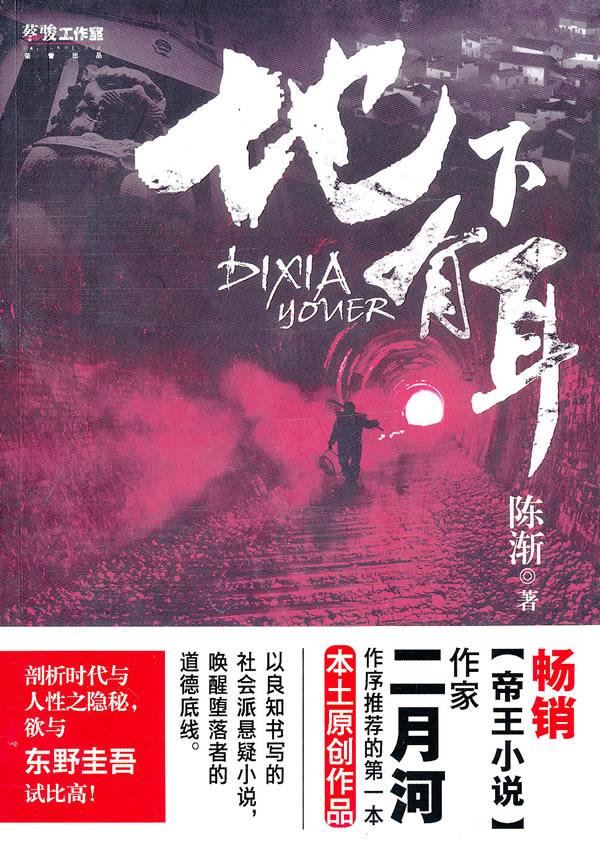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没有带我们今天刚到的这组人参加作战;认为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洗个澡。我洗过澡,休息了一下,便出去逛营地,想视察一下。营地里有五六个地下室:一处是司令部,三处是住所,一处是医院;有一个地下室还没有造好,可是已经给它挖了个坑。这个地下室预定安置印刷机,印刷报纸和传单。
地下室的屋顶只是隐约可见的几个土墩,上面已经铺好草泥块,有的上面甚至已经栽了灌木丛。有一辆“M——型”小汽车早已不用,为了隐蔽起见,一半埋在地里,用树枝盖着。敌人从空中是不容易发现游击队营地的。
在地面上不仅可以发现——潜入营地并不特别困难,在距离中心一百公尺到一百五十公尺的半径内,一共只有三名哨兵在值班。
两个木工正在给印刷机铺装底座,我和他们攀谈起来,接着又走来了几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开始明白支队里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战士们都不满意,但是为什么不满意呢?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们喜欢波布特连科,对其他的领导同志们也表示完全信任。只是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引起他们的愤慨:这个人饮酒无度,待人粗暴,而主要的是对游击战一窍不通。
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波布特连科:说他是个能干、刚勇、聪明的司令员。固然,有时他包揽一切;过分急躁;但他是公正的,必要时还是和蔼可亲的。而对于敌人,他却凶狠得出奇。然而总究……
我好久还不能体会到藏在这个不可捉摸的‘然而总究’后面的意思。
他们告诉我,当支队一路从古林诺转移到新根据地来的时候,原已决定消灭一名伪村长——康卡村的卖国贼。
伪村长本人跑掉了。游击队员们没有赶得上抓住他。在他的草棚里发现了德寇留下来叫他保管的一百副马鞍子。这些马鞍子在支队经济部门中能有用处,但是他们放火把它烧掉了。这不是出于任性蛮干,便是为了伪村长脱逃而懊恼的缘故。这个老乡们对游击队留下了轻举妄动、某种不必要的豪气、简直是流氓行为的印象。
“为什么要白白地烧掉好东西呢?要是我们真的不能带走,而且可能落到德寇手里……费多罗夫同志,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没有骑兵吗?我们只会做那一星半点的战斗……这里窜出来炸坏一辆摩托车,那里杀死一个德国兵,临了还会为了药杀一条军犬而干杯:好一批豪迈的游击队员啊!”
这是一个相貌堂堂、年约四十的小胡子汉子说的。
他正在挖土坑,把铁锹插在泥里,在裤子上抹了抹手,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您来仔细瞧瞧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作战的,并且在希望什么。我们现在就靠坑里埋着的东西活命。甚至把面粉搬运到邻村去。那边的大娘们极乐意替我们拿面粉做面包、做饼干、做包子。唉,咱们的面粉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向大娘们去恳求呢?”
“别介意,吃不完的,”一个愉快活泼的女炊事员摇了摇手说。“他们说,存粮有的是……库兹米奇,你准备打多久?”
“要是象现在这样打下去,那么储存的东西还会有剩。不过问题是:剩给谁呢?据看来是留给德寇。他们虽然是蠢材,但也不会容忍我们太久的。他们首先会消灭巴拉贝,接着是柯济科,而后你瞧,就会悄悄地接近我们。他们陆陆续续开来了多少队伍呀?已有一营人到了菠戈列察。”
又有几个人加入谈话,他们是从营地的各方面走来的,大家对这些问题很着急。
“干么还谈面粉和咸肉?我们是怎样打仗的?瞧,现在他们去干什么了?他们能够在大路上稍稍吆喝一下德国兵就欢天喜地啦。喂,他们会放上几枪,要不就是一无所成。不过是一次远足罢了!”一个两臂都受了伤的机枪手怒气冲冲地说,还啐了一口唾沫。
“侦察员报告,是说德寇在奥尔洛夫卡。那就是说离开我们十五公里。他们是靠两只脚走去的,并且全程跑步,还带着满满的背囊和轻机枪。来回得三十俄里,再加上弯道和小路就的四十俄里。而战果是打死三个德国兵。”
“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事情,”库兹米奇又喃喃地说。
“那么,什么才是主要的呢?”
“你所谓‘什么’是什么意思呢?”他惊奇地反问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的是坚持下去。红军一揍他们,我们说到就到。红军从前线打,我们从后方打。那时就看我们起来打吧!我们应该保存实力。这就是主要的事情!”
“你认为这样能保存长久吗?”
“长是长不了的,可是无论如何总得三四个月,我们应该节省粮食,假如能节省些,定额分配好,就可以坚持下去。”
我打断了这位发言人的话:“慢着,同志,你准备打多久?三个月吗?你们的意见怎样?”我又问其余的人。
其余的人似乎也不准备长久打游击。只有一个同志说要打八个月。他们都嘲笑他,叫他古怪人。
“指挥员们对这个怎么说呢?波布特连科怎么说呢?”
“他说,德寇在今天冬天就会垮台。”
我把听到的一切思索了一番,估量了波布特连科报告的开头部分,回想了伊琴雅支队留下的印象,我了解到主要的不幸正就在“坚持”这两个字上。
但是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显然已开始了解到,就是分散的小股部队也都是不可能坚持的;少数的、偶然的、无计划的袭击战术是危险的战术。
就象是为了证实这种意见似的,波布特连科在第二天拂晓时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战士们都浑身湿透,又生气,又疲倦得要命。
“德寇坐的是汽车,我们是步行,”战士们气忿忿地说。“我们哪能追上他们?”
波布特连科本人对这次进军的结果也不满意;固然,他不愿意表明战斗失败是因为考虑得不正确。他自怨自艾,喝了杯闷酒,在我身旁躺下,说是要睡觉了。
但是他睡了一会儿便低声地开口说:“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着,不很自然地笑了。“我原以为喝杯酒会睡着的。但是并不,酒精也不中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总有点什么不妥当,有些事情得改变一下才对。”
我也想到这一点。我坦白地对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我认为我们直到现在所采取的路线还是不正确的。各支队必须团结起来,不容分家。如果各自为谋,我们来不及醒悟,就会被逐一击破。庞大的队伍能够进行重大的战斗,能够击破敌方的卫戌部队,当德寇进犯时,我们不是等待,而是攻击他们。
为了不致吵醒同志们,起初我们悄悄地说着;但是题目这样激动人,以致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而且立刻发觉所有躺在这里的人都在听。然而因为紧靠着躺在这里木床上的全是省委的委员,所以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当天早晨会议的延续。
就这样没有点灯,也没有起身,卡普拉诺夫、诺维科夫、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们已把他列入省委会)都发言了。
原来,极严重的危险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德寇和匈牙利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队伍。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构筑好一道没有缺口的防线;但在三十公里到四十公里的半径以内,几乎所有的区中心和居民点都有了德寇的卫戌部队;在若干地点,敌人早已集中特种部队来和游击队作战。
附近的那种扫荡队,实力相当于一个营,几天前便到达了波戈列察,他们的侦察兵已经开始搜索森林,每天跟彼列柳勃支队找麻烦。
“巴拉贝到洛沙科夫那里求援,”卡普拉诺夫说,“但是洛沙科夫却回答说:‘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们自己去打吧。’唉,巴拉贝那儿有多少人呢,只有二十七名游击队员。”
大多数同志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把所有驻扎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森林里的支队合并起来,这一点波布特连科也赞成。商定以后,他就不会拖 ,他不是那种人。他没有浪费时间,便起来点上灯,写好一道命令,叫所有支队的指挥员在第二天早晨到司令部来。
“你认为怎么样:大家都会同意合并哩?”我问。
“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们就是在梦想合并啊,”波布特连科回答说。
我们决定再和指挥员们商讨另一个酝酿好久的问题:怎样吸收新人入队。希望入队的人很多:有大队的,有小队的,也有些单独的人……
十一月十九日,各支队的指挥员和政委们会集了:巴拉贝、那哈巴、伏多皮扬诺夫、库罗契卡、柯罗特科夫、洛沙科夫、柯济克、德鲁日宁和比沙拉勃。省委会全体委员和省支队的分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和卡利诺夫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由我个人负责,还邀请了一个人,这是我们这里几乎谁也不知道的尔凡诺夫中尉。他在两天以前才到支队的。
尔凡诺夫当时的外表绝不引人注目:中等身材,声音文静,举动羞怯,而且还伤了一只手;他应该治病,不应该指挥。而我却把他作为未来的联合部队的参谋长介绍给同志们。
为什么我任命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人来担当领导职务呢?这个问题我在出席的大多数人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向我当面提出。当然,我有重大的理由。我自己的见解暂时只对波布特连科和支队政委雅列明科谈过,他们都同意我。
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太暖了。开会的人很多,有些人不得不坐在地上。我劝同志们把大衣脱下,大家都脱下了。只有当地的支队指挥员比沙拉勃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这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困难的。他身上挂的军用品实在太多了:腰带上是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军用挂包、望远镜、指南针,还有许许多多的皮带,使人奇怪的是,他怎么没有给这些皮带缠住。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比沙拉勃,是个四十岁光景、生得结结实实的男子,战前是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甚至担任过短时间的区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对付不了工作。然而他在各边区却是个大大有名的人,也是个独断专行的人。大家都知道比沙拉勃,还因为他在农业集体化时期做村苏维埃主席时,有一个富农想谋害他的生命:子弹打穿了窗户,打伤了他的脑袋。
比沙拉勃动作迟钝,宁肯不走动,不说话。当环境逼着他说一两句话时,他经常从咳嗽声开始,嗯噢着,然后说出毫无意义的两个词儿:“啊哼-呃。”此后他就把这两个词儿一起或者分散插入他谈话的开头、中部或末尾。所以人家想起他的时候,甚至在想起他的姓名之前,许多人就记得“啊哼”和“呃”这些词儿。
“呃-啊哼,我不想脱衣裳。我,啊哼,有病。怕,呃,伤风……”
然而说到比沙拉勃,我必须记得他是志愿到我们这里来的,是自动留下来的。而集体农庄的人们仍在追随着他,承认他是自己的指挥员。他是无条件地忠于苏维埃政权的。
我在会上所遇到的人,在他们成为游击队指挥员或省委会委员以前,几乎全都曾在切尔尼多夫我那里待过。关于波布特连科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