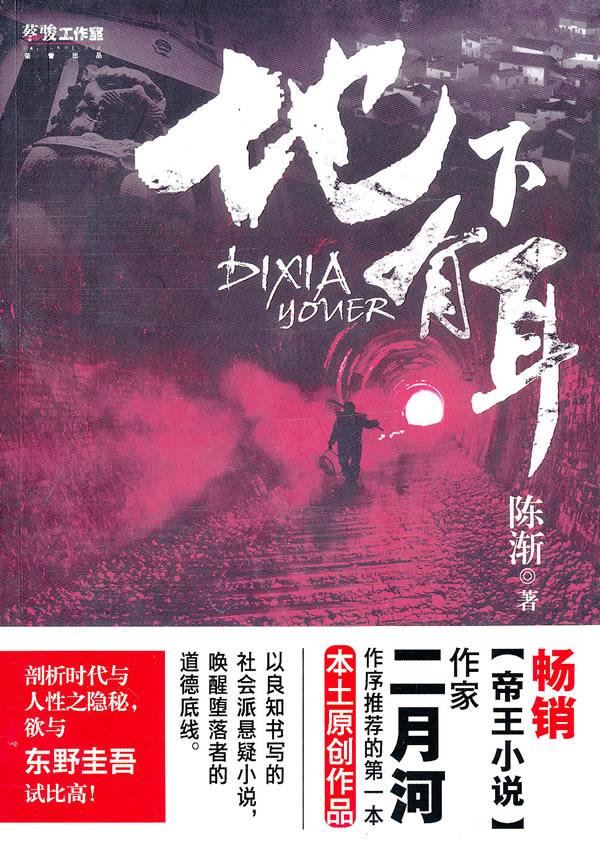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干燥的野草沙沙地响着,正在这时候,乌云好象故意作对似地把月亮遮住了。我在沟底又爬了一会儿,又开了枪。我发觉水沟比我想象的要深些,底面有水,两边长满了密密实实的荆棘,以致在黑暗里什么也分辨不出。况且我又气花了眼睛。我不顾一切地往里钻,给荆棘缠住了。他大概已经靠近水面爬走了。
“我要等到早晨,等到天亮,看你跑得了,你这个坏蛋!”我在黑暗中疯狂地喊道。可是等我稍稍冷静下来时,我这是办不到的。
我爬出了水沟。乌云还遮住月亮;天开始下毛毛雨。但是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得见一点东西,大路的轮廓也辨别得出了。我又拿着手枪在桥边站了十分中光景。喔,你可以想象我怎样咒骂自己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向前走去。
他随后再没有向我开枪,这件事使我想到他已经被打伤了,甚至是致命伤也说不定。我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搞得太蠢了。我至今还很惭愧:眼看着一个明目张胆的卖国贼从我面前溜掉。
我怀着抑郁的、非常愤怒的心情在草原上走。雨越下越大,潮湿的风扑打着我的脸。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当天夜里我还会碰上一件相当不愉快的事情。
早上四点钟光景,我从屋后的菜园,进入马洛·捷维察区的列夫基村,敲了一下博契科对我指点过的那座房屋的窗户。
门里有一男一女方的两种声音在相骂。那女的声音是坚决而气焰很高,男的声音是激怒而刺耳。他们没有立刻听到我的敲门声。
“唉,你这个蠢货!”女的喊道。“你原就是个蠢货,现在仍旧是个蠢货。你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哼,你为什么不作声?对我说,你脑袋里装着什么东西,臭粪呢还是锯屑?”
男的宁愿把这个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当作耳边风:“马露辛卡,你瞧瞧这件事的根由吧,具体地……”
我敲得更响了。这一对吵架的人立刻不作声了,接着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耳语,然后象在移动一件沉重的东西。
不久,女人声音竭力装得挺温和地问:“谁呀?库尔科病在床上哩。”
“开门!女当家的,开门。快一些,自己人!告诉库斯马·伊凡诺维奇,他的老朋友费多尔·奥尔洛夫来了。”
费多尔·奥尔洛夫是我地下党里的诨名。凡是被留在本省做秘密工作的人都知道。
女当家的走开了,显然,是跟男的商量去了。
不久她便回来开门,没有和我打招呼,便指了指火炉那边:“就躺在那边!”
库斯马·库尔科躺在炉台上,除了下巴,浑身裹在被里。他的妻子把小油灯举高了一些,几乎碰到我脸上。
“我知道是费多罗夫,”库尔科说。“果真是,费多罗夫,我和爱人老是等着德国人,所以拟定了一个秘密计划:我‘害了’伤寒病。据说,德国人不让任何人住进有人生过伤寒的房子,总是想法回避。”
“一点不错,”我认真地回答。“他们把所有生过伤寒、肺结核、赤痢和其他有传染性疾病的房子都钉上木板,周围堆上稻草,连里面的一切东西都烧光。”
我不知道库尔科是不是相信我,他好象被蜜蜂刺了一针似的,从炉台上刷地跳了下来,很快地穿上裤子和衬衫,在桌边坐下来,默默地瞧着我。他的妻子也不作声,但是我发觉她脸上却隐现着相当恶毒的微笑。
我这时已经暖和了一些,开始不慌不忙地打量这间屋子。主人们的行动举止有些儿古怪。在进行谈话以前,我要知道自己在和怎样的人打交道。我可以说是按正式程序认识库尔科的。我曾在切尔尼多夫的各种省级会议上时常遇到他,当我访问马洛·捷维察区时也和他交谈过。他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他的外表也是相当平凡的:中等身材,中等体重,后脑壳还秃了一块;穿着也跟大家一样。他遵照地下区委的指示,从区中心迁居在列夫基村。他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他父母的,便是他岳父母的。
尽管房间里的灯光如何暗淡,我从许多征象上还是可以看得出,主人们要不是在分家产,便是在准备搬走。一只大皮箱塞得满满的,连关都关不上。几件新的羊皮短大衣,放在几张拼在一起的靠椅上。十只新水桶,一只套一只地搁在屋角里,而在它旁边,东一堆西一堆地摊着马具和缰 。一只装满洗衣肥皂的木箱,已被匆忙地斜推到长沙发底下。几件儿童大衣,杂乱无章地堆在大床上。这一切里面出类拔萃的,是从床底下突然伸出头来的一只咩咩叫的绵羊。
我请求男主人说:“那么,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您出了什么事,工作进行得怎样?德国人在哪里?总而言之,一切事情……”
“这里列夫基有一批人,”库尔科相当含糊地开始说,“有些是新来的,其余是本区的共产党员。我们在逐步准备……这种工作是新的,可以这么说,还在组织的阶段。我们打算召集一次扩大会议。”
他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你少说些废话吧,库斯马。扩大会议,尽是些会议!这么说,你还要我们在这里呆下去吗?难道说,我们比别人傻吗?噢,你对我瞪着眼睛干么?清清楚楚对我说:库斯马,他是不是你的朋友?(最后的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你干么不作声?”
库尔科茫然眨着眼睛。
“朋友,是朋友!”我对女主人说。“您尽可放心。”
“好,既然是朋友,那么让我们来谈一谈吧。现在您,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称呼您袄,可能是个没有家庭的单身汉,可是我的男人却有一大堆儿女。他可能被吊死,那么让他至少预先给我们打算一下。假如您是他的朋友——那么请给他空洞的脑瓜搬点东西进去,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天的时候,德国人可能来……”
“当然应该藏过,”我说。“为什么你们把这些东西摊得一地?我看这里面还有集体农庄的财产呢。德国鬼子可能真的突如其来……”
“费多罗夫同志,这一点我还会不懂吗!”库尔科举起两臂大叫。“我们刚从地板下面把这些东西拖出来。这里一试就知道是空的。”他在地板上蹬蹬脚。“德国人又不是傻子。他们在地板上跳跳,就会说:‘过来,把它揭开来!”
“这就是我们反复争论了两星期的事情,”他的妻子又开始说。“我们一会儿把这些东西藏起,一会儿又把它们拖出来……您知道这个下流坯要什么?他说:让我们把它拿到村子那头爹爹去吧……要是德国人把你抓住了,那么我可以到公公那里去要……他要把一切东西都拿走。我什么也不会给你爹的!”
“可是我父亲要比你老实一百倍。”
参加家庭的口角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站起身来,戴上了便帽。库尔科也学着我的样穿起衣服来。
但是他的妻子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说:“我哪儿也不让你去,休想!你还没有在区苏维埃里呆够吗?现在你又出去了?”
“库尔科同志,请您告诉我,现在我能到谁那里去?能在哪里找到一些头脑清楚的人?”
他竭力想挣脱他妻子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我懊丧地走了出去,砰地把门关上。
冷冰冰的风吹袭着我。我想:“好,我又落难了,库尔科和他的老婆真该死。现在我怎么办呢?碰到人家便敲门吗?还是象以前那样找个干草堆呢?……”我已经转过街角,想到菜园后面去找个干草堆,这时候库尔科的屋门又打开了,主人挣脱了她,带来的是惊哭和恐吓。
“真是个鬼婆娘!”他吃力地喘着气叫道。“走吧,奥尔洛夫同志。我带您到一些正常的人家去。您瞧,我是个废料。唉,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要您能叫我怎么办就好了……”
我们一起走了不下半小时工夫,我们向前走时,库尔科抱怨自己的命运说,和他那位老婆在一起,从来就没有幸福。
“您等着瞧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会认清她的性格的。记住我的话,明天她会跑到伪村长那里去说:省委书记在这里。”
“千真万确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虽然她是我的老婆。我和她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了,她是个毒辣的婆娘!她什么事都做得出。”
“您怎么和她一起生活的呢?”
“我哪有过生活,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只有受罪。”
月亮下去了,我们在黑漆漆的暗地里慢慢地走着,冷风差点儿把我们吹倒。
“听着,库尔科,”我在暗地里里说,“您把我一送到目的地,您懂地我说的话吗?”
“懂得,奥尔洛夫同志!”
“那么,您把我一送到秘密接头地点,马上就回家,叫您的妻子别声张。”
“我还是不回家的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不,您要回家!您应该到家里去,照我嘱咐您的话去干!”
“是,奥尔洛夫同志。”
“她知道我们上哪里去吗?”
“知道!”
“那么她知道所有属于地下组织的成员吗?”
“不完全知道,不过,知道得也不少。”
“您可完全知道?”
“我也不完全知道。”
“请您告诉我,当您在德寇的后方留下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要面临些什么任务?”
“噢,当然想过。就是现在我也明白了。我疏散过我的家眷,亲自让她和孩子们坐上马车。好,她坐了车子大约走了三十公里,兜个圈儿便转回来了……‘该死!’我对她说,‘什么事把你带回来了?滚开,你想上哪里就上哪里。我有工作要做。’但是她固执得不得了,一动也不动。德军正在这时候包围了列夫基,前线也转移了。唉,在这里我还能干什么?”
库尔科的声音是可怜的:似乎因为烦闷苦恼和一筹莫展而快要哭了。然而,我并不可怜他。
“您认识这一带的路吗?”我问。“请您解说明白,我怎样去找那个秘密住所,您本人不必远送了。我给您的命令是:随您怎样去干,可是必须迫使您的玛露辛卡不做声。别让她有一分钟不在您的眼前,要看住他!”
库尔科又咕哝了几句,后来还是回转去了。
我等到他的脚步声消失以后,就回过身来,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沿着收割后的庄稼地径直走过田野,走了大约两小时,拂晓时分发现到了西斯基村。我很幸运,那里没有德寇。
当地下省委在切尔尼多夫我的办公室里开会,讨论万一本省被德寇占领的情况时,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组织方案:在每一个村庄,无论如何在大多数的村庄里,都要有地下支部,抵抗小组,所有的区一律要有游击队和党的区委会;要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及万一他们被捕后的几个接替人;在支队、区委和支部之间要经常保持联系;省委指导区委,区委知道基层组织;人员要时常进行会议。自然,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甚至后来,在雅勃隆诺夫卡会议以后,在波略丁的混乱以后,在很多天的单身流浪以后,我还有这样的想法:只要一到达切尔尼多夫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