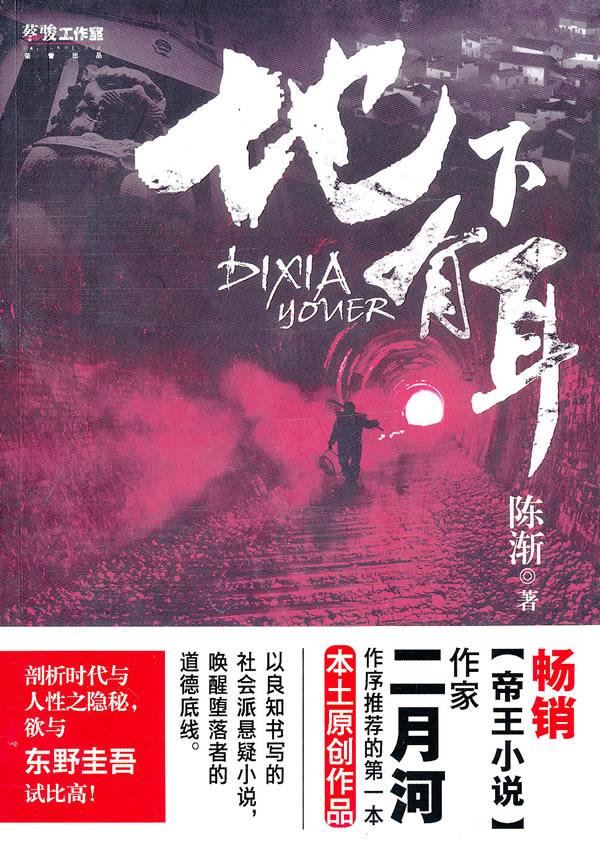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兵,在跨过小河的桥梁底下可能有敌人的地雷在伺候着爆破手;换句话说,为了在铁道上埋地雷,首先应该扫除通向铁道的进路上的地雷。
困难虽然增加了,被我们颠覆的军车数量却也每星期都在继续增多。但是使我担心的是,在敌人的地雷上受了重伤的事故越来越多。在离开铁道时,我们优秀的指挥员之一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牺牲了。德寇把地雷挂在树枝上,把导火线向下拖着……当然,很难预察到这种诡计的。但是我们的爆破组在袭击列车以后,特别是在得手的袭击以后回归营地的路上,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不太谨慎,这一点我们决不能不闻不问。小队指挥员别洛夫也由于不小心而牺牲了。他俩都是巴利茨基大队里的。常常有些马车载着伤员们到我们的中央医院里来。有马尔科夫队里来的,有塔拉先科队里来的,但最常见的是巴利茨基大队里来的。
巴利茨基继续带领人数很多的游击小组到铁道上去,他自己也跟着他们去,并且要求分队指挥员们也参加每一次爆破战……
到八月中旬,巴利茨基大队所颠覆的列车数目是最大的。在一个半月当中,他炸毁了四十八列军车。为此许多游击队员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可是巴利茨基的威望却依然很高。
我记得,跟巴利茨基的队伍接邻的一位支队指挥员尼古拉依·阿尔希波维奇·普罗科皮克尤到联队司令部来了。他和麦德维捷夫一样,也是为了特种的目的而来的。他这个比较不算大的小组是在离科维里不远的地方用降落伞空投下来的。一批从德寇俘虏营里逃出来的红军战士和当地的农民青年来和这个小组合并了。在短短的时期中,普罗科皮尤的小组增长为一个有二百多名战士的支队。善战的、果断地指挥员决定,在完成自己的任务时,顺便来动手打敌人的军车。
来到我们这里以后,普罗科皮尤叙述了他的支队是怎样和巴利茨基的支队在一起进行“卸货战役”的。
“您想想看,我们的人有一百二十名,而巴利茨基随身带来了大约一百五十名战士。有这样的情报:说有一列载着军装的军车要开来。我和巴利茨基决定要把货卸下来。我们在树林里散成散兵线伏下,距离铁道约有一百多公尺。巴利茨基不爱惜炸药——在机车下面埋下二十五公斤,把整个机车给炸得粉碎:车轮的碎块、车轴、钢轨的破片都在我们的头顶上嘶嘶地飞过去。然后我们用冲锋枪和机枪的火力向列车打去,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巴利茨基,喊道:‘跟我来!’他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个煞星,亲自顺着列车跑来跑去:‘弟兄们,把那节车厢打开,拉门哪!’每个战士手里拿着一束稻草。他们从车厢里拖出碰到的东西,而在包儿或者箱子的空地位上,用稻草和火把在车厢里放起火来……军车着了火,护车队被打垮了——我们就退进了森林……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小的误会。我们在这列军车上多多少少弄到了一些军服,可是大部分的袋子里装着奇怪的货物。后来,已经是在森林里,在平静的环境里才看清楚。你想象一下吧:原来是些蚊帐。好几千顶蚊帐……但这是小事。整个说来,作战进行得很顺利,很热烈,是大可欣赏的……”
我的地雷爆破活动的助手耶戈罗夫听了半天,忍不住说:“为什么弄得这样吵闹呢?为什么使这样多的人在铁路上呢?你要知道,如果支队指挥员们每一次都亲自参加军车的卸货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没有人来指挥了……”
“不,这挺妙!巴利茨基不错:很热情,嗓子又粗壮——那么鼓舞着战士们!”
我呢,产生了双重的感觉:当外人、客人,这样诚心诚意地夸奖我们的同志们,这样赞美他们时,我觉得高兴,甚至很高兴。我不由自主地以巴利茨基自豪,虽然同时也知道他骄傲过分,自信过强……
我本来应该到第一大队去一次,亲自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但当时使我更为焦急不安的,倒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区段上的大队,而是那些安安静静、缺乏生气的区段里的大队。最安静的是在塔拉先科大队的区段里。他在自己的最近的无线电报里发牢骚说,他的爆破手们没有能够掌握好新型地雷。
一个星期以后的深夜,我们坐在塔拉先科的很大的司令部地下室里。我同耶戈罗夫已经在第七大队的驻地里逗留了三天。在这段时期中,耶戈罗夫给爆破手们作了几次指导性的报告,我熟悉了一下营地的生活,召开了一次大会,我们预备在第二天早晨动身回到联队司令部去。
现在耶戈罗夫好像作总结一样,很快地在纸上描画着各式各样的地雷爆破的技术图解,一面还谈到最新式地雷上的爆帽、雷管和电气化学上的优点。接着他把话题转到怎样爬近最好、怎样隐蔽自己和怎样伪装地雷的问题。他所谈的一切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是必须的,虽然不很引人入胜。
“我认为忽视定时地雷是由于对它研究得不够的结果。”
塔拉先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是个性情急躁的人。我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在起着变化,连颈子上的血管都突出来了。
“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亲爱的耶戈罗夫同志。你要看看我们这里是怎样的结果。这不是定时地雷吗,对不对?”
“当然。”
“问题就在这里:它有时慢到这样的程度,使爆破手们寂寞得很。当他爬去埋地雷的时候,也很容易送命。对不对?”耶戈罗夫点了点头,“同时如果碰上了巡逻队,他也会被打伤。危险性反正和普通的地雷一样,而效果却不一定什么时候得到……你要知道,敷雷手是急性人,希望看到自己引发的爆炸,感到自己的泼辣的工作。而现在在前三天把地雷埋下便走开了。就象钟马铃薯一样:要等到秋收。”
“原来您是在寻找心理上的辩护理由……”
“不是辩护!”塔拉先科叫起来了。“我是坚持着技术总归是技术,不过应该叫敷雷手也弄到了解为止!”
支队政委米哈依洛夫是个身材很高、性情平和的人,初看甚至有点儿萎靡不振,但总是很好地发挥或者软化指挥员的想法,弥补他的不足。现在他十分独特地加入了争论——请耶戈罗夫抽一支烟,而当米哈依洛夫神经质地伸手去扳打火机——那么长久地、徒劳无益地旋转着小齿轮的时候,耶戈罗夫也等得不耐烦了,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打火机,急忙地打着了火来抽烟……
米哈依洛夫说:“请原谅,耶戈罗夫同志,我这个打火机是定时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耶戈罗夫也微微一笑。
米哈依洛夫接着说:“耶戈罗夫同志,当你一下子打不着火的时候,您也有点儿着急。瞧,我们的敷雷手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接受您的一切指示,会说服他们的……”
这时值日员报告说,克拉夫琴科支队的通信员到了。
克拉夫琴科没有无线电台。他都经由塔拉先科的大队司令部转达自己的报告。他的支队从七月十六日起到我从洛勃诺耶走开的一天止,已记上了十三列爆破的军车。在我已看过的他那最后的报告里,克拉夫琴科抱怨炸药不够用,跟平时一样,他请求额外地拨给他一些武器。他诉苦说,作为一位指挥员,他自己不得不在没有冲锋枪的条件下设法对付……这当然为的是加强印象。哪有支队指挥员把冲锋枪给战士,而自己留下了步枪或是手枪的!
我们忙于热烈的谈话,没有立刻把克拉夫琴科的通信员请来——他能报道我们一些什么特别重要的消息呢?大概又是抱怨武器不足吧。
通信员还是自己叫我们想起他来:他通过值日员的转告,说是指挥员叮嘱他不要耽搁——把情报交上立刻就回去。这个小伙子大约十八、九岁,穿着一件土布的长外衣,腰里束着一条鞣皮皮带,头上戴了顶没有边的帽子,活象我们革命前街上的水果摊贩们戴的那种帽子。腰带里塞着一双手套、一根鞭子;旁边还挂着两颗手榴弹。小伙子敬了礼,接着突然摘下了没有边的帽子,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
“怎么,难道指挥员没有教你应该怎样作报告吗?”
“一点不差,教过。”
“那你为什么要鞠躬呢?”
“这不是在房子里吗……”
“那么,你在房子里没有见过指挥员吗?”
“没有。打从侵略者烧掉了我们的房子以后,我就没进过房子。”
“噢,情报在哪儿?”
小伙子伸手到工统靴里,取出一张写有密码情报的揉皱了的纸。当我们了解了数字的符号时,通信员咧着嘴笑了……
“哎呦!……大概弄错了。你看一看吧,耶戈罗夫同志。”
耶戈罗夫大声读了一遍:“从八月八日起到十四日止,我们炸毁了敌人的九列军车。其中有一列修理车,是八月十四日夜间被定时地雷炸毁的。在总共三十一天里,我们一共炸毁了二十二列军车。由于支队活动的结果,总共中断运输一百五十四小时……”
“扯谎!”塔拉先科气忿忿地叫道。
这下子通信员变了样了!他顿时脸色发白了,手足无措起来,微笑一下子从他脸上消失了。看来他好像要扑到塔拉先科身上去。但小伙子只是倒抽了一口冷气,然后很响地吐了出来:控制住了。
“说吧,说吧,”我鼓励他说。
“我们的指挥员一点也没撒谎!”他热烈地叫道。
“你自己数过列车吗?”塔拉先科冷笑着问他。
通信员没有理他,甚至没有向他那边转过脸去。
“该审查一下,”耶戈罗夫怀疑地摇着头说。
“我说,他一点也没扯谎!”通信员重复说。
为了使他冷静下来,我命令他出去。的确,审查一下是应该的。如果我不知道克拉夫琴科没有特殊的原因从来不喝烈酒,那就会认定情报是他因受喝醉的影响才写的。
大队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好象说他自己道:“前天有人给克拉夫琴科传达了准备一些受奖材料的指令……”
“哎,算了吧,”我说。说过,我当时就想到,一些大支队送来的情报都要细心地审查审查。不管是到巴利茨基、马尔科夫那里,或者到塔拉先科这里,总有联队司令部来的同志。但是从来没有人到克拉夫琴科那里去过。尽管疑心有功的指挥员在欺瞒敷衍是很难过的,可是审查他的情报是必要的。
“其实,我了解克拉夫琴科的性格的哪一点呢?”我心里案子思量。“他是泰然自若、冷静沉着的,但有时侯几急躁的。他很惊喜,能确切执行任务,并行毫无疑问是勇敢的。但克拉夫琴科是个阅历很深的侦察员。我所看到的品质,也许根本不是他的性格的品质,而只是职业上的特征。”
“他在我们这里领了多少炸药?”我问耶戈罗夫。
“我正好也在想这件事呢,费多罗夫同志。最后一次给他送去了一百公斤……”
“我向他借了二十公斤,”塔拉先科说。
“那就更奇怪了,”耶戈罗夫接着说。“整个这段时期中只有一百八十公斤……如果按照巴利茨基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