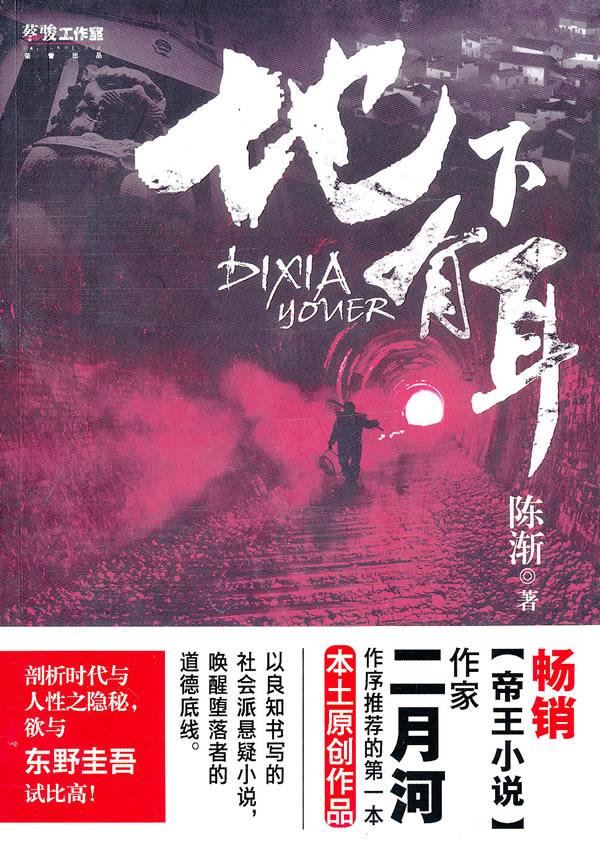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0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游击。
我们的地下室是在枞林深处,在树木最繁密的地方。谁都发现不了我们。我们总是在天色微明的清晨烧炉子。我在三点钟起来升火,然后准备给伤员们包扎伤口。有时象个流浪者一般到勃列什涅去讨一条旧床单或毛巾。人家给的时候也不加过问,大概知道我是谁。古拉克开始有些儿复原,真叫人高兴!这就是说,我们的劳动没有白费。而他可以说曾经是一具尸体:浑身——满脸、满胸、满背都烧伤了。后来我的古拉克就开始行动了,甚至还请求站岗。
而谢尔盖·波马兹的盘骨被打坏了,只能躺着。身体倒是健康的,可是站不起身来。我为他忍受一切,给他洗涤……我很害怕坏病,他自己也害怕——由于这种害怕,他吃不下饭,瘦了,睡觉时大说梦话,好不嚇人。白天还好,他有些精神。他的创伤五个多月没有养好。大概我们甚至在冷天也把他放在太阳光下照晒而生了效吧,当我看到创伤开始收口时,我的谢尔盖微微地笑了。他开始请求弄些肉吃。这就是说,他复元了。
我们到伪村长那里去偷了一头羊来宰了,把肝儿炒来吃。大家高兴极了:‘瞧,目前这几天里大家会吃得饱了。’我把羊肉挂在树枝上。伊凡·费多罗维奇说:‘今天你做个羊糕,烧些菜给弟兄们吃个饱吧。’
我拿羊肉去了,走到跟前,只悬挂着一些骨头,完全给喜鹊吃光了。我们只得舔舔嘴唇……可是我把骨头煮了,清汤是很肥美的。我们再没有去碰另一只羊。村子里已经够惊慌了。
我们这样过了六个月。这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二月底,夜里两点钟,听到了脚步声。我坐起身来。我有两颗手榴弹,就这样决定:一个投向谢尔盖,把他炸死;另一个投向门口,而用手枪来自杀。吉洪诺夫斯基和其他三个弟兄正在玩骨牌。门突然打开了,有个穿白色罩衫的男子走了进来。伊凡·费多罗维奇立刻拿起手枪,我也挥起手榴弹。
‘住手,吉洪诺夫斯基,别开枪!’
这是我们的人来了。队伍回到了叶林诺森林,波布特连科立刻派人来找伤员们和整个小组。关于我们,有人说,全体给德寇抓去了,所有的人几乎全被打死了,而我却受了重伤。并且好象是后来有个德寇军官和我结了婚。简直是胡说八道。波布特连科不相信。
我们都坐上橇车,被送往营地去。是怎样迎接我们的——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大家都吻我们,还给我们唱了几支新歌。女炊事员特地为我们备办饮食……但这以后再讲吧……第一天我就知道格列沙不在。
格拉沙哪里去了?他健康吗?
‘据说:在莫斯科呢。’
我想:送到莫斯科去的只有重伤员。我问:‘他哪里受了伤?’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许他已经功成名就,被送往莫斯科休养去了!……’
但是总还是有人告诉了我,他鼻梁和一只眼睛给碰伤了……过了几天,飞来了一架飞机,我们跑去迎接。当我们跑到飞机场的时候,大家已经走出飞机。我跑去找巴利茨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而我在他一旁跑了过去……费多罗夫给我问了好,拥抱了我。
‘你为什么不给格列沙问好呢?’
‘他在哪儿?’
我一看,在我面前站着个漂亮的男子,打扮得够俊,胖胖的,戴着高高的帽子。我想,这个焕然一新的人,不是格列沙。当我带着我们那组人走开的时候,格列沙是穿着棉袄,戴着便帽的……
‘而我呢,’他说,‘看着——她向谁跑去了,谁是她所最珍贵的?’
于是我抱住了他。这时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跟摄影员说:
‘快拍!’
我问格列沙:‘你的眼睛怎样了?’”
他淌下了眼泪,可是他说:‘能看得见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的叙述完了。现在请别人来讲吧。”
马露霞讲完以后,大家好久没做声。可以听到篝火中的树枝发出拆裂声,就象马儿用牙齿咬嚼着青草一般。马露霞走进阴影里,坐在一个人的宽阔的背后。那时我想会有人详细问她。不,好像大家同意了,在这种叙述以后应该把思想集中一下。许多人瞅着巴利茨基,他就站在那里,带着很自信的姿态。我感到他不满意马露霞的叙述,甚至想推翻她讲的某些东西。他整个的体态、服装、风度,都可以看到他的豪华气派。他头上戴着一顶要掉下来的、飘有红带的黑羊皮高帽。天气早已回暖,还戴着冬天的帽子是可笑的;但巴利茨基不是人家可以来取笑的那种人。
在那个时期中,他的声名在我们队伍中是最卓著的。这是大无畏精神和军事上的幸运的声名。敌人的子弹都放过了他。不错,他丢了一只眼睛,但这是自己的冲锋枪的弹壳打的。
巴利茨基没有立刻就开始讲,不得不请求他。也许他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讲吧。早晨我和他争论过一阵。他是昨天从莫斯科回来的,报告了完成任务的情形。而今天他突然交给我乌克兰司令部的命令,里面指示我拨出一定数量的人员——普通的战士和指挥员给他,同样拨给他武装、弹药、口粮,建立一个以巴利茨基为首的新队伍,而且这个队伍要按着独立自主的行军路线前进。
没有办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命令是必须服从的。我对巴利茨基说,每一个大队的指挥员都会拨给他一部分自己人。但是巴利茨基要求我下命令,把他指挥过的第一大队拨给他。我们认为第一大队是我们联队里最好的一个大队,里面大多数是老游击队员,都是切尔尼多夫人,我坚决拒绝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用无线电征询了一下乌克兰司令部。那里支持了我。结果巴利茨基放弃了独立自主的任务。我们决定了巴利茨基留在联队里当第一大队的指挥员。
但是他显然到现在气还没有平。他不时向我这边含怒地斜着眼瞅看。毕竟被人家说服:他开始叙述了。他带着不太注意往事的那种人的样子叙述着。听众觉得他讲得有些儿自高自大,但是却原谅了他这一点。也许有些人还认为著名的游击队员应该这样说话哩。
“我们在这里感怀往事,甚至嘲弄自己。我们每个老游击队员都经过了许多次死亡。即使谦虚地来计算,我个人就逃过了二十二次死亡,而且继续在行动。有时我问自己:‘格里戈里,为什么你还活着呢!保护住了还是侥幸呢?’我是这样回答的:‘战斗以后依然无恙——既不是你个人的幸福,也不是为了休息或光荣而留了下来,而是为了继续斗争到最后胜利!’
如果谈到抒情的和带诗意的事儿,对我来说,一直到战争结束,最带诗意的是敌人的死亡和覆灭……我是一个有目的的人,而且现在要同大家谈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过一位同志,他曾经很勇敢。但一切都精打细算,他说:‘我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接触了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我的几乎逐次在递减——不是弹着点过远,就是弹着点过近,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总会打中的。’每经过一次战斗,他就变得更加小心,渐进到这样的地步,有一次在伙伴们中间醒来,嚇得眼前发黑,跳起来大叫‘德寇来了!’用手枪指着太阳穴——于是就完了。我们甚至来不及阻拦他。而那时恰恰没有德寇。
我有时侯听到这样的词儿:‘小心谨慎’,好像游击队员应该是小心谨慎的。但这个与恐惧畏缩的界限在哪里呢?当然,界限是有的。小心谨慎——这是一种念头,人还在想,还在理解怎样卫护自己。恐惧萎缩——这是无意识的逃走,是张惶失措。例如:有一次我们躺在散兵线上,在掩蔽所背后,看到一个德寇的步兵正向我们走来,我们让他接近。突然有一个我们敬爱的同志喊道:‘弟兄们,这是冲锋枪兵!’跳起就跑,于是大家跟着他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早就知道德寇步兵中有许多冲锋枪兵吗。不,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冲锋枪兵,而在于张惶失措分子的声音使人神经受了影响。
恐惧畏缩是游击队员最凶恶的敌人。至于说到小心谨慎……小心谨慎起着别的作用,它是恐惧畏缩的姐妹,可是很狡猾,它一切都可以理解、可以辩护,逐渐地使游击队员变成胆小鬼。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指挥员给了任务,游击队员去了,并且看到,很困难,又很危险。这时他已经不是在走而是在爬了,这是对的,应该爬。但是总有时候得站起来啊。单爬是不中用的。而他抬不起头来,好像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的头压在地上。他心里可原谅地把它说成小心谨慎,而这种小心谨慎早已成长为恐惧畏缩了。这种游击队员回来就报告:‘指挥员同志,任务完成不了。’并且把一切都那样详细地解释了,使人只有为他的小心谨慎而夸奖一番。而目的呢?目的可没有达到。小心谨慎变成了目的。
所以我们有一条游击队的法则:出去完成任务,你的生命、智慧、心灵、思想、武器,一切都是为了目的。应该以智慧、以计算来行动,甚至也可以施用小心谨慎而完成任务!
从这儿出发,我来谈谈自己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其他人一样,谈谈我个人经历的头几天的情形。你们的头几天是在老同志们中间过的,我们那时可没有老同志,指挥员们也都没有游击经验。
一九四一年九月里,有一次波布特连科说:有一座德寇在开工的磨坊,应该把它炸掉,不让敌人磨粮食。他给我的任务是:‘你考虑考虑,给自己选一个小组吧。’彼齐卡·罗曼诺夫、瓦尼亚·波列舒克和我三个人一起出发了。彼齐卡假扮了农学家,瓦尼亚扮成了农民,戴着便帽,而我冒充是人教师:我经常这样去侦察。大车上放着一袋黑麦和一袋大麦,又拿了一束导火线,一些炸药,还有一支冲锋枪。我们把这一切都藏在大车里。
从森林里驶出去,刚到林边,马溜了。我从来没有套过马,我的伙伴们也没有套过。瓦尼亚想跑回营地去。幸亏我们的哨所里有位集体农庄庄员出身的同志,给我们把马套上了。我们也练习了卸下几次,套上几次,然后才出发。
我们来到了阿列克桑德罗夫卡,已是黄昏时分,应该找个过夜的地方。请求了一位女农民,她有个女儿。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宵。早晨开始套马,套不上。她的女儿嘲笑我们,却给我们把马套上了。
这个时候,老年的女主人问道:‘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呀?’
‘到磨坊去。’
‘唉,你们哪!怎的什么都不会做呢。怎的你们三个人却带着两个袋子呢!’
‘这只是我的袋子,我是教员;这只是彼齐卡的袋子,而这位是我们的赶车的。’
她带着笑问:‘为什么三个人去磨两袋子粮食呢?’
她教我们学会了先见之明。我们理解到很容易被人识破。女主人很好,她丈夫在前线。我们请求她再给我们一只袋子,把粮食分成了三份。
我们带着三只袋子继续前进,下午五点钟,到了区中心米纳。我已经到这里来侦察过。我在想:‘万一有人看出我们呢?’我们停好马车,自己走进了磨坊。门口有一个德国兵,另一个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