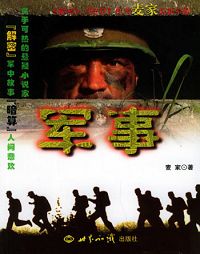中共无衔军事家-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情况既然如此严重,党和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时撤退,留下管军事的同志在这里指挥。”
匆忙之中,总指挥部作出主力经花县和石龙、惠州之间撤往海陆丰的决定。在敌军冲进城内、部队被打散后,叶挺化装成瞎子,戴上破帽子和墨眼镜,遮住脸,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妹妹,凶险万分地逃到了香港。
这次起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撤退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许多战斗单位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仍在原地作战,损失惨重。教导团撤出城后,敌人杀红了眼,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仅仅三天之内就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徐向前当时担任工人纠察队第六联队军事教官,他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 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时也没有部队,听说已撤往桂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聊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有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里才走的。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8节 选择流亡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当时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中央政治局扩大到广东省委,尔后又蔓延至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大多数起义的当事人,特别是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和冷静思索,认为关键的原因是总指挥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几次拒绝叶挺向海陆丰转移的正确意见:
——徐向前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拼硬打,想占住城市不放。”
——聂荣臻、叶剑英认为,起义初胜后两次军事会议是一个关键,如果采纳叶挺的意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那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起义队伍包括人数巨大的工人赤卫队还没有被打散,如果带往海陆丰,加以整顿,会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负责处理广州起义党内纠纷的周恩来十年后在《六大研究》中也提到:“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撤退,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革命干部。”
——连当时坚决反对撤退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在《往事回忆》中承认:“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特别是受由于敌人大屠杀所激怒的复仇情绪影响,党组织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1927年12月下旬,中央巡视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到达香港,经过调查,写出《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1。起义前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单纯搞军事运动,甚至借口保密而阻止鼓动群众。2。起义后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3。完全没有执行没收反动政府和反动派逆产的政策。4。未能有计划撤退,许多负责同志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因而很多干部和赤卫队未能撤出,在敌人反攻进城后被杀数千人。 应该说,这个报告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广州起义中的失误。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也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
错误起缘于1928年1月1日至5日举行的新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会上,许多参加者怀着复杂的心情,激烈地批评起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和红军总司令叶挺首当其冲。主持会议的李立三不仅拒绝叶挺等人与会,剥夺了他们说明事实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不仅未能引导出席者冷静地理顺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总结经验教训上来,反而提升和张扬了这些不适当的追究、迁怒和罚办倾向。会议通过《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严厉处罚了所有起义的领导者,分别给予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议案指斥叶挺在担任红军总司令期间,“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叶挺怀着一腔委屈,向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到一些广州暴动负责同志的申诉和李立三的信件、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后,认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 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李立三主持下对广州暴动的错误结论和处罚决定,派邓中夏接替李立三的省委书记职务。
留党察看的处分虽然撤销了,但是叶挺“表现消极”、“指挥动摇”等罪名依然未改。叶挺觉得不满意,继续要求改正错误的指责。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留守国内的中央机关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叶挺追到苏联,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
在苏联,叶挺受到冷遇和明显的歧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不让他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不给任何答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更有甚者,深受米夫青睐的王明还写《广州暴动纪实》一文,指责叶挺在指挥起义中违背了苏联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和原则。叶挺奋笔疾书,写下关于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同时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如果在一月之内仍然得不到答复,自己就离开苏联。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答复,连个回条都没有。莫斯科的高官们好像没有意识到叶挺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叶挺这个人。
共产国际不理睬叶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却景仰这位传奇英雄。他们派代表邀请叶挺去作报告,用鲜花把会场装扮得十分美丽。可是,米夫、王明又指使一批学生故意捣蛋,共产国际也下令不准叶挺去演讲。叶挺一气之下,离开了苏联,来到德国。
后来,叶挺意识到党内的争论不能靠怄气解决,愤然出走过于意气用事,于是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这时,谁也不理他,连以前的熟人都像遇见瘟神一样躲着他。叶挺无奈,只好再次选择流亡。
在党内,他是不受欢迎者,苏联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在国内,他是红军总司令,被蒋介石悬赏缉拿。有党难归,有国难投,他只好选择欧洲和澳门作为避难地。这一避就是十年。
对于这段历史,叶挺怀着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深怀委屈,当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党时,他辛酸地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呀!”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年的负气出走也觉得惭愧。
其实,当年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组织实行罚办主义,不只是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的许多起义领导人都遭受过各种处分。毛泽东自己统计,他遭到的党内错误处分达八次之多。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选择的是继续工作,让实践来证明孰是谁非。
周恩来是叶挺信赖的朋友和知己,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解释这段历史:“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训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伸冤。”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9节 新四军
主动请缨,担任新四军军长。身为军长,叶挺理应成为决策核心,但是他的非党身份又使自己处于配角地位,加上与项英的分歧,他在三年任职内竟然两度出走,引发政坛轩然大波。蒋介石大做文章,毛泽东亲拟电文,明确叶、项的职权。周恩来由渝赴皖,调解军政矛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战。北伐名将重 新出山,成为当时政坛关注的焦点。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协议。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民党提出由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都退一步,提出邀请叶挺出任这一职务。叶挺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当过共产党党员。他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认为,经过党内斗争的沉重打击,叶挺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如果主动提出让叶挺挂帅,可以施恩于他,便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捏在自己手中;同时,叶挺毕竟是正规军人,不同于以钻山窜岭、分散割据为资本的“山大王”,通过叶挺将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既可以稳住后院,也可以驱虎斗狼,让红军游击队与日军拼个两败俱伤。于是,他不等中共方面正式表态,就抢先发布委任状。
叶挺渴望上阵杀敌,立即同意领导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这个军改编后的番号为“新四军”,以纪念北伐战争中威震遐迩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蒋介石与叶挺的举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疑窦。毛泽东10月1日发电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9日,毛泽东又来电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叶挺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后,万丈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叶剑英来看老乡。他委屈地说:“国共两党都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都在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早知如此,我又何必争这个宝座,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