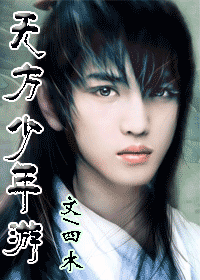恰同学少年-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泽东喘着粗气对他说:“我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来求见袁仲谦老师的。”
“学生?也不看看几点了,有事不能明天说吗?”
“我真的有事,我想马上见到袁老师。”
“可先生已经睡了……”
两人正说着,袁吉六的妻子戴长贞从里屋出来,站在走廊上问:“长顺,谁来呀?”仆人转头回答:“是老爷的学生。”
戴长贞赶紧说:“哦。大冷的天,先让人家孩子进来嘛!”“是,太太。”仆人拉开大门,对毛泽东,“你进来吧!”
毛泽东进到院子里,垂手立在天井里,听到里屋戴长贞正对袁吉六说:“说是来跟你道歉的,人在院子里等着呢。”袁吉六气冲冲的嗓门从房间里传出:“他爱等等去!谁也没请他来!睡觉!”
话音一落,窗内的灯光骤然黑了,整个院落归入了一片宁静与黑暗,只剩了毛泽东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院子里。
夜空沉沉,星月无光,上半夜的满天星斗早已不知踪影。寒风骤起,在树梢、枝叶间呜咽,也卷起满地秋叶,掠过毛泽东一动不动的双脚。风是雨的脚,风吹雨就落。紧跟着,雨点落在了静静地伫立着的毛泽东的脸上。寒风和着秋雨,刹那间笼罩了整个院落。房檐下,雨水如根根丝带,在风的吹动下,摇摆着。不平的地面上,很快形成了许多的小水潭。全身透湿的毛泽东平静而倔强,他垂手而立,一动不动,仿佛雨中一尊雕像。他那被雨水浸透了的头发一绺绺沾在他的前额上,雨,正顺着发梢不断地滴落。他的衣裳已经湿透,一双布鞋全部被从身上滑落下的雨水浸湿……
晨曦初露时,雨终于停了。渐渐的,东方的天际,一片火红。晨光中,雨水冲刷过的大自然,是那么干净、耀眼。
袁吉六伸展着胳膊一走出卧室门,就听到毛泽东的声音:“老师。”
袁吉六扣着扣子,扫了仍然站在原地的毛泽东一眼,一言不发。
毛泽东往前走了几步,抬头正视着袁吉六逼人的目光,一字一顿地再次说:“老师,我错了,请您原谅我。”然后,深深地向袁吉六鞠了一躬。
在毛泽东身后,残留的雨水悄然灌进了两个深深的脚印里,袁吉六心里一动,威严的目光从那两个脚印移到了毛泽东身上,看到眼前的学生静静地伫立着,浑身上下都湿淋淋的,脸上却平静谦和,全无半分疲色。
良久,袁吉六接过妻子递过来的水烟壶,口气硬冷地说了声“跟我来”,便转身沿着走廊走去。
望着这一对师徒离去的背影,戴长贞笑着招呼着仆人:“去,把我昨天晚上准备好的干净衣服拿来,还有,叫厨房烧碗姜汤。”
师生俩进了袁家古色古香、四壁皆书的书房。袁吉六将水烟壶往毛泽东手上一塞,说:“拿着。”然后他踮起脚,小心翼翼地从书架上端取下了厚厚的一整套线装古书——那是一套足足二十多本的《韩昌黎全集》。
“古文之兴,盛于唐宋,唐宋八大家,又以昌黎先生开千古文风之滥觞,读通了韩文,就读通了古文,也就懂得了什么是真文章。你的文章,缺的就是古之大家的凝练、平稳、含蓄、从容,如满弦之弓,只张不弛,令人全无回味。这是作文的大忌!这套韩昌黎全集是先父留给我的,里面有我几十年读此书留下的笔记心得,今天我借给你,希望你认真读,用心读,读懂什么是真正的千古文章!”
“是,老师。”
“遇到问题,只管来找我,我袁吉六家的门,你随时可以进,这间书房里所有的书,你也随时可以看,但有一条,毛病不改正,文章不进步,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袁吉六炯炯的目光注视下,毛泽东用力点着头:“放心吧,老师!”
三
袁老师的课,毛泽东这段时间是突飞猛进,可其他课,毛泽东就没这么幸运了。
饶伯斯的英语课毛泽东还勉强过得去,美术课上他看其他科目的书,黄澎涛老师也能容忍,但在费尔廉老师的音乐课上,他那五音不全的大嗓门可就让他出尽了风头:他一跑调,隔壁几个班的同学全能听到,引来一片又一片哄笑,常常打断隔壁班老师的讲课。当然,这些还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他的数学和理化成绩不理想。没有办法,每次完成数学和理化作业,他都必须请教蔡和森跟萧三他们。
这天晚上,他又抱着课本到了六班寝室。蔡和森去教室自习了,只有萧三在。两人约定,萧三先给他讲,讲了之后,毛泽东先自己做题,实在做不出来,再问萧三。萧三也不离开,就在旁边看书陪着他。
“X加2Y等于X的平方,Y减X又等于……”毛泽东眉头紧锁,一副绞尽脑汁的苦相,一边做题还一边念念有词。
萧三把手里的书一放:“你做就做,一晚上老念什么念?”
“好好好,不念不念。”毛泽东苦着脸,继续做着题目。过了好半天,他终于把笔一放,长出了一口气,说:“哎呀呀呀,总算搞完了。哎,你看看,这回应该搞对了吧?”
萧三接过作业本,逐一检查着。这个严厉的小老师看着看着,眉头皱起来了,脑袋一摇,把本子往毛泽东面前一塞,说:“润之哥,怎么回事啊你?”
“怎么,还有错的?是哪一道?”毛泽东嬉皮笑脸地问。
“哪一道?七道题搞错五道!总共两个公式,一晚上都跟你讲三遍了,第一遍你错七道,第二遍你错六道,第三遍你还要错五道,你说你怎么得了哟!”
“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我还烦得死咧!什么鸡兔同笼,和尚分饼,一元二次,二元一次,鬼搞得它清?”毛泽东把作业本一摔,长叹一声,他显然也烦得够呛。
“那你老是搞不清,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萧三问。
毛泽东摇了摇头,仰头倒在了萧三床上。
萧三又翻开了数学课本,没奈何地说:“算了算了,我再跟你讲最后一遍。”
毛泽东强打着精神,支撑起身体,却无意间看见了萧三床头的一本《读史方舆纪要》。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读史方舆纪要》?哎呀,这可是好书啊!”
萧三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一把把书抢了过来:“哎!不行不行,这书不能给你。”
“我看看怕什么?”
“我还不知道你啊?看着看着就看到你手上去了。不准动啊。”
“我看一下,就借三两天,两天可以了吧?”毛泽东哀求着。
“一天都不行。”萧三护着书。
“子暲,你不是那么小器的人吧?”
“不是我小器。这是我哥的书,我刚拿过来的,他专门叮嘱了,不能借给你。”
毛泽东:“怎么就不能借给我呢?哦,我借他的书什么时候不还了?”
“你倒是还,还回来还是书吗?”他随手抓起床上两本书,翻动着,书上天头地脚到处都是墨迹:“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你还回来的书,结果呢?上面写的字比书上的字还多,搞得我们哥俩都不晓得该看书上的字还是你写的字了。”
“读书嘛,还不总要做点笔记?”
“那你不会找个本子写啊?非要往书上写?我不管,反正我哥说了,什么都可以借给你,就是书不行。”
“你哥讲了是你哥讲了,你可以通融一下嘛,我们两个还不好讲话——这回我保证不往书上写了,悄悄借,悄悄还,不让那个菩萨晓得,这总可以了吧?”
“你会不写?我才不信呢。”
“我保证!我,向袁大总统保证!”
毛泽东把手伸到了萧三面前,脸上全是讨好的笑容。望着他,萧三满是无奈:“你到底是来补数学的,还是补历史的?”
四
毛泽东的作文终于让袁吉六满意了,最近的一篇作文,袁吉六居然给他打了满分,还批了大大的两个字:“传阅”。
这篇带着鲜红的“传阅”与满分成绩的作文,豁然张贴在一师公示栏的正中央。吸引着众多学生挤在公示栏前,争相阅读。何叔衡也挤在人群中,扶着眼镜仔细地读着,边读还边忍不住直点头。
何叔衡读了毛泽东的满分作文,满脑子装的都是毛泽东,心里对这个比自己小了近20岁的年轻人钦佩不已。却不想从公示栏回来,一踏进讲习科寝室 ,正听到有人在说毛泽东。
“我说了,什么都可以借,就是不能借书给他!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又成什么样子了?他保证不写,他毛泽东的保证你也信?他那身毛病,一看得激动起来,管他谁的书,反正是一顿乱抒发感慨,你又不是不知道!”
何叔衡笑说:“子升兄,是什么书啊?能不能借我看看?”子升把书往他手里一递,“送给你了!”
何叔衡接过来一看,是本《读史方舆纪要》,随手翻开,上面天头地脚又到处是墨迹,不觉好笑。这时子升拉开抽屉,取出几张空白描红纸,气冲冲地提笔在纸上的示范格写起偏旁来,感觉有些莫名其妙:难道他还需要练字吗?便好奇地问:“子升兄,你写这个干什么?”
子升没做声。萧三赶紧解释:“是这样,润之哥正在练字,我哥每天都给他示范几张,好让他照着练。”望着子升一面带着气,一面一笔一画,精雕细刻,何叔衡忍不住笑了。
子升看了何叔衡和萧三一眼,自己也不禁笑了,无可奈何地说:“交错了朋友,算我倒霉,行了吧?”
何叔衡在子升一边坐下,读那本《读史方舆纪要》。他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分辨着天头地脚上毛泽东潦草的字迹,与书上的内容作着对照。翻过一页时,他又寻找着上一页毛泽东未写完的评语,再翻回来对照着,不住地点头。不一会他便向毛泽东的寝室走来。
“烦死了!” 何叔衡远远便听见一个声音。看见寝室里的桌子上,摊着课本、作业本,一个人正用圆规、直尺照着书画几何图形。左量右量,怎么画都跟书上对不上,烦得把尺一扔,却又碰掉了铅笔,铅笔滚到了床下。他嘟哝了一句,俯下身来捡铅笔,但铅笔滚到了床底,他只得尽量趴下去,使劲探着手臂。
何叔衡不觉疑惑,问道:“请问毛泽东同学在吗?”“我就是,等一下啊。”那人探着手使劲地够着,总算够到了那支铅笔,从床底下钻了出来,拍打着满头满手的灰尘。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手里还拿着那本书的老大哥,只觉得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名字了,喃喃地问:“你不是那个?”“何叔衡,讲习科的。”
“哦,对对对,何兄找我有事?”“我刚才看了毛兄公示的范文,还有这本书上的笔记,毛兄的知识之广,见解之深,立言之大胆,思索之缜密,令我非常佩服,真的,佩服之至。我有一个冒昧的想法,希望今后能多多来向毛兄求教。不知毛兄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
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拍拍后脑勺说:“你看你这是怎么说的?你是老大哥嘛,我那点本事算什么?”
“学问、见识,不以年龄论短长,我虽虚长几岁,却是远不及毛兄。今天,我确实是诚心诚意,来向毛兄讨教的。”何叔衡的态度非常恳切。
毛泽东不喜欢客套,很爽快地向何叔衡伸出手来,说:“都是同学,有什么讨教不讨教?这样吧,我们交个朋友,以后,多多交流。”一老一少,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