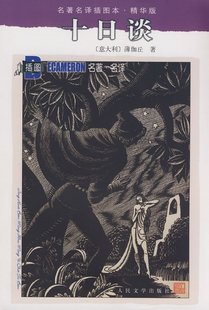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识基础的。还是那句话:一个社会中,某一部分与当今时代思想意识不同的人,特
别是形成帮派或集团的人,他们要把历史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倒退,他们带给人民的
是幸福还是灾难,是判断黑道还是白道的主要标准。白道意味着科学、进步、民主、
正派、光明;黑道意味着迷信、落后、愚昧、专制、黑暗。
根据这样的认识,不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尽管也号称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实际上却是江青和康生之流的娼妓和特务分子在操纵,是
地地道道的黑道当政,是变相的黑社会势力在大陆死灰复燃。中国共产党党内有派,
这不是秘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先进的革命派被打倒了,落后的
反动派篡夺了党政大权,把一个革命的政党,几乎变成了封建帮派。他们的统治,
其实是黑社会帮派式的统治,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我这样说的根据:第一,
它充满了迷信、落后、愚昧、野蛮、专制和黑暗。所谓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有的本
身就是地痞流氓,他们完全继承了封建帮主的那一套,其所作所为,包括组织系统、
等级制度、家长式统治、独断独行、飞扬跋扈、以强凌弱、打击异己、疯狂报复、
残酷的非刑……等等一系列表现,完全是黑社会帮派式的。有许多连黑社会帮派都
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甚至公开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给黑
社会帮派的形式披上一件“革命”的合法外衣,行黑社会帮派体系统治之实。第二,
整个“文化大革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从中得到好处,而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
来的只有痛苦和灾难。第三,它的流毒与恶果,将影响中国两代到三代人的素质与
社会风气,今天中国大陆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各种犯罪团伙,正是这些黑帮们的流
毒,有的就是他们直接培养扶植起来的。
这样的论点,当然也只是我一个人的,别人,特别是大陆的人,还没有也不敢
有这样尖锐的提法。
我这样笼统地、抽象地说,对你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未免太空洞、
太遥远也太难以理解了。还是结合我自己本人的故事,跟你形象地说明吧。
我祖籍中国江南山区,世代务农。我祖父从小天资聪颖,是吴家唯一的一个读
书人。他青年时代,思想进步,暗中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中
组织光复军,参与了江南一些城市的光复。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军政府工作了一个时
期,不久就继续上大学念书。二十年代从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参加北伐军,当上了
团党代表,一直打到了北京。北伐完成后定居上海,挂牌当律师。抗战军兴,我爷
爷自己奔赴抗日前线当军法处处长,让当时正在工学院念书的儿子也就是我爸爸投
笔从戎,报考中央军校。为了报效祖国,父子两人几乎同时投军,上了前线。抗战
胜利以后,父子二人又先后退伍,我祖父继续当律师,我父亲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人开业的律师被取消了。好在我爷爷是民主人士,又是法律
界的名人,政府部门组织他学习了一段时间,就被安排在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
我爸爸在厂里也有创造发明,升任了工程师。1952年,我在上海出生。我妈妈是个
女医生。
从哪一个角度说,我家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至少不是反动的。
但是我外公家是地主。其实地也不多,就二十多亩。在中国江南,土地虽然比
不上湄南河三角洲,也还是比较肥沃的,每亩地能收租谷500 市斤,合250 公斤。
全部租谷,一共五吨,一辆大卡车就运走了。这点儿粮食,对已经从经营土地发展
到经营工商业的江南地主来说,不算一回事儿。因为我外公主要靠在县城开布店和
织布厂赚钱。
我还有个舅舅,也是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本来在部队里当军需主任,抗战胜
利后在武汉当某军的留守处处处长。是他先认识我爸爸,后来才把他妹妹也就是我
妈妈介绍给我爸爸的。1948年5 月,我爸爸和我妈妈在上海结婚。1949年4 月,我
舅舅奉命撤退到台湾。后来退伍了,在九龙开了一家饭店。1950年江南开始土地改
革,我外公把全部土地都主动交出,被评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斗争。他觉得
自己年纪已经大了,戴着一顶地主帽子,生意也不好做,儿子在台湾,没有任何消
息,女儿在上海,即将生育,正写信来要老伴儿到上海照顾她。于是他干脆把布厂
和商店都关了,在1952年带着一些积蓄,到上海来与女儿一起生活。
一直到1955年,我一家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劳动,都平安无事。我外公、
外婆照顾着我,他们的户口也都从农村迁来上海了。
到了1955年,大陆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不是由公安、司法机
关办案,而是由各机关、企业、厂矿通过群众提意见的方式来“挖掘”。
我父亲本来就是个大学生,只因为抗战上了前线,应该说,他不是勇士也是
“爱国将士”,而且是尽人皆知的,本来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根本就挂不上钩
儿。可是群众一“挖掘”,首先把我父亲挖掘出来了。口口声声,只问我父亲为什
么不跟蒋介石到台湾去。我父亲说:他是学工的,他的事业在工厂,不在军队,抗
战期间当兵打仗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是爱国行为。积极分子们就问他:“你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特别是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谁敢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只好承认自己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啰。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用三段论证法来批驳我父亲:“大前提:
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是唯利是图。为了赚钱,他们是连祖宗都可以出卖的。小前提:
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结论:你的阶级特性注定你只能
去当汉奸,你是不可能爱国的。再不然,你去当兵,就是为了想当官,好骑在人民
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因此,很可能你就是一个潜伏的特务。”
您别笑,像这样的逻辑,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但没人笑,而且被奉为经
典的至理名言,被当作唯一标准,可以用来分析一切是非曲直的。
我父亲据理力争,当然不会有人听他。幸亏经过内查外调,他确实是上着大学
去参加抗战的,抗战结束,以上尉副营长的军衔复员,以后继续从事本行业务,没
有血债,也没有罪恶。仅仅因为他是个国民党员,是“连以上伪军官”,最后被定
了一个“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本来因为他有创造发明,技术部门原计划提升
他为副总工程师的打算,也因为“控制使用”而取消了。
好在我爸爸认定自己是“凭本事吃饭”的人,对于这种是非颠倒的“光荣称号”,
本来就不太计较,也无法计较,只是苦笑一声,也就算了。
可是我妈妈却想不通。1957年,大陆又开展“整顿党风”的运动。本来这是共
产党内部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很诚恳地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母亲也就很诚恳地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我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太冤枉了。在抗日战争那
个历史时期,只要是抗日的,就都是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好,所谓征求党外
人士的意见,本来就是一个“阳谋”,要的就是你这样一条意见。联系到她父亲是
地主兼资本家,哥哥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丈夫又有历史问题,认定她是阶级异
己分子反攻倒算,经过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生活最苦的苏
北农村劳动改造去了。幸亏她是个医生,没干多久的农活儿,农村人民公社成立,
就让她到乡村医院当医生去了。
从此,我父母被人为地分隔在两个地方,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也因此我母亲
没有再生育。而我还没有上小学,就等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母爱。
1960年,中国大陆因为天灾人祸,主要是“瞎指挥”和贪大喜功、虚报产量,
造成特大浪费,于是出现了特大饥荒,到处饿死人。苏北农村生活本来就苦,一闹
饥荒,老百姓连糠都吃不上了。我们在上海,生活比别的地方还好一些,但也是什
么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一家还不能不节衣缩食,从已经很少的口粮定量中节省出一
些来,接济我母亲。
1965年,我母亲经过八年的劳动锻炼,总算“改造好了”,给她摘了右派帽子,
把户口迁回上海。但是还不能让她当医生,只能让她到挂号室当挂号员。
对我们一家来说,只要她能回来,大家都念阿弥陀佛,关于职务高低、工资多
少,都不去计较了。
1966年暑假,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开始了。我家从此陷入了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悲惨境地。
首先遭殃的是我外公、外婆。革命派说他们是“逃避改造的地主分子”,没收
他们的全部存款,把他们押解回原籍,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还什么也不许带,只
准许他们带一床被子和几件替换的衣裳。那一年,我外公、外婆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说起来虽然都是农村出身的人,可一天农活儿也没干过。到了农村,只能参加积肥
组干点儿轻活儿,每天所得的“工分儿”,只够喝粥的。天天晚上还要挨批斗,不
挨批斗也要陪斗,没有一天消停的日子。没过几年,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接着遭殃的是我爷爷。当时他虽然年纪已经很大,早就离开了法律顾问处,但
仍在市政府的政法研究小组挂一个“组员”的名义,有时候去开开会,讨论一些司
法方面的政策性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革命派”就说他是“反动学术权
威”,先贴他的大字报,接着拉出来批斗。他们采用“形而上学”的逻辑,问我爷
爷:“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判错的案子没有?”我爷爷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知道自己不是圣贤,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没有一万件也有几千件,怎敢说连一件也
没有判错的?他刚答应了一声“那当然有”,“革命派”就递给他三张纸、一支笔
要他写交待:要写出判错的都是什么案子,为什么要错判,被错判的都是什么人。
我爷爷说:“说有,那只是估计而言。如果自己明明知道是错判的,还要那样判,
岂不是明知故犯了?”他们说我爷爷态度恶劣,抗拒交待,“呸”地一声一口唾沫
吐在他的脸上,继续批斗。
如果我爷爷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革命派们”当然要说他不虚心,不实事
求是,结果依旧是继续批斗。
总之,那时候是只讲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许讲理的。这一点,连封
建帮会都不会这样干。
我爷爷一辈子光明磊落,仕途通达,没有受到过任何侮辱,如今当众被乳臭未
干的小辈唾面自干,无法忍受,当天夜里一根绳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们发现的时
候,早已经断气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张白纸写了“士可杀不可辱”六个脑袋大的字,这是他的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