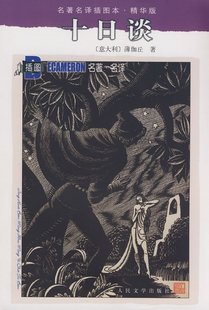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玛妮走了以后,吴永刚仰靠在椅子上,抽了一支烟。他并没有烟瘾,每逢遇上
烦恼,遇上伤脑筋的事情,他就抽一颗,无非借这烟雾缭绕增加一点儿思绪。他说
不清自己怎么忽然会对泰国的妓女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欲望。他在九龙生活了十几年,
尽管自己对旅馆业不感兴趣,可是阴差阳错的,命运迫使他非干这一行不可,到美
国专修旅馆管理业,回香港后从舅舅手上接过了玉龙大饭店来,经营了好几年,成
绩居然还算不错。玉龙饭店虽然不在九龙红灯区,可是在那个世界中,妓女与饭店
有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互利关系。在那里,他从练习生当起,当过经理秘书、襄理、
财务部主任直到舅舅认为他已经成熟,可以出山了,让他当了副总经理。十几年间,
他见识过的妓女,没有一千也足有八百了。在他舅舅的言传身教之下,他全盘接受
了舅舅的观点:作为一个大饭店的老板,也算是“上流社会”的人物,绝对不能入
黑道;但是他开的是饭店,与黑道及下流社会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然,这饭店
就无法开张。因此,他只能学一个“中庸之道”,在夹缝中求生,采取“敬鬼神而
远之”的对策。在妓女这个问题上,第一不能排斥妓女,第二绝不能沾上妓女,第
三更不能养妓女。因此,多年来,他只和妓女打交道而不和妓女交朋友。每个妓女
见了他都笑脸相迎,也都恭恭敬敬,彼此之间,谁也不多越雷池一步。如此和平共
处的结果,是他只认识妓女的外表,而不了解妓女的内心。当然,能在玉龙饭店进
出的妓女,都是比较高级的,有的被称为“交际花”,有的是时装模特儿,有的还
是这种“星”那种“星”,她们长年在饭店里包租一套房间,只和一两个有钱的大
佬来往。香港、九龙的妓女,特别是高级妓女,手面阔绰,生活奢华,即便有一本
苦经,也是不可告人或不愿告人的“隐私”,轻易不会真实地告诉别人。除非是特
殊关系或特殊需要,例如和某人有了真正的爱情,或发生了大案、要案,为了洗清
自己,不得不在法官或律师面前和盘托出自己的身世。
没有想到的是,他花了一笔与妓女过夜的钱,却从玛妮的口中听到了一个泰国
山区旅店女招待的可悲身世。他想:香港、九龙的下等妓女,大概也都有这种被逼
为娼的悲惨故事吧。
他这一次来泰国,是和贡叻先生洽谈业务合作项目的。雨季进山,也不是为了
考察民风民情,而是想寻找一个当年救过他性命又对他一往情深的泰家姑娘柳芭。
当然,现在的柳芭,也已经三十多岁,早不是什么姑娘了……
他正在浮想联翩,忽然听到房门上响起了剥啄之声。这时候大雨如注,雨点打
在房顶上和房后的芭蕉叶上,像炒豆似的噼啪作响。要不是他细心,这轻微的叩门
声,几乎被这曲天然的《雨打芭蕉》淹没了。
朝南的窗户,因为窗外就是阳台,实际上就是走廊,因此玻璃窗用的是花玻璃,
以免外人窥视房内的春色。不过这时候玻璃窗分明开着,关着的是纱窗,从窗外一
眼就能看见房内。为防蚊子进来,房门倒是关着的。因此门外的人经过窗户,已经
看见房内的一切,而房内的人却不知道站在门外的人是谁。吴永刚只当是玛妮还不
死心,想再来杀一次回马枪。可一想,她来了是不敲门的。刚才送饭送茶,都是推
门就进,好像她们这里女招待伺候客人,根本就没有敲门这种习惯。那么会是谁呢?
是不是扎嘎来通知明天几点钟上路?可扎嘎是个粗人,敲起门来,恐怕不会这样文
雅。不管他,开门看看再说。
吴永刚把房门轻轻拉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穿一身棉质
的黑缦,一块丝质的黑纱龙,从头顶一直披到肩膀,只露出一张雪白的鹅蛋脸和两
只闪闪发光的大眼睛。俗话说:若要俏,一身皂。这话也许有点儿道理。不过也有
一个前提:脸蛋儿必须长得白。在全黑的背景下,才能衬托出那白玉一样的晶莹来。
要是脸蛋儿长得像黑炭,再穿一身皂,那可真是乌鸦掉进煤堆里,分不清谁是谁了。
眼前这个女人,就很能利用这种反衬的功效,不但把自己洁白如玉的脸庞全部衬托
出来,而且显得端庄稳重,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跟玛妮那种上下色彩极
不协调的“乡下姑娘怯打扮”和一脸挑逗性的淫笑比较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两
个世界的人。一个是举止轻佻,热情似火;一个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吴先生,我可以进来么?”那人站着不动,只是怯生生地小声问。
“快请进来,你再不进来,蚊子可都进来了。”吴永刚轻松地笑笑,以冲淡刚
才自己长时间注视她的失态。
那女人走了进来,随手又把房门关上。没有再问,随即在桌子旁边的另一张椅
子上坐下了。她的坐姿比较特别:上身挺得笔直,脸却不朝向主人,而是朝向房门,
给人家看的,是一个侧面。吴永刚忽然发现,她的侧面像,比她的正面更好看,高
而直的鼻梁,简直有点儿像维纳斯。整个身子,像是大理石雕琢的,或者说像是一
尊蜡像。
直到这时候,吴永刚才想起来,她是和自己同一辆车来的。只是她在车上沉默
寡言,从早到晚没听见她说过一句话,而且总低着头。在车上,她穿的是一身灰色
的布缦。
“外面雨下得很大。”她忽然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令人不着边际。外面下
大雨,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何用你巴巴儿地跑来通知?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看
着门,好像在自言自语,其实,明明是说给吴永刚听的。
“是,雨是下得很大。”他的回答也有些不着边际。其实,是他贪婪地在欣赏
她这庄重的姿态和极美的侧面像,因此随口答应,有口无心。
“我住的房间,漏了。嘀嗒嘀嗒的,听得人心烦。地板上都是水。”她像在诉
苦,又像在解释她为什么夤夜敲门,而且房内住的,又是一个单身的男子。
“是吗?”连他自己都奇怪,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废话来。
“不信,你去看看,我就住在你隔壁。”
“哦哦,不用了。这种小旅店,店房年久失修,也不奇怪。”
“我想在您这儿坐一会儿。”
“房间漏了,找老板换一间嘛!”
“您不欢迎我?怕我打搅您?怕我妨碍您?”这时候,她才转过身来,面向吴
永刚,而且两眼深沉地注视着他,长长的眼睫毛,一眨也不眨。又是一种特殊的美。
“哪里,哪里!欢迎,欢迎得很哩!”吴永刚有些惶恐了。他暗暗埋怨自己怎
么这样不会说话,急忙转圜。“我正说长夜漫漫,无法消除寂寞呢,有您来聊聊天
儿,太好了。”
“刚才,那个叫玛妮的姑娘,不是一直在您这里呆着,还给您唱了歌、跳了舞,
您艳福不浅嘛,难道还寂寞么?”
“是,是。她是在这里坐了一会儿。她是旅店的招待,是专门伺候客人的。”
也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说话有些支支吾吾的,言不由衷。
“应该说,她是专门伺候男客人的。从您的房间出来,她又进了我隔壁的房间。
那房间分明没漏,可我的房间漏得哗哗的。她从我窗前经过,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是吗?”他嘴里随口答应着,心里却在想:这个玛妮,我好心好意放她一夜
假,让她好好儿歇一夜,可她偏不愿意歇着,还要去挣一份儿钱。也难怪,那是她
的职业,她是指着自己的身子赚钱的。放过该赚的钱不赚,岂不是罪过?
“其实我也就坐一会儿,不会打搅您很久的。”她特别重读“一会儿”这三个
字,似乎在暗讽吴永刚方才说的“玛妮是在我这里坐了一会儿”的自我解嘲。“单
人房间已经没有了。除了您这间头等的,二等客房一共只有六间,我占的是最后一
间。要换,只能去住三等统铺了。其实,床位那里并不漏。我烦的是那嘀嗒声。它
令我想起童年时代我家的那间破屋子。”
“哦,哦!”他不敢随便表态了。怕再次被她抓住什么,令自己难堪,甚至下
不来台。
“我叫娜达莎。”她见吴永刚被自己噎得有些难堪,也不敢动问她芳名,只好
自报家门了。
“您是俄罗斯人?”他有些惊讶。
“不,我是泰国人。不过我奶奶是俄罗斯人。尽管我有一个泰族人的名字叫
‘娜达’,可我奶奶总叫我‘娜达莎’。”
听她这样一说,他倒不感到惊讶了。原来她是一个隔代的混血儿,难怪她的皮
肤这样白皙,又有一个既高且直的鼻梁!
“请恕我冒昧,我猜想,您奶奶一定是俄罗斯贵族吧?”
“不错。她出生在俄罗斯大公的贵族家庭,还是一个小公主呢!不过她从懂事
以后,就没享到贵族的福,而是在颠沛流离中穷困地度过了她凄凉的一生。俄罗斯
革命以后,她父亲带领军队上了前线,让她和全家人随着大管家离开莫斯科,撤退
到西伯利亚。那一年,她只有七岁呀!不久,她父亲死在战场上,她只好随管家流
浪到中国的东北,后来又流落到越南、泰国,在酒吧间里卖过唱,最后被大管家卖
到歌舞团里当个小演员。我出世的时候,我奶奶已经老了。我爸爸是一半儿泰国人
一半儿俄国人,我妈妈是日本歌舞伎,所以我从小既会泰族歌舞,也会俄罗斯歌舞,
还会日本歌舞。歌舞团的人,不论大小,都很喜欢我。他们给我起了个艺名叫‘百
灵鸟’。”
“这样算起来,您是二分之一的泰国血统,四分之一的俄国血统,四分之一的
日本血统。不过从性格看,您继承的是日本女性的温柔文静,而不是俄罗斯女子的
热情奔放。”
“是吗?您真这样认为?热情嘛,有人热在心里,有人热在外表。您喜欢的热
情,大概是外向的奔放型。我是个热在心里的人,不过要奔放,也很容易的,我马
上可以热情一下给您看。”
说着,她站了起来,把披在头上和肩上的大纱龙一摘,旋风似的在地板中心跳
了一曲急促奔放的热情波尔卡。没有伴奏的音乐,她就两手捻着脆响的“榧子”作
为节拍,嘴里轻轻地哼着优美的主旋律,脸上的笑容随着节奏的加快而逐渐绽开绽
开,终于开成一支鲜红欲滴艳丽芬芳的花朵,妩媚万分;目光左右顾盼,如寒星,
如流萤;腰枝轻柔扭动,如柳摆,如蛇行;特别是两条雪白的玉臂,每一挥动,每
一上举,哪怕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所传达的,都是她如火的激情。整个舞蹈,动
中有静,刚中有柔,热得像一盆火,几乎能把人的心儿熔化,但并不失优美与和谐,
依旧是婀娜一曲婆娑舞,而不是痴女发疯学颠狂。跟玛妮那扭捏作态的摇摆晃动比
较起来,又是一个天上地下。这见所未见的艳舞,看得吴永刚眼睛都直了,不由得
站了起来,心里赞叹:啊,真正的玉树临风,果然是翩若惊鸿,舞蹈中的娜达莎,
与马车上的娜达莎,与刚进门时的娜达莎,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
吴永刚正在恍惚迷离中,冷不防娜达莎一个旋风,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