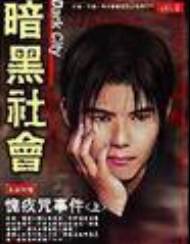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liv
以上诸氏之兴立,可分四期,以栾、韩二氏兴立最早,鲁桓公2年,栾宾为封曲沃桓叔之傅,桓公3年,韩万御戎,此为第一期;赵、魏、范、、狐、羊舌氏之立则都在晋献公年间,此为第二期;晋文公期间则有中行、先、胥氏之立,而赵、狐二氏力量也在此时迅速壮大,此为第三期;最后,鲁宣公至成公年间,则有知氏、祁氏之立,是为第四期。
以上诸氏之废亦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鲁文公6年狐射姑因与赵盾冲突而奔狄,宣公13年,先氏以战败被废;第二期是鲁成公17年晋厉公用胥童杀三而被弑,而胥童亦随之被杀,、胥二氏均灭,而栾氏也在襄23年被废;第三期是昭公28年羊舌氏与祁氏被废;第四期是范氏、中行氏于哀公5年奔齐而被废。至春秋左传纪年终(前468年),晋国只剩下赵、韩、魏、知四大卿族(知氏后被三家灭于前453年)。
赵氏与晋国其他世族的关系则颇有一张一弛、一逼一让之势。赵衰甚让,赵盾则已有逼人之势,至赵同等则已相当倨傲,赵氏不久亦罹祸;至赵武则又颇温良恭俭让,赵鞅却咄咄逼人,赵无恤外柔而实刚,颇能“忍耻”,故最后反联合韩、魏而灭了知氏。
赵盾于赵衰死后即与狐偃之子狐射姑(贾季)产生矛盾,狐、赵同为文公旧勋,赵盾得阳处父支持而取代狐射姑为中军,两人又在立君问题上发生冲突,狐射姑杀阳处父而后奔狄,狐氏遂废,但赵盾还是派人把狐射姑的妻室送去,以示礼貌,当文公13年中行桓子建议请复狐射姑时,赵盾却没有同意。狐射姑对赵衰、赵盾父子的评价是∶赵衰是“冬日之日”,赵盾是“夏日之日”,杜预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lv
鲁成公8年赵庄姬之难时,庄姬谮告晋侯赵氏将为乱,栾氏和氏做了不利于赵氏的假证词,使赵氏几乎覆灭,幸赖韩厥得以渡过危机。韩厥小时为赵盾所待养,故此有这份情谊。lvi 后来,赵、韩两家的关系一直相当不错。后来定公13年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均违君命而行火并,结果范氏、中行氏被逐,赵氏却赖韩魏两家向晋侯请求而得无事。
世族之延,固然首先在继承者得人,同时也靠时运。一起一伏常常反而胜过直线上升。“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一族发展过速反易招致君主猜疑和他族忌恨,昭子“富半公室”,“家半三军”,氏一氏曾有三卿五大夫,却一朝覆亡;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不久却亦及难;范宣子在其盛时畅谈本氏的“死而不朽”,然而范氏隔世亦亡。赵氏的绵延壮大有起有伏,有进有退,结果反而避开了一些最容易招致祸难的时期和事件。赵氏的两次危机都是由内部而起,一次因赵庄姬之谗,一次因邯郸午不肯允诺,而其家臣却甚忠,与季氏家臣颇不同,董安于告赵鞅先备难,后又为防知氏发难、安定赵氏而自尽。各大家族又常联合起来对付公室,晋厉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亲信,结果自己反而被弑;后晋六卿为削弱公室,又尽灭晋之宗家祁氏、羊舌氏,把它们的采邑分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在公室大大削弱之后,六大卿族之间的兼并转趋激烈。赵氏以晋阳为后盾,终立于不败之地。赵氏的结局则已为所知,赵转成诸侯后亦是三晋中的最强者,在战国时与强秦抗衡最久最力。
总观春秋列国,非公族的发展看来超过公族,随着公族的普遍积弱,非公族却有几家脱颖而出,呈现出趋强之势。公族占优势的鲁、郑、卫、宋到战国时代均已成蕞尔小邦。而瓜分强晋的三家中,赵、魏二氏均非公族,韩氏也只是桓庄之族的劫余,与异姓的赵氏关系最好,齐国则是由外来的陈氏夺国,这几个由世家转变成的国家还要在战国时代上演二百多年轰轰烈烈的戏剧再告消亡。要未上升为诸侯,要未解体为个人,这就是春秋世族的命运。春秋末年已不存在一定数量的世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形势。任何一个再高贵的家族,任何一种再优越的血统,也不可能永久占有世间的荣华富贵。毋庸下溯很远,迄至春秋之末,无论公族还是非公族,绝大部分显见已脱不了烟消云散的命运,覆灭之劫,百难逃一,正印证了帕累托(Pareto)“历史是贵族的坟场”的名言。lvii世家大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正是时间,是它们本身的延续。即便它们不面临整个世袭社会的覆灭,它们也会被另一些新兴的世家大族所代替或凌驾。然而,在历史上,又确实有一些时代,这些时代由于各种机缘使贵族得以产生或异常活跃,春秋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对这样一些时代,我们又可以说:“历史是贵族的摇篮”或者“时代是贵族的舞台”。
上一页|回目录|下一页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五、世族的文化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世袭社会》 《选举社会》
第四章 春秋社会的世族
五、世族的文化
世袭社会的文化主要呈现为贵族的文化。假如春秋贵族要面对后人为自己辩护,优雅的文化大概是他们最可能援引的一个理由。贵族文化在春秋时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最盛期又在襄、昭年间,随后就渐趋枯萎。
周代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象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传统社会是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lviii 所以,我们下面要联系人来观察那时的几种主要文化活动,例如“赋诗”以赵文子,“观乐”以季札,“有辞”以子产,“有言”以几个集体参加的场合,所系的时间主要在赵文子执政的八年(襄公25年—昭公元年)。那几年正是贵族文化奏出自己的华彩乐章的时期,也是世家大族的几位顶尖人物最为活跃,并且相当频繁地互相来往的时期。
1。赋诗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赋诗现象,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文献,且迄今仍不断有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陆续发表。lix 何为“赋诗”?我们观察“赋”字在《左传》中的用法,“赋”字共104见,其中与诗有关的79见。这79次赋诗似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简单说明创作的由来,如隐公3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公2年:“郑人为之赋《清人》”,这里的“赋”即“创作”的意思,所赋诗是《诗经》中的诗。
第二类则不仅是简单交代这种自我创作,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或独处、或面对的创作场景,所作诗亦非《诗经》中的诗,如隐公元年郑伯庄公入隧道见母亲,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出而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这是面对;又如僖公5年,晋士在晋献公、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之间感到无所适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是独自。虽然这种赋诗有时是面对他人,但还是以自我创作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是,上述两类赋诗仅见5次,且都是出现在春秋初年。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赋诗”主要是指第三类∶即一种引用已有的他人所作的诗篇(一般都见于现存《诗经》),并且在面对他人的场景中抑扬顿挫地将其呤咏出来的活动。
这种赋诗不同于自我创作,自我表达,自我尽兴的赋诗。诗是别人作的,赋诗之意也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心志和感情,而并非是要自我表现和尽兴,所以,这种赋诗总是要面对同等身份、可以交流的他人,它必须要在一个有他人在的场景中发生。也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这种赋诗也有别于表演性质的“歌诗”和言谈评论中的“引诗”。“歌诗”一般是由专门的乐工进行,并常伴以舞乐,应当说在艺术形式上肯定会更精致,更好看,但是,“歌诗”之意并不在使表演者自己与观赏者沟通。观者在这种“歌诗”中所欣赏、或者受感动的,并不是作为表演者的那个人,而是所表演的诗篇及表演本身,或者说,他最多会赞扬表演者的技巧,但并不接触到他更深的人格和价值。因为,作为“歌诗”表演者的乐工,并不具备与观赏者沟通和交流的同等身份,而“赋诗者”与“听赋诗”者则都是同等身份的君侯和卿大夫,他们往往同时既是咏者又是听者,他们此时所渴望的是相互沟通,而不是单纯欣赏。
赋诗也不同于“引诗”。“引诗”可以出现在与他人当时的谈话中,也可以是在事后“君子”的评论中,而即便是在当时的谈话中,“引诗”也主要是引用诗句来说明自己的理由,加强自己的论点,如果说有交流,那也是更偏于理性的说服,而非感情的沟通,且“引诗”不拘场合、形式、礼仪,也不具表演性质,不必抑扬顿挫的呤咏。
因此,赋诗既是一种讲究身份的交往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讲究形式和韵味的艺术活动。作为赋诗者,如何根据场合,根据听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诗篇;如何优雅地将其诵咏出来;作为听者,如何从诗句及其诵咏理解赋诗者的心志和感情并做出得体的反应,如何揖让进退,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些都涉及到一种文化的修养,涉及到一种精微的领悟力和判断力。于是,在这样的场合,最高的权威就常常并不是在场的权位最高者,而是最富文化修养者,此时的臣下,甚至能够根据自己对诗意的理解,而命令自己的君主作出某些反应。例如,前述僖公23年,赵衰听了秦穆公的赋诗之后,立即命自己的主人公子重耳降拜;又如襄公26年,叔向听完齐侯、郑伯二相的赋诗后命晋侯拜二君表示感谢。卿大夫中不懂诗者常常遭到讥刺,例如齐国权臣庆封于襄公27年、28年两次见到鲁国叔孙穆子,第一次他是聘鲁,叔孙穆子亲赋《相鼠》一诗,讥其失礼,他不知道,庆封回国不久即被逐;他第二次奔鲁时,叔孙穆子则仅使乐工为之诵《茅鸱》一诗,刺其不敬,他仍懵然无知,叔孙穆子说他将有“天殃”,将被“聚而歼之”。而能解诗赋诗者则受到称赞,楚国罢参加晋侯的享礼宴饮将要退出时,赋了《既醉》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