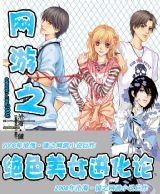������-��6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ȥ������Ȼ���ڶ��֡���������֡��͡������ݾ͡������͡������ͺ��ͣ����ü�����ȥ��ֻ�е�һ�֡��͡�����ƽ�ͺ���͡������ӿ������Ը��е�����ʿ��˵�Ʋ����ڸ߾͵����⣬����ʿ���ź�����������е��ܳ����������ǡ�������֮������̹֮Ȼ������֮�˵�Ŀ�ľ����ھ����������Զ�����������ԣ��ڶ��֡��͡����ǵȴ�������������֮�����������֡��͡���ֻ�����������������Ӳ������Խ���Ϊ����������ˣ�ֻ�Ǵ�ʱӦ��������ӱ����Ǹ���ƶ������Ը�������ػ��ء���С���������ڳ�����ʱ��Ȼ��Ҫ��ְ����������˼������λ������λ�����Ըߣ���Ҳ�������أ����������������������ų��˲ų��֣�����ְ��Ȩ������������ߵģ�ʧְ��Ӧ����ȥְ�����ԣ�������ʱ���ԳƲ������������������ԡ��ۡ�Ҳ�����ԡ��١���������ʱ�ž���֮�����롨��ٹ�ݶ��С�����
����ΪʲôҪǿ�����������õĽ����ǡá�����֮���Աش��˾��¾�����������ߣ�������Ϊ���������ֵ�֮�IJ����ǣ���������ΪҲ����26�����һ�ֶ�ʿ�ˣ����������ص���˼�����ԣ���˵��˼��������ߵذѸ��������ʹ�߸ϳ����ţ���������������Ͷ�����֮�����������Ϊı�������˵���Ϊ���������������ӡ���������������������ʥ��֮ѧ����ϰ����ҵ�����Ա�õ�ٺ»������˫�ס���
��������˵����֮����Ϊ�е�������Ҳ�С����п�֮�ˡ������ʿ�֮�ˡ��͡�����֮�ˡ��������п�֮�ˡ���������е������ˣ������൱��ǰ����˵�ĵ�һ�֡��͡������ʿ�֮�ˡ��롨����֮�ˡ������൱�ڵڶ��֡��͡���ֻ�ǡ��ʿ�֮�ˡ�������������������֮�ˡ���һ��������������Ϊ��ί����������ſ������ڵ����֡��͡����Ŵ�ʿ���������ʱ���־������桢���������������϶������ν�����ϵ��һ��������ʱ�����֡��͡���ܲ����͡������ǽ�������ԭ�������аѱ���ԭ����ʵ���ˣ����廯Ϊ�˸�Ͱ�����������˵��Ψ�����ܺ����ܶ��ˡ���ͬ��������ҲΪ������Ȩ��ԭ���������ṩ������ʥ�͵���������̸������𢡢�ջ�������Ȥ��ͬ��������������ʱ��������ͬ����˵���ӡ���˼���ӵ����ܣ�һ����һ���أ�������Ȥͬ������������ͻ������������������Ϊ���ġ����������»ݡ�������ʥ����
���������ǡ�ʥ֮���ߡ��������е����ߣ�������ǿ�ҵ�������θк͵���ԭ�������������Ա��ױ���������������Ϊ�ˣ����ĵķ����Ǵ���η�ģ��������Ǹ��˵ķ���������������Զ�������������ദ���紩�ų��³���������Ţ��һ���������ǡ�ʥ֮���ߡ�����������θ�ǿ�ҵ�ֻҪ�뵽������һ����ͨ�ϰ��յò���Ң˴֮���ĺô����ͺ������Լ������Ƶ��˹���һ�������»��ǡ�ʥ֮���ߡ������ǡ������۾�������С�١�������ʲôְ������������ܣ�����������Ҳ�߸����ˣ����ǽ��˱�����������������ദ���ֵá�����Ȼ����ȥҲ������ʹ���dz���¶�������Լ�����Ҳ����Ϊ�⡣���������ǡ�ʥ֮ʱ�ߡ������������ٶ��٣����Ծö��ã������Դ������������˶��ˡ���27��
�����ٽ���һ�����ӡ����Ӷ��ù��ķ��ࡣ���ǿ���˵�����Ľӽ��ڡ����ߡ�������������Ϊ�������ӽ��ڡ����ߡ������ڻ�����Ϊ�����»�������������ǡ���Ը������ʵ����ȴ���ǣ���Ϊ����Ϊ��Ȼ��ͣ�����ȴ�����ȷ���ĵ���ԭ��á����»ݲ�����������顨�����������˵�ǡ��е��������С������˾�Ϊ��ʥ��������һ���壬ɱһ���������½Բ�ΪҲ�����������ǵĹ�ͬ�㣬����Ϊȡ�ụ�в�ͬ��Ȼ��������Ҫע�⣬������Ȼ������ͬ�������Ӻ�������ʥ����һ����Ҫ�IJ��ü����ġ����������»����˸��Զ����ܲ�ȡ���˵���Ϊ��ʽ��������ȴ���Ը���ʱ�ˣ������ȡ�����κ�һ�˵���Ϊ��ʽ����������ʥ��������ִ�ţ����塢���Ρ���ͣ�������ȴ��ʱ���������塢���Ρ���ɺ͡��⿴������������Ϊ����ʤ��ǰ����ʥ�ĵط�����������˵�����ǡ�������ߡ���ԭ���⡨ʤ������������Ҫ�����ڡ��ǡ�������˵�����������⡨�ǡ��ġ�Ȩ�������ǡ��ܡ��ʡ����ߡ�ʥ������Լ����Ȩ��Ҳ�ܡ���������Լ�����������ǻ���ԭ��Ȩ������ԭ���������á���
�����С������ޡ�Ȩ����ɹ�ִ����ƫ�ڿ������С�Ȩ���ޡ����������Ը����Ȩ����Ҫ�С���������Ȩ��Ҫ���롨�������������ǵ�һλ�ģ��������ɿ���Ҳ������Ը������˵���ò�������֮ʿ�����ཻ���Ǿͱ�����������������ڿ����У�����ʧ֮������Ҳ��ʧ֮�ڿ���Ϊ������Ϊ��Ϊ��Ҫ����Ը��������ӽ��ڡ�ʥ֮ʱ�ߡ�����ӽ��ڡ��е�������ʵ������������Ҳȷʵ���ֱ棬���ԣ����ӡ�������������Ը����Ϊ��Ը��������£��������¡�����Ը�ǡ�ʥ�����������ǡ�ʶʱ���ߡ����������ߣ������ߣ�ò�¶��ǵ¡�����˵�á�����Щ������������ʥ�ˡ�˼�����п�Ϊ������Ը����˵�ӡ�����֮�˲�˵���˲�ʶʱ֮�࣬����Щ�ô�����˵����Բ��ʶ��֮�࣬���ɹ��ӡ���28��
����������ǿ�����Ρ���ǿ���������������ַ��������������������˴��������������������֡�����֮�ֲ��ڹ��������Բ��ڶ��ĺ�֮���������ԣ�����в����ɣ�����Ӳ����ɣ��ֶ���Ҳ����29����Ҫ���ġ���֪�ԡ���֪��á�����Ա������ӣ��������ϣ���Ī���ɡ���30���Ŀ���ԴȪ�����Լ���������ֿ���������һ�����������ģ��ؼ�����Ҫ���ϡ�������˵�����ǡ��������֡�����������Ҫ�����Լ�����ij���֮�֡á����������죬���������ˡ���Χ�ƴ˺��ĵ����������ֿ��֡á�һ�ǡ���ĸ���ڣ��ֵ��ʡ�������֮�֣�һ�ǡ�������Ӣ�Ŷ�����֮���Ľ�ѧ֮�֡������Ƕ����Կ����ǵ�һ�ֿ��ֵ����ܣ�������Ȼ����һ�����ҡ��֡������ֿ�����ȻҪ����һ���������������������ձ�ģ����ǽϾ�˽�����ʵ����������Ҽ�ʹû�����ǣ�Ҳ����һ���IJ������Ŀ�������ʲô����Ҳ��ߵģ�����ȫ�������Լ�����ġ�Ҳ����˵�������Ϊ��ᾡ��֮��ʹ�ǡ�ʱ�����������Ͷ�����������Ȼ�ǿ��Եõ����ֵġ�����������ڲ�������Ҳ����·�������������������������Ȼ��ʱ����ֻ��һ�䡣��
�������Dz�����̸���֣�Ӧ��˵������������ܶ��ԡ��õ����������ܡ��õ����Ļ��֣���ô����ʹ�����Ѿ�����������˼�Ŀ��ѣ�������Ȼ����Ҫ���������ȱ�����Ӷ�ʹ�������ܲ����ܳ�Ϊ�������õ����ܡ���ֵ���Ƴ��Ҳ����������һ��̬�ȣ������������С��������������������С�������֮��������һ��̹Ȼ��̬�ȣ�����ֹ�ǡ����費��������Ȼ������һ�ֱ���ʧ̬��������һ�ְѸ������ڵ�һ�п��ú���ܵ��Ļ�������̬�ȡ����η������������壬��˾����ࡶ����ͨ����������ʮ���꣬���½�ȡ����Ǩ�����ɼ������ֱ��ʱ�£������˱ܣ�����Ȱ������˵�á�������ţ�һ����Ŷ�����Ϊ���£��кβ��ɣ��������Զ�أ����ڱߵء���֮��̹Ȼ��ͬ�ڿ��֣����˵�һ������������Ϊ�������ƣ����������һ��ȴ������˿��ῴ����������Ң˴��ҵҲ�硨һ�㸡�ƹ�Ŀ������Ϊ�˼�Ŀ��Ѳ��ɵ�����֮���˼�ķ��������Ȼ���ص�ѹ�����ϣ��ͻ���ֹ����̹Ȼ��Ϊ���֡���
����������һ��̹Ȼ��ף���Ȼ�Ͳ����ڳ���֮������˽�����ջ���Ψ�Ե���Ϊ�顣�غ��Ժ���Ȼ��Ը֮�����������㡢���֮�����Ӹ�λ������Ҳӿ����������س���֮�������֮ʿ������֮ʿ���Լ��о���Ȩ�������е����ܹ�������ҵ������֮ʿ������������Ȼ��̸���ԣ��������Ҳ��Ȼ�ɹۣ������ѧ��������ڡ����̡���ɽ�����ӡ������������ػ�����˽ڲٽ����˸��岻�ѡ�������δ�����һ���������ͤ�֡�����֮�������˵ȶ���ֲ����ˡ��ˡ��ƶ��˾�Ӧ��ѧ��ʿƣ����ܳ�����ʷ����ͤ��˵�á������˿ɳ�������ز��ɳ��ӣ�������ʮ���̺�����ֻǷһ����������ƣ���
����������ѳ֮�ӣ���31����֮���Ǵ���������������أ��������ͨ�������������һ����ɽ��ʮ���꣬�������ʯ��֮Ϊ����ɽ������������Ի���������ҿ����棬�߳ߴ����������
��һҳ����Ŀ¼����һҳ��
������ҳ��ѧ�����������ڿγ̡����мƻ���ѧ��������ɢ������������������
������������������������������������ʿ�˳�������ʷ����
ѧ������������ѧ������������������������������������������������ѧ�����ʷ��������ѧ��������ҳ��ѧ�����������ڿγ̡����мƻ���ѧ��������ɢ�����������������������������������������ۡ���������������������Լ������������塷�������¡��ϵ����ˡ���������������������������������������������������������������������������
�����ڰ��£�ΪΪ��
�塢ʿ�˳�������ʷ������
����Ȼ�����ݹ���ʷ��������ע�����һ�����ƣ����������ص���ԭ���ʿ������Խ��Խǿ����������ǿ�����ء���ǿ����������ǿ����Ĭ���ˣ��Ȼ�롨�����ѽ����ˣ�С�������ˡ��ĸ���Ʒ���йأ�����Ҫ��������������˱仯�����������ԡá��������Ծٳ��������Ҳ����32�����Ե�ʱ������������ʿ����������̫��ɱ��ʿΪ����˵���������ͷ����߾���ɱ֮������Ѱζ���ǣ����ⷽ�棬�������ӵ����룬���Ǻ��ǵ������ں����õ���ij�̶ֳȵ�ʵ�֡���������������ʱ���־���Ϊӭ�͡�ӵ����������������Ʋϯ�����龰�����ټ�������ʱ���ֶԴ�ʿ�������ʡ������мӵ���������ܶá���̫��ɱ��ʿ�������ԣ���̫��ɱ����ȴ��ʵ�¡����Dz���˵�������������е�Խ��Խ�ѣ��˴��ص�Ҳ�IJ����ˡ���
����������˵�á��������£������Կ���������ί�ҡ���33�⿴��Ҳ����������ʿ֮�����ݱ������һ��ǡ���������������������ǵ�Ȼ�����Խ��˵��۹�������µؼ������С�����ij����������һ������ר���µľ�Ӣ�ȼ�����ᷢչ�ı�Ȼ���ƣ����Ļ��Ĵ�������չ������Ҳ������ء���������ʱ�ڣ��繫��롢����һ�����Ķ����˱Ͼ����ȿ��������������壬�����д��ɼ��������������š����š��������������Ļ����ط�չ�ˣ�Ҳ�����ˣ�ʿ�˴��������ˣ�Ҳ�����ˣ��������ܵ�������صĽ���֮·��ֻ������һ;�����������ȿֺ���֮�����ˣ����Գ�͢��ٴ�֮��������Ƿ�֮�������ƾٳ����硨�о������硨�����������ԣ����ܲ���ʶ���߶����ǣ������ݱ�ʵ�������Լ����������������а������������������ӡ���
�������������ﲻ�ٷ����������Ʋ�����ԭ���dz�����һ��ʵ�ü�ʿ֮����֮·ȷ��Խ��Խխ�����ƣ��������������Խ��ԽС�������dz���������Ϊ�����Բ��������������˻���ի˵����֮���ˣ�ֻ����»����34������вŻ���ѧ�߸�ɽ˵�á����˲�Ω����ʱ�������������ʱ���������������ѣ��ǵý�����Ҳ���˱�ƾһ־�֣���־�����У������Թ���������ݴ��գ������Ѷ�������������֮ʱ���ڹ���δ���мã��������ӡ����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