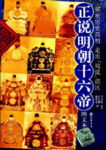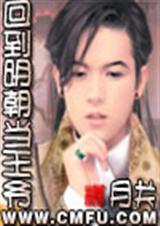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禁学令下,他视若无物,仍在湖北孝感聚众讲学。他还倡导建立独特的公社式团体,名之曰“会”,提倡在会中“老者相与以安,朋友行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因为搞这一套,他难免被一些人目为“妖人”与“狂狷”。
张居正早就认识这个特异人物。
在任国子监司业时,张居正曾在当时的御史耿定向处偶遇何心隐。何非常突兀地问他:“张公您执掌太学,可知道太学之道么?”张居正博学,却对这个“太学之道”闻所未闻,知道这是胡扯,便瞪着何心隐,没有好气地说:“你时时都想飞,却是飞不起来吧!”(《明儒学案》)
张居正走后,何心隐大感沮丧,对耿定向道:“此人能操天下柄。”又说,“你记着,此人必杀我!”
何心隐以布衣倡道,且极端狂热,这对当时处于疾苦之中的民众,不妨说也是一种安慰。张居正却对他不能容忍,授意湖北巡抚陈瑞将其逮捕入狱。陈瑞调走后,王之垣继任,于万历七年九月,杀何心隐于狱中。史书上说是“拷死”或“毙之狱”,也就是活活打死的。
何心隐一死,名声反而越响亮。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李挚写了一篇长文悼念他,称“人莫不畏死,公独不畏死”,“武昌上下,人几万数,无一人识公者,然无不知公之为冤也”。他高度赞美何心隐“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之不可覆盖矣”。还说,大众虽然深信张居正“有大功于社稷,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焚书》)。因为耿定向未能援救何心隐,李挚遂愤然与之断交。
晚明的书院,虽不免有空谈的毛病,但却是清流所在,保留的是文化一脉。张居正想靠高压手段来禁绝,不可能有长期效果。他身死名毁后不久,各地书院便纷纷复燃,最终汇成了明末的清流大潮。
张居正的新政因触及了利益集团,且力度甚大,遭到顽强抵制并不足怪。另一方面,自执政后,与太后、冯保相安无事,小皇帝更是在其卵翼之下,在没有权力制衡之后,人性中恶的一面也十分易于滋长。他素有刚愎自用的特点,此时就更为独断专行。这也引起了一些言官的不满。从万历三年起,弹劾张居正的风波便先后不绝。
第一个跳出来挑战的,是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有白燕,内阁有碧莲早开,张居正以祥瑞呈献给皇帝。冯保则不以为然,对张居正说:“主上幼年,不可用异物让他有玩物丧志之心。”
此事由万历下诏予以通报批评。
张居正拍马拍到了马脚上,自然无话可说。余懋学跟着就奏了一本,说张这样做,有失大臣风范。
小小的给事中也来说三道四。张居正心里恨恨,但忍下了没有发作。
第二年二月,余懋学又上疏议事,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并暗讽张居正是阿谀之臣。张居正看了奏疏,大怒。随后万历下诏,给余扣了一顶“此必是受了富豪贿赂”的帽子,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余懋学这人,其实很清廉,只不过有些不识时务罢了。
这个小小的风浪刚过,到年底,更大的风潮又来了。
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上疏,讽谏万历失德,实际是暗指张居正误国。他提出,王安石曾以“三不足”误宋神宗,皇上可千万不要自误。他还为余懋学喊冤,认为一个言官以忠言上谏,竟然终身不用,“远近臣民不悟,遂谓朝廷讳直言如此,其逐谏官又如此。相与思,相感叹,凡事有关于朝政者,皆畏缩不敢陈矣”。
——你做得好,自然不应该怕人说;你做得不好,难道说说还不行吗?
哪个当头儿的愿意听这话?傅应祯这下可惹火了万历,要动用“廷杖”伺候。张居正则表示反对,说圣旨一下,人心自当畏惧,就无人再敢于妄言了,劝皇上还是“行仁行义”。于是万历亲笔批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镇抚司是属于锦衣卫的机构,专管诏狱,直接奉旨办案,用刑尤其惨酷。傅应祯被打成重伤,到年底发配浙江定海充军。
在这个事件中,大明官员不怕“逆鳞”的倔劲儿又表现了出来。给事中徐贞明心生不忿,半夜光着脚悄悄潜入诏狱,给傅应祯送去药粥(国家监狱看守似乎也不严)。御史李祯、乔岩也毅然前往探监。三人均被锦衣卫告密,后被贬官。
此时是万历三年,张居正的专横还没有达到膨胀的程度,傅应祯因此躲过了廷杖这一劫。
但不怕死的仍然有,这一次,蹦出来的人叫人大吃一惊。此人居然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是傅应祯的老乡——巡按辽东御史刘台。
刘台,字子畏,江西安福人,隆庆五年的进士。张居正不但是他的会试主考、廷试读卷官,还曾举荐他当了现在的这个官。但刘台认为张居正钳制言论、斥责言官、结党营私,都是动摇国本的行为。虽然自己是张一手提拔的人,但也不愿坐视不问。他声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终不可以荐举之私恩,忘君父之大义。”(《安福县志》)
就在傅应祯被发往福建一个月后,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刘台上了一道著名的《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不再拐弯抹角,而是直呼其名,谴责“大学士张居正作威作福,蔑祖宗法”。奏疏言辞激烈,且条分缕析,把张居正执政以来的专横与不检点之处,大加鞭挞。
刘台首先从内阁权限说起,他说,国初设置内阁,官职不高,因此没有总揽之弊。二百年来虽有作威作福者,总还是怕人议论,惴惴然避宰相之名。惟独“大学士张居正专政以来,每每自当必曰: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致使大小臣工,不是惧怕他的威势,就是感怀他的恩德。
接着的驳难几乎势不可当。他说,既然张居正自称“吾守祖宗之法”,那么——
兴王大臣狱,诬陷高拱又是何企图?高拱擅权是有的,谋逆则闻所未闻。先是诬之逐之,逞宰相之威;后又私下里写信安慰,布宰相之恩。“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如今一有诏旨下,如果是严厉的,则张居正曰,我费力多少才不至于更严厉,于是人不敢不先谢他。如此,人们畏张居正甚于畏陛下。如果诏旨是温和的,则张居正曰,我多少费力方如此,人们又不敢不先谢他,于是人们感激张居正甚于感激陛下矣。“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张居正又设立考成之法,使内阁权力在部、科之上。本来内阁是没有大印的,官职属于翰林,不过是聊备顾问而已,不能直接处理政务。张居正创立考成法,是想辖制科道大臣,令他们只听他一己之令。“祖宗之法”有这样的吗?
而后,又将张居正的“劣迹”逐一开列——
逐大学士高拱去国,竟然不容旦夕之缓;
引用阁臣张四维、吏部张瀚,均不通过廷推;
贬斥言官余懋学、傅应祯等,几乎扫空了言路;
为固宠计,献白燕白莲以为祥瑞,招致严旨切责,传笑天下;
为夺好田宅,授意地方府道诬陷辽王,滥加重罪;
为让家族子弟连中乡试,许诺御史某人以堂官、布政使某人以巡抚;
起大宅于江陵,费资十万,规模直逼皇宫,且派遣锦衣卫官员监造;
天下哪个不知,江陵地面膏血已枯,有人还在大起违禁宫室!
我看,张居正贪污的来源,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
否则,何以入阁仅仅几天,即富甲全楚,究竟是用何法致富?华屋宝马,妻妾成群,有如王侯,究竟又是谁人供给?
——刘台的这个奏疏,虽然炮火猛烈,但也不是蛮干,他多少用了一点策略,就是刻意离间万历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
他说:当此之时,给皇帝提意见易,给大臣提意见难。当大臣的,每听到有人批评,则接着皇帝宠信,激怒皇帝,或加罪一人以警告众人,或株连多人以杜绝后来者。如此,大臣之恶日益滋长,天下国家之事大势去矣!
这简直就是一篇讨张檄文,虽有夸大,但也其源有自,并非捏造。尤其是侵占辽王田宅一事,把陈年旧事也牵起来了。
应该说,张居正在大明的官员中,虽不属十分廉洁,但也不是贪渎成性之人。他历来标榜“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曾有一知县向他行贿遭拒绝,以为是嫌少,便又多加了一条玉带再送去。张居正两次奉还,并致信说:我一直以“守己爱民”四字与你共勉,你居然会以为我嫌礼品少,还是认真思之以自励吧。据他自己说,两广将帅先后欲向他送的礼,有万金之多,他都一概拒绝了。
那么,他在江陵的万贯家财又从哪里来?原来是他的父亲、子弟和仆人大开了受贿之门(不收就太脱离群众了)。
据说,隆庆六年,湖广抚按建议为张居正修建牌坊,张居正没有同意。抚按就把募集来的钱送到了张家。因这钱不大好退回,张居正便提议,此钱交给地方官府,作为张家购买辽王府的款项。但后来这钱只做了废王府的装修款,而且大大超支。张居正表示,愿用历年的工资、赏赐和田租来偿还,但最后还是由地方官“统筹解决”了。因此,说张家在江陵修建的大宅来自民脂民膏,亦不为过。
此等隐私,又如何解释得清?
张居正就是铁打的身躯,读了这样犀利的檄文,怕也要冷汗直冒!
自万历二年以来,倒张的力量就在积蓄。一部分言官因张居正弹压言路,产生忿恨,连他的功绩也一概抹煞。他们倒不一定是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受损,但其言行却代表了一批反对改革的朝官。
刘台的弹劾,只是是一次大的爆发。反对派意在逼迫张居正下台或做大幅度退让;而张居正则处在刚把局面打开、欲放手大干之际;两下交锋,双方已无一点回旋余地。
面对如此系统的攻击,无论真伪,张居正也不免尴尬,只有去见皇帝面奏自辩。他没有检讨自己的问题,只是极力推测刘台的动机。他对皇上说:刘台因与傅应祯交情素厚,见傅被充军,怕自己将来也不免,就反攻为守,泄愤于臣。这样既可以免于处分,又可以沽名钓誉。
张居正说着,忍不住泪下如雨,哀叹自被弹劾以来,门可罗雀,谁都不敢来了。“国朝二百年来,并未有门生排陷师长,而今有之。”(《万历邸抄》)
次日,张居正依惯例递交了《被言乞休疏》,要求辞职,并在家等候处理。
据说张居正在递交辞呈时,曾伏地痛哭。万历慌忙将张居正扶起,说:“先生起,朕当逮刘台入狱,关他一辈子以谢先生。”
看过了辞呈,万历当即下旨慰留:“卿赤忠为国,不单是刻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鉴。那邪恶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应以朕为念,速出辅理,不要介意那些浮言。”
二十五日,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他说,现在诸事未安,臣岂敢言去?但臣乃不得已也!臣所处之者,实乃危地也。因为所理之事是皇上之事也;所代者乃皇上之言,现在言官说我作威作福,而我是在代王行政,那么肯定非威即福。如此,事事都可以说是作威,事事也可以说是作福,谗言日日喧哗于耳,虽然皇上圣明,不可能听他们的,不能让臣背负恶名,但作为一个臣子不应让皇上如此费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