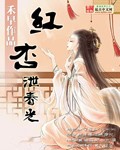智慧的灵光-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鹑宋饰野蛩固垢宜盗诵┦裁矗揖菇膊磺宄!�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顾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生命奥秘的破译者们
作者:沃森
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国遗传学家。生于芝加哥。196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6年到哈佛大学任教,1961年成为教授。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与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共同阐明DNA分子双螺旋形结构,设计出结构模型,回答了遗传物质自行复制问题。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展。二人同莫里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基因分子生物学》等。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像卢瑟福或波尔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地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40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像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像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