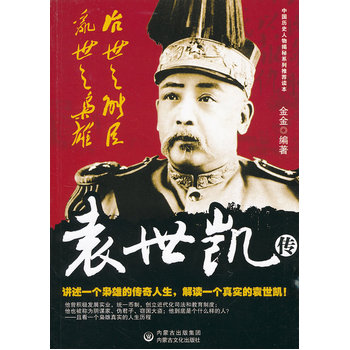当中国统治世界-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艿搅斯惴旱淖鹬兀廖抟晌什换岽τ诹邮频匚弧S肱分尴啾龋泄酝蹲实闹С窒喽愿伲侵泄泊嬖谑恐诙嗟拇笮凸衅笠怠V泄谐〉某墒於缺扰分藁垢撸⒌氖奔湟哺ぞ谩R另桑∕ark Elvin)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①。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缺乏木材、燃料、衣服、家畜、金属、还有肥沃的良田。整个19世纪都存在盲目的森林砍伐行为,在一些地方,木材短缺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柴可烧,只能拿玉米秸秆做燃料。在河南、山东等人口大省,森林覆盖率下降为土地总面积的2%~6%,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这一比率高达~25%。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情况下,人口的持续增长给土地和其他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没有资源丰富的海外殖民地,中国不具备能使其渡过日益严峻的资源受限难关的外生手段。
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利润率的下滑以及市场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们没有足够的动力投资于能够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相反只能鼓励节约资源和固定投资。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技术飞跃到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工厂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正如伊懋可所说的:
“在融合了一种强烈的经济理性意识、一种对发明者的崇拜心理,以及一些引人注目的机械化天才的文明背景中,技术进步一直在推进。”
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英国国内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投资,是一种完全理性的行为,它实现了发明、应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中国依然沉浸在陈旧的生产作业里。在英国,小规模家庭作坊被证明是后来工厂体制的先驱,而在这种农村工业化水平至少与英国持平的中国,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英国的经济逻辑揭示了家庭作业与工厂体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英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中国:广泛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没有带来中国的工业革命。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6)
中国人眼中的“国家”
欧洲和中国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不是它们对各自工业化进程时机的把握,而是两者政治构成的本质存在深刻的不同,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2 000年,而且其影响难以计数。毕竟,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理解中国时欧洲模板显得那么贫乏无力。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哪怕拿破仑和希特勒再野心勃勃,欧洲也没能够对几乎整个大陆行使中央集权控制的帝国政权统治。相反,政治权威转移到了许多小国手中。甚至在统一的进程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欧洲仍然保持着分裂为多国家制度的特征。与此相反,中国从未丧失过帝国的国家制度,这种体系是经历了紧张的诸侯间争斗后显露出来的。实际上,除了外蒙古以外,今天的中国,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其在清朝达到最大地理范围时所获取的国家保持着共同的边界。中国的平衡状态是一个统一的农业帝国,而欧洲则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组成的团体。
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人和欧洲人态度上的根本差别:在中国人视统一高于一切的时候,欧洲人更相信民族国家而非欧洲范围内的主权――尽管成立了欧盟。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古老帝国的分裂和众多新型国家的建立,而中国并未发生类似的事情,甚至连丝毫可能发生的迹象都找不到,这些事实都体现出中国渴望统一的内在动力。中国能够致力于统一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国家和人民把统一作为优先考虑的根本事项;期望国家在确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人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为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它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分裂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幅员辽阔以及远远多于欧洲国家的多样性特征,我们不用对此大惊小怪。由于高度重视国家的统一,所以中国大体上逃脱了几百年来笼罩欧洲历史的内部战争,但是在四分五裂的时期,它往往要付出战争和饥荒的惨痛代价,尤其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中。国家频繁地出现分裂,加上由此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助于增强中国人对统一的向往,统一的传统来自春秋时期的孔子,由于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华大地饱经战乱之时,孔子深深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
中国和一些地位相当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另一个重要区别,即中国从来没有面临过试图限制其权力的贵族精英的竞争。到10世纪中叶,当时的贵族精英全部都被摧毁,其后果是没有一个精英能够享有独立于国家的权威――正好相反,精英深深依赖于国家赏赐给他们的地位。这种情形的关键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到唐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称得上很完善了。虽然贵族在这些考试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科举考试还是为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了大门,成为皇朝招贤纳士的有力手段。对于那些考生来说,儒家经书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有助于强化共同的价值观。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端的时期(例如战争年代)以外,精英仍然相对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在中国,由于精英都是由国家录用的,而且有效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往往按照国家的旨意来行事。在皇帝的庇佑之下,朝廷在盛世时根本不用担心来自宗教团体(9世纪查封佛教徒的财产后)、司法机构、贵族成员、军队或城市中产阶层的挑战。不过其中最大的例外是文人,他们像孔子一样洋洋洒洒地写出惊世骇俗的文章,却与社会日常生活越来越脱节。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7)
故而,与欧洲的情形不同,中国从来都不受强有力的精英的制约,它享有广泛存在和不受挑战的权威。因此,在欧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明确地勾勒且争议不断,中国却不存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边界始终是模糊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没有必要去界定它们,因为中国不存在互相竞争的社会团体。界限,只是一个组织约束和资源限制的实际问题。相比之下,在欧洲,自主、竞争的精英――贵族、牧师和市民,都在为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战斗。欧洲国家和精英之间的竞争,与教堂和阶级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学者、农民、商人和艺人的功能分化,并没有转化为独立的权力基础或制度化的声音。
要治理的疆界太过广阔,中国没有――也不能――单纯依靠或主要依赖武力高压政策来行使其统治。那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实施起来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极其可观的。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武装力量确实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至少到20世纪初叶还是如此。相反,国家权力主要依靠通过高压政治来强化服从观念。在明朝和清朝,封建政权想尽办法向国民灌输在儒家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体系。相比之下,欧洲恰好相反:欧洲人并不把灌输价值观和文化思想当成国家的责任,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职责一直都由教堂来履行。无论是中国的普通民众还是精英人士,都认为这种道德教义本身是可取的,而且也是行使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精英层而言,国家要求学校必须教授儒家经书,同时它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应试科目。另外,它还促使普通民众遵守儒家教义,就连皇帝在处理社会等级和纳税等事务需发布敕令时,也频繁地采用道德的论调。中国还试图宣扬对神灵的尊崇,同时极力压制那些它认为会造成社会*的潜在因素。
除了宗教控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比欧洲先进数百年,后者是到19世纪末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出现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正如历史学家王国斌所说:“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缺乏对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关注,欧洲的统治才会遭遇根本限制,教育和道德教化在欧洲统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政治体制可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和预防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是家族和血统,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对家族和血统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家族或血统关系盘根错节,均以追溯男性祖先为特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只有不到500个姓),它们都是建立在正式成员关系基础之上的。每个家族都享有很大的权力,通常会排斥外姓人,因而也会造成社会的分化。
封建国家非常清楚善政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政思想与儒家传统密切相连,后者着重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例如,皇朝统治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在于一种认知,即税收必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以便农民丰衣足食,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避免抵制和反抗。这里也不缺乏问责制:皇帝的权力拜上天所赐,因此只要统治者治理不善,他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在周王朝统治期间,周王首次阐明他治理国家是遵“天命”,自己是“天子”,民众要忠于天子的统治,宣称统治者必须对引导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力量负责。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8)
中国人的天子概念,不同于西方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明创造和控制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天子胜于一切,但他并非造物主。与西方人“君权神授”学说不同,天建立在“生”的基础之上,上天的子民通过道德获取力量,这一做法使人民不会质疑统治基础,只去思考皇帝的道德统治及其政策是否合理。连年的收成不佳、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一系列自然灾害(例如洪水、地震)发生之后,人们可能会质疑皇帝的统治权力:这种日益增长的合法性危机,可能导致和经受声势浩大的民众暴动,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动,是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的运动,那时,上千万的民众都开始相信:天命已经召回。
中国关于道德作用的假定,只是它如何看待自己的责任这一极其广泛概念的一部分。天命意味着,国家在干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同时,还要调节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职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家管理粮仓储备以确保粮食的供应能相对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保持粮价稳定,这可以追溯到元朝甚至更早。国家还对一些从时间标准来衡量可谓规模庞大的基建项目,例如为防止干旱而治理黄河、建设大运河等承担责任。在上述每一个问题中,中国人眼中的“国家”责任与欧洲的都大相径庭,欧洲人在随后几个世纪中都认为国家责任仅仅是立法。以上情况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是独特的,这也驳斥了其他国家必须遵守以欧洲为中心的发展路径的单一观点。
总之,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很久以前就获得了一个“现代国家”的许多特征,与欧洲的历史进程相比,它应该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此外,从后来的17世纪起,在这些力量的驱使下,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展逐渐向外向型转变――战争的危急、国家对财富的追求、政治代表的呼吁,这些都与中华帝国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