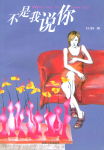别跟我说你懂日本-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接过的骚扰电话多数是默不做声的,但也有例外,曾在午夜两点多接到一通,那端传来一位女人低沉的抽泣。挂断之后,我睡意全无,走到窗前,想到这世上此刻有多少伤心人夜不能寐,对那位来电者已没有怨言。若真的能减轻一点她的苦恼,被骚扰一下倒也无妨。不过,某男性友人在夜深亦曾被骚扰过,对方女子发出挑逗的呻吟声,被他身边团聚不久的发妻听到,掀起了一场无中生有的轩然大波。
据媒体报道的案例,某夫妇在两年内接到了50000余次骚扰电话,两人心理生理上都遭受严重伤害,骚扰者使用的是无须登录个人情报的卡式手机,导致警方调查进展缓慢。被逮捕后,与受害者相识的骚扰者说她的动机无他,只是觉得对方冷淡了自己。这种骚扰是怨恨使然,但我们通常受到的应该源于孤独。想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站在街头的公用电话亭里,投下硬币,拨通不相识的号码,既花钱,又挨冻。为的是什么?孤独啊,孤独。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漂泊客,多少会理解这种心情。对方只要接了电话,旋即挂断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都是一种安慰。
第48节:我骚扰故我在(2)
各类骚扰现象非日本所独有,但骚扰电话已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报刊和网络上传授各种“击退法”,我估计效果不彰。相识的国人里几乎人人都有过被骚扰经历,严重的如一位女留学生,对方听出她是外国女性后,一天拨打数十次,最后逼迫她花钱更换号码了事。实际上,“いたずら电话”仅是骚扰之一种,尾随(スト‘)、偷窥、窃取内衣等都算在内。
尾随就是被跟踪,据统计90%是男跟女,10%是女跟男,一半以上是出自“喜爱之情”。警方的案例数据是2008年发生14567件,比2009年增加一成。但这仅是警方立案的部分,应当是冰山一角,我认识的人当中被尾随过的不下十人,却只有一位报了案。
陶渊明《闲情赋》中为了思慕的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这种情感我们能够理解。尾随者若就是想瞄着“美人”(不论性别)的背影,踩着“美人”的脚步,那倒和陶渊明的理想差不多。然而,有的尾随事件最后发展成住所被探知,以及偷窥、盗窃等暴力犯罪。因此,尽管很多尾随者似乎满足于默默地亦步亦趋,可是对被跟踪的人来讲,当然是很不愉快乃至惊恐的体验。
尾随者的心理状态被称做“执拗”,但它和“いたずら电话”一样,验证着人的孤独和对自我存在的不确定感。在电话或跟踪给对方造成的不快里,和陌生人发生了联系,因此获得了“我骚扰故我在”的自我认知。
香港的日本电影专家舒明提到一个现代日语中几乎成为“死语”的词:垣間見。它指的是平安时代的贵族男子躲在贵族女子的住处附近,偷窥她的容貌。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有宋玉被邻女窥墙的典故,所谓“垣間見”也就是扒着墙头或墙缝偷看。舒明认为,日本文化中对这类基于“好色”(爱美)之心的偷窥,非但不加批判,反而赞其风雅。这应当是今之尾随、偷窥者们的有力辩辞吧?但是,跟着走几步路看看也就罢了,偷内衣、拍照片、打电话等可就大大不妥。
骚扰可能违法,可还有合法骚扰者。两位相貌不错的女性朋友曾遭受过日本警察的“合法骚扰”:一位忘记带外国人登录证,虽有学生证为凭,而且离住处不远可以回家去取,就是不容她分辩;一位明明带着护照,偏被怀疑伪造。她们都被几名警察大张旗鼓地带回警署,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等她们错过了本有的约定或被气哭,再宣布无事释放。这种变相的“いたずら”固然等而下之,可还真的拿它没办法。
第49节:道即是空
道即是空
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中空”这个特征,比如俳句的写作、茶道、华(花)道等。
初学日语不久,知道了“季语”这个词。所谓季语,就是表示季节景物气候的词语。据说在俳句的写作中,一般是必定要有一个季语的。可俳句本来只有十七音而已,去掉季语,还能剩什么呢?后来买了一本信笺,发现扉页上全是写信时常用的固定季语,如“值此春寒料峭的时节”、“在这初雁带来秋日气息的日子”……诸如此类的文字,让人想起中国隋唐时代的《书仪》。《书仪》专门罗列按照节气时令的问候套话,并组成固定的首尾格式,辞藻华丽雅致但空洞僵化。《书仪》的流行,是因为有人要模仿贵族的高雅和教养,而葛兆光指出,这种拼盘“使得过去人间交往的真情实感与舒卷自如的文人书札,变成了标准尺寸的零件装配”。日本人可以说把《书仪》的模式与精神学到了精髓,并将其空洞僵化加以发扬光大。
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对自然四季的变换感觉敏锐是其优点,但季语作为符号,实际上没有意义。它们是空的。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内容都有这个特征:中空。比起季语更闻名也更突显的,莫过于那几样“道”,如茶道、华(花)道。
茶道的说法,唐人称“茶圣”陆羽著《茶经》,“于是茶道大行”。此一茶道,意思是饮茶的习俗和品位。如果茶真的有道,那么道应该在茗品、茶器、泉水和汤侯,而不在于居所、礼仪、姿态和服饰。归根结底,茶是要喝的,人是饮茶品茶的主体。日本的所谓茶道,用外在的烦琐甚至古怪的形式,冠以生硬比附的玄谈奥义,弄得买椟还珠,失去了品茶的真谛。
曾经看过一次茶道表演,表演者属于著名的里千家流派。坦率地说,不论是茶道、花道,我无法区分这些流派的区别(日本插花艺术协会有500多个流派加盟),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煞有介事。那次观看表演是一次不大舒适的经历,只能出于礼貌表示赞赏并忍耐到结束。不敬地说,有时还会因表演者夸张的动作感到滑稽。
茶自中国传播海外,不论日本还是欧美,最初都是上流阶层的奢侈品(与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不同)。日本室町时代,茶只在贵族与武士中流行,被称为“书院茶”。受到禅宗影响,本来是僧侣的村田珠光将饮茶与宗教文化融合,提出“和、静、清、寂”的原则(华道的基本理念更宏大:天、地、人),茶道或以此为肇始,到千利休而发展完备。不过,我认为考虑到日本历史上宗教势力与世俗武士政权的纠葛关系,茶道的过度阐释毋宁说是僧侣以风雅和修行为名,试图在精神层面控制武士的一种手段。因此,茶道从场所到仪式设计了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而茶室的入口(日语称“芸凇保└歉鲋蝗菀蝗斯蚺澜サ男《矗锩婵占湟嗥南列 U飧鋈肟谟胄∥菥菟翟醋浴段︒稻罚︒稻邮吭诙肥抑杏胛氖馄腥八耐虬饲У茏酉嗷幔⒁馕虻勒叩男木持尴薰愦蟆?墒牵璧酪造谖渲匾睦砺叟矢剑切┬问缴系木心嗳闯闪恕罢稀保疚薹ǖ执锼拇档木辰纭!昂汀⒕病⑶濉⒓拧惫倘桓呙睿训览肟问降氖烤筒荒懿挝蛄寺穑�
在今日的大阪城内,可以看到丰臣秀吉当年的“黄金茶室”之仿制品,整个房间全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它表明茶道之所以受到推崇,得自武人对风雅的追慕。茶道的玄谈确实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茶道的集大成宗师千利休也死于丰臣之手。
战后的日本对外宣传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营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风雅形象,所以,茶道华道的海外普及工作开展得很有声色,佐以日本的经济成就,更增加了蛊惑力。假如说对东方文化所知有限、容易被表象迷惑的西方人会轻信还情有可原的话,中国人人云亦云就有点不应该。插花固然能陶冶人的审美情趣,品茗文化也是生活艺术,但言过其实则大可不必。认识的在日华人中,有些女性热衷学习华道、茶道,归根结底是出于知识上的短板和对“先进文化”的自卑感。
听说中国近年来兴起所谓“茶艺(道)表演”,更有说法称茶道从中国传到日本,现在又回到中国云云,不禁哑然失笑。茶道是空洞的,“茶艺(道)表演”或许连空洞也谈不上。
饮茶就饮茶,插花就插花,至于“道”,还是免了吧。
第50节:拉面王之死(1)
拉面王之死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
意大利男足有一年来日本比赛,托蒂在下榻的酒店吃了一碗日本拉面,花了1000多日元,大呼太贵。以他的收入水准来看,这抱怨颇令人不齿。不过,日本饮食中,拉面确实算性价比比较差的:一碗面很难吃得饱(对成年男子而言),成本又极其低廉(售价却通常七八百日元上下)。但是在日本的吹嘘和包装之下,拉面的名声响亮得很。一些中国来客吃过之后,也大赞日本拉面如何了得,甚至有乐不思蜀之感,可那喜悦我想大概一半是出于新鲜,一半是对“日本”的膜拜。
《朝日新闻》的调查,得出“国民食品”的双璧是咖喱饭与拉面,寿司、荞麦面、乌东面紧随其后。拉面的受欢迎程度虽然略逊咖喱,但食用频率更高,22%的受访者称每周要吃两至三回以上。以汤的口味论,拉面的排行是酱油、大酱(味噌)、猪骨和盐。
偶尔也会去吃碗拉面,谈不上有特殊爱好,仅仅为了换个口味或贪图简便。但在生活中,拉面的身影可谓无所不在:电视里播放着各地“名物”拉面,拉面大赛;书店里排列着拉面词典、拉面全书;超市内各式各样的拉面商品琳琅满目;网络上有人气旺盛的拉面爱好者组织、研究会、讲习所(就差没组党了);每一处商店街都少不了拉面店,每一家都自诩风味独特、用心良苦(常见的写着“魂入り”)……当然,人愿意吃什么是他的自由,我感兴趣的日本拉面文化体现出的一个特征:过度阐释。
第51节:拉面王之死(2)
吃食物,是人作为生物的本能,但在人类社会中,吃什么,怎么吃,从来就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罗兰?巴特来日本兜了一圈,写下著名的《符号帝国》,26条随笔里多则和吃有关。近年来,由于日本人平均寿命长,日本饮食跟着沾光,似乎成了延年益寿的重要原因,颇受好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夸张,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食品卫生、文化传统、保健医疗、社会体制等相比,人的寿命和饮食习惯的关系究竟有多大?
2008年,日本拉面界的旗帜性人物武内伸因肝硬化逝世,享年48岁。他曾获第二届“拉面王”大赛冠军,担任日本拉面协会副会长和横滨拉面博物馆的宣传负责人,经常在媒体上品评拉面,号称权威拉面专家。在他生前出版的《百吃不厌的百家拉面店》一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他“吃过4000碗拉面”的业绩。媒体报道大多没有明说他的病因与拉面的关联,声势浩大拉面业界可不好对付,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一日三餐皆拉面”的过量油脂摄取,是他肝脏机能崩溃的罪魁祸首。病故前两年,武内伸去看医生,医生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