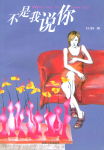别跟我说你懂日本-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降姆饨熘骱推锸浚胫泄钜烀飨浴�
这个差异是理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一个节点。或许可以说,当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日本的中学世界教科书中提到中国的宋代,称之为“文治主义”。这或许是士的概念在中国经过漫长演变,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清末学者汪士铎批判宋儒及理学,有一段观点颇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礼,而略其经世之说。又以军旅未学而讳言兵,由是儒遂为无用之学。”他提到能辅助孔子之道的,分别是申不害、韩非、孙武、吴起,后两者都是军人。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单纯依靠中国式的文士,没有法家兵家的辅弼,不足以令国家富强。
中国的士变成文士,与武士的脱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宋代以后,文士因掌握行政权力,压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将之间长期的难以调和的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严重内耗。而反观日本则似乎不存在这种情况,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战时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人员。武士被要求学习文化,欣赏艺术,哪怕是附庸风雅。“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出身倒数第二级的下层武士,年轻时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代人抄写的零工。或可以说,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个“军人政权”了。
文士与武士,眼界和看法自然不同。清末,日本学者冈千仞来华游历了数月,说了解了中国的病根在于“经毒”和“烟毒”。所谓“经毒”,自然是指中国文士对经书的沉湎。在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眼界最为开阔者之一王韬的交谈中,他说:“世谓战危事,兵凶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与天下者而论之,安知危事凶器非即祥云庆星也?”这段话鼓吹暴力手段的积极意义,已经显露出日本未来国策的端倪。
王韬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之为“日本儒士一孔之见”,因为“苟必以战斗为练兵之具,是残民以逞而已,非治国家之道也”。王韬的说法也没有错,日本后来确实因暴力倾向失控而滑向了残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韬那一刻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中国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41节:与地震同行(1)
与地震同行
日本人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最近在阅读英国学者托尼?麦克米切尔的著作《人类浩劫:失衡生态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物性、文化、健康与疾病模式的影响,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环境之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一个实例,不妨说说地震。
2009年夏天的地震比较频繁,传说中的东海或关东大地震又成了舆论热衷议论的话题。根据手边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势,未来30年内,东海地区里氏8。0级地震的发生概率为86%,关东地区里氏6。7~7。2级地震的发生概率是70%,茨城县海域里氏6。8级地震的概率更是达到90%。近一段小震多发,类似数字便纷纷见诸媒体封面和头条,颇为吸引眼球。似乎谁说得越危言耸听,谁就卖得越好,有点像恐怖电影。
我已记不得来日本之后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确切日期,却记得因晃动并不算剧烈,没感到特别的惊恐,反而带一丝新奇生出的快慰。后来的十几年里,经历过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严重的是2005年新泻地震。当时我在东京电影节设置于六本木高层建筑49楼的新闻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风浪般的摇晃。在那一刻,很多欧美人士惊恐失色,有的甚至画起了十字祈祷,可日方人员大体上保持了淡定(暗示着一种因勇气而生的优越感)。当天一共震了三次,时任首相小泉在开幕式上草草致辞就离开前往灾区。第三次时,发现手机信号因通话量过大而阻滞,我也有些慌了,问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情况如何。他笑了笑:“没事。请放心吧。”让我不禁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惭愧起来。
第42节:与地震同行(2)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已经有地震的记载,并且描述了给当时人们生活造成的威胁。一个族群在岛国这种相对封闭的土地空间内,不断经受地震的考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该族群的身心发展。托尼?麦克米切尔说人类自身为了因应周遭环境,会持续地发生着变异,他称之为“天择”。今天的日本人祖先主要是从东亚大陆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移民,他们在日本列岛上的生活历程和人类进化史相比虽然短暂太多,但可以相信,“天择”必定也是在悄然进行的。
在主要的破坏性自然灾害中,地震或许是来得最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一种。地震对人类生物性的潜在触动可能极其漫长,在心理层面却见效很快。以我个人的心态变化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两年是恐惧,曾经有午夜遇震半裸着身子跑下二楼的“可耻”举动。但当几年之内的地震都没伤到一丁点儿皮毛之后,会进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继续大睡,您爱怎么震就怎么震。这段懈怠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了。我还不知道如何为之命名,它的感觉是恐惧掺杂着茫然,成为头脑中的一个预警装置。它带来的变化,就是开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样,筹划买点应急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筑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种因为较长时间接受突发危险冲击的紧张,渐渐演变成了本能性的戒惧反应。
日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几乎渗透到血液中的防灾意识。1月17日是防灾暨义工日,7月1日是国民安全日,9月1日是防灾日。日本关于防灾的各种演习、训练、宣传可谓繁多,客居的外国人有时也要被组织起来学习防灾知识。寓所楼下几十米是一座小公园,公园内有一栋铁皮屋,名为防灾仓库,里面储藏有工具、生活用品等,以备不时之需。这种铁皮屋是很多公园内的固定风景,而且有专人定期检查。许多国家假如能把防灾工作做到接近日本的程度,相信会减少极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数日前,一辆大阪开往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长途客车在高速公路上骤然起火,满载的乘客以“镇静有序”的方式全部脱险,无一人伤亡。临变不惊的素养,得自从小就接受的防灾教育,也受益于生性俱来的警觉。
如果和中国对照的话,我不禁想到历史学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中的一段论述:中国历史上太多的面临异族军事侵略导致的失败,使中国士大夫们在最初的失利之际缺少应有的警觉。佐藤慎一说得很对。在西方列强挟坚船利炮之威闯入东亚世界时,中国人认识到此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足足花了几十年,在被人家零打碎敲中频频割地赔款以换得片刻苟安。失败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觉?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来攻击就是元军那未竟的远征,又为何始终保持了对外患的高度警觉?
关于地震为代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给日本文化带来的特质,已有不少人论述过,比如生死观、美学观,等等。我以为,对外界事物和身处环境的恒常警觉,该算是地震的一个副产品吧。
第43节: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三刀的日本人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台大历史系高明士教授在《东亚的政治与教育》中说,日本对隋唐帝国的称呼有两面性,在国内用“邻国”(藩国之意)指称,与隋唐打交道时则称“大国”,俨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称之为“两面性礼仪”。
两面性,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
说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死忠,这的确是武士形象极有代表性的一面。来日本这些年,电视经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里面的四十七位武士为了“尽忠”已死的主公,拿别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极为简单,却不断被翻拍,版本多达数十个,比咱们的第五代导演狂恋秦始皇还厉害。然而,前面也说到本尼迪克特举的例子,日军俘虏转身就能变成配合盟军的模范,甚至反戈一击,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战后期,美国不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应军方要求,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本尼迪克特那本名著《菊与刀》就是此一计划的产物。菊与刀的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一种两面性。本尼迪克特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人的伦理会依照境遇变化而随之改变。一个日本人可能温和礼貌,也可能粗野残暴,这要看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可以迅速完成从一面到另一面的转变。
人发明的棋类游戏能够折射文化内涵,日本将棋(象棋)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对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盘之上(名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将棋和中国象棋、西洋象棋的阵式没太大分别,但这一招“敌为我用”却非常独特。中国与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战场,可日本将棋的“持子”竟然能归来与旧主厮杀。它很精辟地从侧面说明,日本文化在对“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实际上还有着另一面的价值规范。
在日本生活略久,两面性的人事种种,可以说司空见惯。应该说,不仅是日本人,任何人类的身上都带有程度不等的两面性,即所谓双重人格;而人类的各个文明里,也都存在表面现象和真实本质之间有所差距的状况。只是,没有哪个社会像日本这样,抽离了对两面性的道德判断,并且为这个两面性设置了极大的阐释与转圜空间,似乎是故意地在维护它的两面性。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开卖淫,一面又允许“ソ抓楗螗伞贝蚬愀胬靠停灰幻媸歉畹俟痰哪行酝ǎ幻媸羌纳阊拐ツ腥说牧砝嗯ǎ灰幻媸欠缁ㄑ┰隆⒋ゾ吧榈南星橐葜拢幻媸茄獗畔帧⒉腥毯蒙钡穆缬埃灰幻娼簿俊袄褚钦筏ぁ焙蜕缁峁拢幻嬗衷诮滞匪娴匦”恪⒃诔迪崂锿研澜拧�
两面性的日本,对于外来的观客而言,具有较大的迷惑性。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外来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现于表层的一面,另一面则需要假以时日才能发觉或遭遇。这当然怪不得观光者,就好像游记这个体裁之所以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单纯地描绘风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当地的状态绝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听过有些外国人抱怨日本人“虚伪、阴险、两面三刀”,可不少情况下,日本人并没有刻意地去隐瞒、欺骗、诡诈,只是不加说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对两面性的习惯,他们或许压根儿没觉得有说明的必要,是外来者自己想当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出身的国家、文化满腹牢骚的,极容易把个人感情投射到他们所接触的某一面当中去,误判也就应运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话,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会对其两面性感到些许困惑:摸不透。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