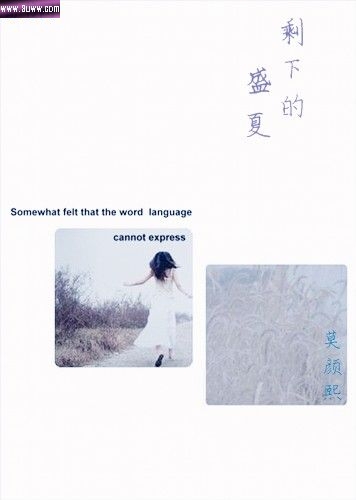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她点头。我问她“干爹”知道吗,她说暂时不想告诉他,好像要挟他似的。我没想到曲薇还是性情中人,这个时候还为别人着想,不禁对她有了几分尊重。我问她喜欢“干爹”吗,她沉吟不语。少顷,她说不知道是否喜欢,只觉得他人不错,对她特别关照,供她上学读书舍得花钱。我说这种事别人决定不了更替代不了,她自己看着办吧。说完,我起身告辞。曲薇却要我坐一会,并且从床上起来沏杯咖啡递给我。我不喜欢喝咖啡,象征性的品尝一口。也许心情使然,那味道像橄榄。曲薇又回到床上,目光逗留在天花板上。她寻思少许,一脸凝重的问我,是不是看不起她。“我?”我尴尬地笑了。想到刚才还在卖黄色光盘,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呢。我说北京这个地方充满诱惑,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我好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更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曲薇淡淡一笑,说她明白我的意思。她还说到北京这么久没有一个好朋友,她觉得我是非常可靠的朋友。既而她漠然一笑,说她错了,在我眼里她与小姐没什么区别。说完,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随即眼泪一点一点地流下来。她说每次看到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做比较,我可以养活自己,她为什么不能?她什么都不差,凭什么做别人的玩偶。
我表示理解,说这种事情现在很普遍,你情我愿各取所需,没什么不好。曲薇瞥了我一眼,将烟蒂狠狠掐灭在烟灰缸里。她板起面孔说我笑话人不带脏字。我嘿嘿一笑,换上一副善意的表情,说现实如此,不能睁眼说瞎话吧。曲薇没有吭声,似乎认同了我的坦率直言。我们之间话不投机,只好岔开话题闲谈了几句。我觉得没有呆下去的必要,客套一番起身告辞。临走时我问曲薇愿不愿意听我一句真话,她深邃地望着我,认真地说请我来就是想听真话。我很坦诚地告诉她,一个人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与生活捆在别人的裤带上,依赖别人不是长久之计。我挪着凳子出去的时候,曲薇一直送到大门口。我没想到平时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姑娘,令人羡慕的背后竟然有那么多无奈与苦涩。也许,我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又过了几天曲薇再次呼我过去,她说我经常在外面转悠,可不可以找个私人诊所或者大夫。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建议她去正规医院瞧瞧。她叹息一声,显得有点无奈,她说想将孩子拿掉。我一怔,要她再仔细考虑一下,她坚定地说早已想好了。其实蓝靛厂有私人诊所曲薇不会不知道,她大概不想让认识的人知道才请我在别处找。我在四季青找到一家小诊所,将详细地址告诉了她。曲薇晚上打车去诊所做了人流。细细一想她也挺可怜的,才二十岁的姑娘遇到这种事。不过她很坚强,意识到错了没有继续下去。
周末我与陈挺去天意市场进货回来,二姐大老远招手示意要我过去。陈挺抱着一摞子画卷跳下车。我开车来到杂货店。二姐夫见了我,坐在椅子上用拐棍指着我,说我不够意思,有女朋友了不告诉他一声。我嘿嘿笑了,说哪能呢,别拿我穷开心了。他笑着对二姐说,我的嘴严实,油着呢。二姐笑了,说小段哪像你,芝麻点儿的事儿,弄得像过年似的。
我看没什么事,客套几句想离开,二姐笑呵呵说:“慢走啊,小段,何琪的事儿,明儿个有时间再说吧!”“何琪!”我心里不禁一颤。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5(2)
夫妇俩笑了,问我为什么不走啊,二姐夫笑我迈不开步了。我这才缓过神来,问何琪怎么啦。二姐笑着说,小段真够可以的,姑娘追到北京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问二姐怎么回事。二姐从柜台里取出一张纸条说,何琪明天下午两点到北京,要我去西站接她。“我的天呐!”我大吃一惊。
夫妇俩大笑起来,说我乐昏了头,连天都喊了出来。我苦着脸说,还乐呢,哭都没有眼泪了。二姐夫埋怨我不地道,有好事不告诉他们。他再三叮嘱我带何琪过去让他们瞧瞧。我没心思听二姐夫唠叨,脑子里转来转去地想着怎么办。我离开时二姐提醒道,接站时别忘了买束鲜花。我回到住地,陈挺正在给画分类。我要他停下来,快去租间房子。他看我着急慌忙的,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心乱如麻,来不及细说,只是强调他快点儿,务必当天租下来,明天就用。陈挺问我到底怎么了,我敷衍道,租到房子再说吧。陈挺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放下手里的活儿。他刚走到门口我又说租房子的地方最好离我远一点,他诧异地问多远,我说蓝靛厂最好。说完,我将车钥匙扔给了过去,要他骑我的摩托车去。我将画卷分好类,躺在床上寻思起来:何琪怎么突然就来了?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呢?一连串的问号好像烤肉用的铁钩子,一点一点地勾心。我一再告诫自己冷静下来,不要乱了方寸。我们晚上吃饭时我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陈挺,他非常高兴,告诫我不要再错过了,重蹈孟香的覆辙。“嗳!”我无奈地一声长叹,说何琪来得不是时候。陈挺驳斥了我,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无话可说,缄默不语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分手后,我去了曲薇家里。曲薇经历了人流事件之后好似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主要心思也用在了学习上。听说她“干爹”因此给了她一笔补偿费。曲薇住的是独门独院,那时已经将其他的两间屋子租给了别人,俨然成了一位房东。她一边沏茶一边说我准有事。我说没事就不能来么。她笑了,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说明来意后她不禁睁大了双眼,连连诧异地说,行啊,小段,真没看出来呀。她比我小,却一直叫我小段。我懒得同她计较。曲薇忽然眉头一皱,若有所思地说,这种事我应该亲自去。我嘿嘿一笑,说我不能开车进站里,这才来麻烦她。曲薇聪明得很,直率地说这不是理由。我笑着说,哪来那么多的理由。她想了想,爽快地说,小妹愿意效劳。我临走的时候要她回来时打车到长春桥,我在桥上等她们。曲薇不解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不进村里非去长春桥,是不是想制造一点浪漫。我说何琪的住地在蓝靛厂。曲薇以为听错了,确定没听错时不由得摇摇头,我听到她在背后说我脑子短路。
我收到曲薇呼我的信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开车到长春桥上等着何琪的到来。我想了很多见面时的开场白,觉得俗的太俗,雅的太雅,都不怎么样。干脆心一横,一切顺其自然吧,爱咋咋地。
等人时感觉时间好像停滞了,一分钟比一小时还长。我眼看着一辆辆出租车从桥上疾驰而过,却不见何琪与曲薇的影子,不免有些焦灼不安。终于一辆夏利车来到桥上,何琪与曲薇正在车里看着我。她们刚要开门下车我制止了,吩咐司机继续开车跟着我走。我在前面引路,来到何琪的住地。陈挺早已收拾好屋子等在那里。我们进屋后,我开始给他们一一作介绍。何琪很拘谨,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西瓜瓤。
相互客套寒暄一阵后,陈挺、曲薇借故先走了。我与何琪在一起居然不知说什么。她见我不说话,矜持地看着我也说不出话来。“一路上还好吧?”我总算找到一句话,打破沉默。她点点头,笑着说,蛮好的。停顿片刻,我又想起了一句,问她家里还好吧。她依旧点点头说,蛮好的。
我语无伦次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说完,干笑了起来。一定比哭还难看。我说她来得够突然的,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话一出口,我觉得欠妥,马上补充了一句,她吓了我一跳。何琪两眼不时地打量我,犹豫了一下,才怯怯地说,她想给我一个惊喜。我做作地笑了。她脸红红地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是吗?”我一愣,到北京后早已忘记什么叫生日了。何琪高兴地从包里取出一件包装精美的衣服递到我面前,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又惊又喜,又苦恼又无奈。心里酸酸地,涩涩地。那是一件李宁牌的红色T恤衫。她将衣服在我身上比试了一下,要我穿上试试合身么。我只好脱下上衣穿上T恤衫。她马上从包里取出化妆盒,打开后要我照一下镜子。我对着镜子一看,衣服不但合身,还显得精神。我知道此刻只能穿着它,一旦脱下来何琪会不开心的。我要她好好睡一觉,然后带她出去吃东西。她说一点儿都不累。我笑着说刚到北京的人都这样,兴奋过头了感觉不到疲劳。她笑着说,真的没觉着累。“好!”我爽朗地说,马上带她出去转转。她高兴地跳了起来。北京的夜色真美,新的街,新的巷,新的酒吧,新的夜总会,新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金碧辉煌。沿着新的柏油马路徐徐而上,顿时来到盘根错节,四通八达的立交桥上,极目远眺,霓虹彩灯像两条串在一起的夜明珠一路延伸而去,望不到边际,仿佛缀满繁星的天堂,拖着灯光的车辆呼啸而过,好似夜空的流星一掠而过,一切恍如梦境,分不清哪里是天堂,哪里是人间。何琪初来北京与我当初一样,感觉一切都那么美丽,那么陌生,那么好奇。她不时地发出兴奋的惊叫,又不时地目瞪口呆,曾多次要我临时停车,站在她认为很美丽的地方欢呼雀跃,流连忘返。看着她喜悦、快乐的样子,我想起初到北京时的情景。虽然我没有她这样近距离的浏览北京夜景,不过心情依如这般欢快。这就是北京!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呈现出她的美丽,她的辉煌,她的繁华,甚至她无以伦比的尊贵。可是她好像蒙着面纱的圣洁少女,没有人可以真正看清她,读懂她,更不用说拥抱她了。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5(3)
我不知一直走了多远,只觉得控制油门的手指已经有点麻木了。我好几次想掉头回去,但看到何琪的高兴劲又犹豫起来。毕竟她第一次来北京,我不想给她留下太多的遗憾。天安门任何时候都是熙熙攘攘、纷至沓来的人群。何琪像个孩子似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她一会儿看看这儿,一会儿摸摸那儿,似乎不闹腾闹腾,少了许多到此一游的惬意。何琪好似服了兴奋剂,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居然还有如此旺盛的精力。我实在感到有些累,只好提醒她该回去了。何琪的兴致顿时一落千丈。她眼巴巴地望着我,恋恋不舍地说她想看升国旗。我笑着对她说,改天一定带她来实现这个愿望。我们返回途中我加大油门一路狂奔。我们交谈时何琪说,她是办了停薪留职,瞒着父母来北京的。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紧急煞车停在路边。也许没有心理准备,只听何琪惊叫一声,差点从车上甩出去。“你家里人不知道你出来?”“我给他们留信啦。”“天呐!”我禁不住感叹道。何琪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欲言又止,随即又慢慢低下头。我点燃一支香烟吸了几口,思忖少许,要她尽快给家里人报平安,免得他们着急。
我们回到蓝靛厂敲了很长时间的院门,房东才嘟嘟嚷嚷地开门,开门后一脸不悦地说以后别回来得太晚了。
我连连说好话,赔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