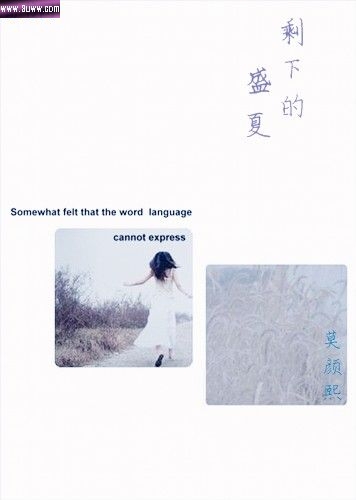当身体还剩下四分之一时-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他们笑了,潘军拍着胸膛说,一定给歌词谱曲。潘军将谱曲好的歌词,一边弹吉他一边唱给我听,我一脸沮丧地对他说“暴殄天物”。谭琴格格笑,对潘军说怎么样呀,我就说了,你的曲子和歌词不匹配吧,人家小段写的是飘飘欲仙的感觉,你那曲子写的什么呀。听说潘军在酒吧里还演唱了那两首歌,可是效果糟糕透顶。从那以后他没有向我要过歌词,我再也没有写歌词的念头。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人大西门卖画,尽管收入不怎么样,不过勉强可以维持生计。陈挺偶尔接到一批信封回来,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按时完成任务。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既平淡又无聊,那时我常常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生活。那天我刚在路面上摊开画卷,有人大声喊,城管来了。顿时一阵骚动,人们疯了似地慌乱收拾东西到处乱窜。我也急忙卷起画卷,可是慌乱之中画卷乱成一团,这时有人过来快速地将画卷收拾整齐递给我。我一看是曲薇,太意外了。她笑着问我,人家不会抄我的东西吧。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她笑了,将画卷放到我后车座上,我说了声谢谢,开车迅速离开。那时候所有在人大西门卖东西的小贩都一样,城管来了四散逃去,城管走了又蜂拥而来。很多人称这种方法叫打游击。曲薇经常带同学来买我的画,时间久了偶尔闲聊几句。她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笑着问她为什么来北京。她笑了,说北京好。我也笑了,说北京好玩。有一天我正在卖画,老五呼我。我打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二姐夫犯病了。我立刻赶了回去。老五说他与二姐晚上去医院,要我在杂货店里守夜。第二天老五回来说二姐夫没事,观察几天就回来。我听了以后很高兴。
谭琴说有人过生日,要我用车送她去蓝靛厂。我开玩笑说“给钱”,她说没问题。原来是曲薇的生日。潘军与一些人早已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我进去,我心想人家过生日又没请我便推辞了。我刚启动引擎,却见曲薇出来了。她笑吟吟地说,赏个脸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没有生日礼物也可以吗。曲薇笑了笑,说指望你的生日礼物,太不人道了吧。我嘿嘿一笑,加足油门疾驰而去。潘军跑出来冲我大声喊,我心里极不痛快,他喊了什么没听清。谭琴回来后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笑着说与人家不在一个档次,何必凑热闹呢。我没想到过了几天,曲薇在卖画的地方遇到我,解释说那天她不是有意的。我嘿嘿一笑,说有意无意没关系,那么多陌生人我不太习惯。曲薇似乎自我解嘲般地笑道,都是江湖儿女,干吗那么计较呢!我重复一句,只是不习惯而已。我强调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希望别人无视我的生活习惯。曲薇困窘的笑了,说她以后一定注意。谭琴与一位鼓手关系密切,偶尔同住一起却没有恋人卿卿我我的那种温馨。我很奇怪,背地里问潘军,他怪异地笑,然后告诉我谭琴有丈夫,过几天就要来了。我“啊”了一声,情不自禁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潘军拍了拍我的肩膀,笑我太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气问我,生理需要懂不懂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却又不太懂。这种事很普遍,没有我想得那么复杂。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4(2)
过了几天谭琴的丈夫果然来了,两口子卿卿我我,恩爱异常,丝毫没有不和谐的迹象。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有天晚上我卖完东西回家路过小南庄时看到曲薇步行回家,我不经意地问她为什么不打车,她说省钱呗。“省钱?”我不禁笑了。印象中曲薇一直花钱如流水,出门车来车去的,根本不是省钱的主儿。她问我最近怎么没去酒吧,我说那是有钱人去的地方,我暂时没资格。她笑了,矜持地问我,如果有钱呢。我告诉她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说完加大油门疾驰而去。我走出几十米,又停了下来。等曲薇过来后,我笑着说她要是愿意,可以顺路捎带她一程。她犹豫了一下,笑着说多谢了,然后轻提裙子坐到车上。我将她一直送到住地门口,她客套了几句,请我到屋里坐坐,我谢过后掉头回家了。用当地人话说,这天一年比一年热了。夏天到了,万泉河里成了天然的浴场。谭琴的丈夫很怕热,四处找人陪他去河里游泳,我毛遂自荐陪他去,众人以为我开玩笑,有人戏谑说,我敢去河里游泳,他敢用手掌煎鸡蛋了。我欲擒故纵,刺激了他几句,他果然中招与我击掌打赌,我游过万泉河,他请众人去小南庄一家四川火锅涮锅仔。我们来到河边,潘军背着我走下码头时很多游泳的人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我视若无睹,用凉水在身上各处拍了拍,并开玩笑说现在毁约还来得及。众人哈哈大笑,说我动真格的害怕了。我“叱”地一声笑,说这顿火锅有得吃了。说完,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潜水游向对岸。我不知游了多远,感到快窒息时立即浮出水面。我看到离岸边只几米远,不免有些遗憾。心想:早知如此再加把劲直接到岸了。我游上岸,坐到码头上,向对岸观望,谭琴手舞足蹈,在对面大声喝彩。我稍歇片刻,跳入水中游回对岸。我发现很多游泳的人像见了怪物似地看着我,有人甚至游回岸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我看到人们多是欣赏、羡慕的目光,不禁暗自得意,愈发在水里撒欢了。我变换着不同的泳姿,轻车熟路地游回岸上。与我打赌的人输得心服口服,外加佩服。我免不了吹嘘地说,家乡的河比这条河宽多了。正在这时一位女子全副武装从对岸游了过来,上岸便说:“小段真牛啊!”说完,摘下了潜水镜。用光彩照人形容曲薇,任何时候都不为过。当她湿漉漉地站在码头上,立即吸引了众多异性的目光。原来曲薇一直在河里,由于全副武装我们没有认出来。谭琴告诉她有人请客吃火锅,曲薇说有这种好事哪能不去,不吃白不吃。她要众人稍等一会,说完一跃而起,潜入水中。看她入水的姿势,很像受过专门训练。曲薇上岸后向我们招手,大声说她回去换衣服,要谭琴骑车过去接她。谭琴说骑车又累又热,建议我开车去接曲薇。我将摩托车的钥匙扔给了别人,接美女的好事自然有人挺身而出。我不会喝酒,吃完饭后告辞回家了。歌手们在一起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娱乐圈,我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谭琴与丈夫经常闹别扭,每次争吵后她丈夫总是到我屋里找我下棋。入秋时谭琴终于同意了丈夫回家的决定,用她的话说,还是老公说得对,与其在北京没有希望地耗下去,还不如回家做点别的。我看着两口子背着行囊匆匆离去的背影,不禁想到自己的处境。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在失望中匆匆逃离这座繁华的城市。北京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更是一个梦破碎的地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梦而来,弃梦而去。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我的生活像歌里唱的那样“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依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穿梭于人大西门,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刮风下雨不出去摆摊的空闲时间,我便和住在大杂院的几个年轻人聚在一块打打麻将,诈金花。我逢赌必输,输赢虽不大,那时候却看得很重。众人大致差不多,收入微薄,有人因输钱日子过得更拮据,甚至连房租都交不上。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我,院子里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盗窃公司的东西被送进了派出所。好在及时找人托关系才没有出大事。从那以后我极少参与“赌博”了。当时一位河南小伙子在北京郊区当兵,退役后与女友来到北京。他住在邻家院子里,常到我们院子里玩牌,我们都称他“大款”。比较而言他的收入比我们高出很多,至于做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经常看到他与女友等人在人大西门的天桥上卖东西。他很少做饭,经常与一帮人在饭馆里把酒言欢,令人非常羡慕。一次我和他在饭馆里碰巧遇见,他非要请我吃饭,我推脱不掉只好与他同桌。吃饭时他提出与我合伙做生意。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缺少做生意的本钱。他说不用我出一分钱,保证每月收入三千元以上。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想:世上有这等好事?他悄悄告诉我每个月他能够净挣五千元以上。我不免有些动心了,问他做什么。他笑着说没人的时候与我好好聊聊。后来他说与我合伙卖黄色光盘。我吓了一跳,当即委婉拒绝了。我不是傻子,知道卖那东西让警察抓住没有好果子吃。何况警察来了,别人跑得飞快,我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他见我胆小怕事,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每天给我五十元好处费,中午管顿饭。条件是我每天开车到人大居民楼胡同里,带着光盘等他。他们卖完了呼我,我只要送光盘过去即可,实际上我是一个流动仓库。我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于是笑着说,他们每人多带一些多省事,干吗非要用我。他这才道出了实情,说带多了抓着麻烦。他说我是残疾人,别人不会怀疑,警察抓住了没什么大事。我觉得主意不错,既有利可图又没什么大的风险,便故作深沉地说我考虑考虑。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第二天我带着一箱子光盘在人大居民楼里转悠,果然呼机响了。我一看不是卖光盘那些人留下的数字暗号,立即找公用电话回话。原来是曲薇,她说她快不行了,催促我马上过去。我没工夫理她刚要挂电话,她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我犹豫片刻,只好给卖光盘的人打电话将东西还给他们,说自己有重要的事要办,说完匆匆离去。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5(1)
曲薇住在长春桥是为了上学便利,我到她住的地方挪着凳子走进屋子。曲薇躺在床上,面容憔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大事,我气得差点骂娘。心想:没事干吗呼我。她要我坐,说桌子上有香烟自己去拿。曲薇抽薄荷型香烟我不大习惯,说了声谢谢。曲薇似乎有话说又犹豫不决,沉思片刻后问我觉得她“干爹”怎么样。那人胖乎乎的,四十多岁,是一家国企公司的头儿。名义上曲薇称他为“干爹”,实则关系暧昧。曲薇见我不吭声,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她“干爹”挺好的。我心里想:的确不错,有钱有车又能说会道。每次见了我小段长小段短的叫个不停,有时将好烟硬往我衣袋里塞,就是官腔套话多点。听说她老婆在外企工作常年在国外。曲薇怀孕了,问我怎么办。我愣了一下,觉得这种事与我何干,问我这样的问题未免有些强人所难,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曲薇看了我一眼,说她一直挺佩服我。我心想这与怀孕有什么关系呢。她又说想了好几天,想听听我的看法。天呐!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事啊!我们才认识多久?不过吃了几顿饭而已。为什么好事想不到我,晦气的事却想到我。曲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强调说不必忌讳,我有什么说什么好了。我思索了一会,问孩子是不是她“干爹”的,她点头。我问她“干爹”知道吗,她说暂时不想告诉他,好像要挟他似的。我没想到曲薇还是性情中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