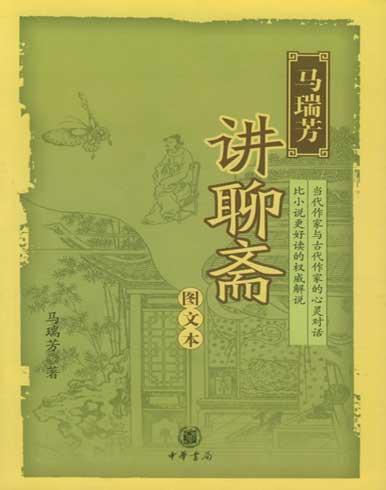马瑞芳讲聊斋-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放蝶
宴会之后入洞房,王勉“视洞房中,牙签满架,靡书不有”,而芳云诗词歌赋,无所不知,问一答十,问十答百。王勉整天对圣贤书顶礼膜拜,芳云却大胆地拿圣人经典开玩笑。王勉这才知道自己只懂得那点儿八股文,不过是井底之蛙。芳云又以“从此不作诗,亦藏拙之一道也”相劝。王勉终于知道“中原才子”跟偏僻小岛的少女相比,既无才气可言,又无学问可恃,“大惭,遂绝笔”。“自念富贵纵可携取,与空花何异”,他不再动辄吹牛,还彻底丢弃了功名之念。
金盆玉碗贮狗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信条;学者立言,贵乎不朽,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座右贾奉雉铭。科举制度下读书人是否还将文章视为千古事?是否还相信“立言”?不。他们实际得很也势利得很。他们,不再用文章关心经国之大业;他们,不再创造千古流传的美文;他们,不再抒发真情实感。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迎合“应制”文体,将自己拉到“科举”这张魔鬼的床上,长了截短,短了拉长。哪怕靠“金盆玉碗贮狗矢”,靠螃蟹、蛤蟆写出的文章,只要能获得功名,就心安理得,求仁得仁。
贾奉雉才名冠一时却屡试不中,他遇到“风格洒然”的郎生,郎生评价贾奉雉的文章确实好,但到科举考试中,肯定不中用。郎生解释:“仰而跂之则难,俯而就之甚易。”贾奉雉考不中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够韩方好,而是写得不够坏!只要将自己降低到科举考试要求,就能如愿以偿!贾奉雉信奉“学者立言,贵乎不朽”,郎生告诉他:除非你决心抱卷终老,否则你就得学习掌握速朽的应试文字。因为考官只懂得也只欣赏这样的文字:“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贾奉雉写的好文章,郎生“不以为可”;贾奉雉将“闒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郎生偏偏说“得之矣”,还“坚嘱勿忘”。郎生在贾朗诵一过后,以符写背,贾奉雉进入考场后,只记得这滥污文字,不得不“直录而出”。他居然因此中经魁!贾奉雉“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认为写出这样文章,没脸见天下人,惭愧之至,自贬这根本就是“金盆玉碗贮狗矢”,决心遁迹山林,与世长绝。
《贾奉雉》写到此,已难能可贵地创造了《聊斋志异》中少有的、强调精神追求的人物形象。意味深长的是,聊斋先生的笔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写仙游归来的贾奉雉:百年后,贾奉雉从仙乡回到人间,发现因为他坚持信仰“贵乎不朽”而不去追求功名,他的子孙都贫穷落魄。贾奉雉不得不捡起狗矢文字,并靠这样的文章做了高官。贾奉雉对“狗矢”文字的决绝和“回归”,描绘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违背良知的悲哀。
第四部分:妙笔抒写民族灾难不懂夫妇爱的书痴丑 1
三仙
贾奉雉用“金盆玉碗贮狗矢”,其他一些读书人如何取得功名?真是蛇有蛇路、鸟有鸟路,旁门左道层出不穷:《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个呆子,在乡试之年,他入闱前,几个书生捉弄他,拟了七个隐僻之题,悄悄告诉他:“此某家关节,敬秘相授。”孙子楚信以为真,昼夜揣摩制成七艺。书生们背后幸灾乐祸地等着看孙子楚的洋相。没想到“典试者虑熟题有蹈袭弊,力反常径,题纸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抡魁。明年,举进士,授词林”。孙子楚高中,用俗话说叫“弯刀对着瓢切菜,完全靠运气”。
《三仙》对取士文体做了富有谐趣的辛辣挖苦:某士子参加乡试途中,路遇三个秀才,谈吐极为风雅,他们邀请士子到“门绕清流”的家中饮酒,且以“场期伊迩,不可虚此良夜”为由,设题作文。秀才喝得大醉,醒来发现“四顾并无院宇,惟主仆卧山谷中。大骇,呼仆亦起,见旁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讶迷惘。视怀中,则三作俱存。下山问土人,始知为‘三仙洞’。盖洞中有蟹、蛇、蟆三物,最灵”。士子进入乡试的考场,惊讶地发现,考试题目竟然就是“三仙”写过的!他将“三仙”的文章照搬试卷上,高中解元!
螃蟹、蛇、蛤蟆,素常在人们眼中,是最不为称道的生物。俗语讽刺字写得不好时,常用“像螃蟹爬的”。螃蟹爬出的文章,竟然造就一位跟唐伯虎同样功名的人物。多深刻、多幽默的讽刺!
不懂夫妇爱的书痴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座右铭,表面是劝学格苗生言,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官本位”权威表述。读书才能做官;做官才能得到金钱、利禄、美女。这“书”不是《庄子》,不是《楚辞》,不是《史记》,不是唐诗宋词,不是小说戏曲,更不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而是四书五经,也仅是四书五经。因为功名利禄的诱惑,聊斋书生的生活重点只有四书五经,生活情趣也只有四书五经,变得像《冷生》里的读书人一样,喜怒无常,像得了神经病。变得像《苗生》里的读书人,什么真正学问也没有,只知道八股文,还要摇头摆尾、煞有介事、不厌其烦地读给根本不想听的人听,连纠纠武夫都说这样的文章一点儿文采也没有,“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笑也”。这帮互相赞赏、互相吹捧的酸书生,终于使得忍无可忍的苗生变成一只斑斓猛虎扑向他们。《苗生浙东生》这戏剧性、寓言性结局暗喻臭不可闻的“闱墨”以及钟情于它们的书生都该从世界上全部消失。
《聊斋志异》写受四书五经毒害的书生莫过于《书痴》。郎生对四书五经痴迷到近于痴呆,“昼夜研读,无间寒暑”,“见宾亲,不知温凉,三数语后,则诵声大作”。大风将他的书刮走,让他无意中陷足古人窖藏的粮食中,他大喜,认为读书读出“千钟粟”。在书架上发现个金辇,认作“金屋”之验,拿出炫耀,被告知是镀金。恰好他父亲的同年(一起考中功名者)来做观察使,有人劝郎玉柱将金辇送他。郎玉柱得到300两银子、两匹马回赠,便认为金屋、车马都应验,是他读书感动了上帝,越发苦读不已。
这位30岁不结婚的痴书生曾宣布:“‘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看到《汉书》第八卷中夹着个眉目如生的纱剪美人,骇曰:“书中颜如玉,其以此应之耶?”名唤“颜如玉”的仙女真正来到郎玉柱身边后,年已而立的郎玉柱却不懂男女情爱为何物,还要请教颜如玉:“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颜如玉授以“枕席工夫”后,他又乐极:“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逢人辄道”,成了笑柄。贾宝玉说:圣贤书将好人变成禄蠹。郎玉柱却告诉我们:死读圣贤书,使人越读越傻,读到连夫妇之爱都不知为何物了。郎玉柱“不知为人”的情节,是中国古代小说写知识分子最具谐趣性、幽默感的章节之一。
书痴
在教会了床上为人后,颜如玉让郎玉柱学习似乎根本与“读书”与“功名”不相干的东西:下棋、赌博、弹琴。郎玉柱以琴棋博艺外出交朋友,倜傥之名暴著。颜如玉说:“子可以出而试矣。”现今社会强调“智商”之外的“情商”教育,郎玉柱就是“高分低能”。他缺少的不是书本学问,而是为人处世的学问。他通过下棋赌博认识社会,提高处事能力,反而有利于考试。但从另一方面看:想升官并不需要真正的学问,只需要会拉关系就行,会赌博会下棋就可以。
第四部分:妙笔抒写民族灾难不懂夫妇爱的书痴丑 2
书痴郎玉柱那份痴迷,那份呆傻,是古代小说中极少见的人物。更耐人寻味的是此人后来的变化。县令想夺颜如玉,将郎玉柱害得家破人亡。残酷的现实,让书痴大开眼界:必须不择手段地爬上去,爬上去可以作威作福,爬不上去就被人欺凌!郎玉柱学会了一整套政治斗争手段,中进士后,处心积虑到仇人家乡做官,细心查访仇人恶迹,终于“籍其家”,报仇雪恨!郎玉柱从只知道书斋死读书到在官场熟练地走门子;从软弱无助、像待宰羔羊的受害者,到纵横捭阖、像狡猾的狐狸复仇;从心思单纯的书痴到心机缜密的官员,郎玉柱做官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是单纯书生“成长”为擅长勾心斗角的官员的典型个案,令人深思。
绣花枕头和梁上君子如果说书痴是明显的受四书五经腐蚀的书生形象,那么可以说,绣花枕头和梁上君子,则是蒲松龄创造嘉平公子的、隐蔽性、深层次受四书五经腐蚀的书生形象。
先看绣花枕头。嘉平公子是位“入郡赴童子试”者,也就是要用自己读的圣贤书去考秀才。他“风仪秀美”,温姬一见倾心,愿托终身。当温姬吟诗希望公子奉和时,公子“辞以不解”,让温姬觉得不可理解但仍然留恋。试后温姬随公子回乡,被发现为鬼,公子家人百术驱逐不得。当温姬看到公子谕仆帖误“椒”为“菽”,误“姜”为“江”,误“可恨”为“可浪”时,留打油诗一首拂袖而去:“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嘉平公子到底考中没有,蒲松龄始终没写。很多聊斋评论家都将此篇看作是对纨绔子弟的调侃。其实,将此篇看作是对四书五经痴迷者的调侃未尝不可:诗词一概不知,写个简单帖子都错字连篇,却要参加科举考试,这“童子试”考什么?提倡什么?不言而喻。
再看梁上君子。读圣贤书读不出期望的效果时,读书人可能比一般老百姓还要悲惨。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家贫又生活无着,只好偷,结果给打断了腿。蒲松龄在《闹馆》中写到读书人的尴尬: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任何其他求生本领,还不如厨师等手艺人可以养活一家老小。有的读书人既想享受富贵生活又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干脆变成梁上君子:姬生白天在人前充圣人门生,夜晚入户行窃。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偏偏“岁试冠军,又举行优”,居然“品学兼优”!《雨钱》里的秀才也热望不劳而获:他认识了言谈优雅的老翁,不向老翁问道解惑而向老翁要钱,老翁略使法术,让金钱纷纷从梁间落下,“秀才窃喜,以为暴富”。当刹那间金钱化为乌有时,秀才非但不认为这是老翁对他的警示而幡然悔悟,反而埋怨老河间生翁,结果给劈头盖脸地痛斥一番:“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做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
《河间生》写河间某生开始与狐交往时,还有所警惕,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就羡慕起狐的“廊舍华好”,“茶酒香洌”,渐入邪道,以至于随狐乘风千里之外,干起鸡鸣狗盗勾当。狐可以随意取酒楼诸人的食物,唯独不敢取一位正人的金桔。河间生由此意识到:狐不敢祟正人,看来跟狐近者必为邪祟。他刚有了这个“自今以往,我必正”的念头,便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河间生盲目地随从狐时是到了“楼上”,等他清醒时,这“楼上”竟然是“梁间”,楼上客人即梁上君子,书生一不留神成了小偷。郭生“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