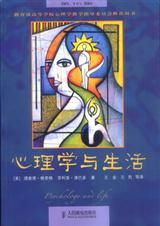流氓心理学:阴山入梦惊魂记-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等等等等!”我打断了她的话,见她面色不善,赶紧解释,“大姐,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话,只是你说的这些信息量太大,我一时理解不了,能不能劳驾你说点我能听懂的?”
她皱皱眉:“那就得从头说起了,啧,你这人真麻烦。”
嘴上抱怨,不过她还真的对我从头开始介绍了。
女孩告诉我,草原上有一种名叫阿合台的巫术流派,和古老的萨满教有些类似,都相信万物有灵,利用灵魂交流来实现祈祷的目的。据考证,它是从西域迁徙到蒙古草原的栗特胡人,与原本居住于此的突厥人文化融合后的产物。时间一久,除了栗特人外,很多突厥人也成了信徒。
“听懂了么?”女孩问我。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我那点可怜的历史知识差不多都还给了语文老师,什么阿合台还有栗特人,简直比火星科技都难懂。
她不耐烦地瞪了我一眼:“一看就是个半文盲。萨满教你知道么?不知道?那么跳大神你总该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我连忙点头,“我姥爷以前得过一场大病,家里人请来个据说很厉害的大神,跳了一天一夜,差点把我姥爷给跳死,后来送到医院才抢救了过来。”
女孩不屑地哼了一声:“跳大神就是起源于萨满教,不过现在几乎都是装神弄鬼糊弄人的。萨满教的灵魂沟通仪式,召唤的对象要么是自然界的灵魂,要么是特定的死者,给你姥爷治病的那位所谓的大神,有没有说他召唤来的是何方神圣啊?”
“好。。。。。。好像是齐天大圣。”
女孩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随即又板起了脸:“阿合台和萨满教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灵魂召唤仪式,唯一也是最大的区别,萨满教巫师是把灵魂召唤到自己的体内,让自己的身体变成灵魂和现实沟通的载体。阿合台的巫师们认为这种做法有风险,所以他们是把灵魂召唤到别的生物体内。。。。。。比如那只鹰。”
提到那只鹰,我不由得伸手摸了摸脸,心中隐隐觉得不安。
“阿合台巫术注重的是攻击性,他们认为只有攻击才是证明强大的标准。”
“明白了。”我插话道,“人家不需要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只需求拎起刀就能打架杀人的土匪流氓。”
女孩撇撇嘴,似乎很不屑于我通俗易懂的解释:“算是这个意思吧。但是自然界的灵魂往往很平和,就算是附到别的生物体内,也不会轻易狂暴,所以阿合台巫术的核心就是,把这些灵魂给逼疯,让它们爆发出最强大的破坏力。比如这只老鹰,就是巫师先把它的灵魂抑制住,再把鼠王的灵魂召唤到它的体内,然后再用咒术锁住,等鼠王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死对头的体内,只有把这具躯体破坏掉才能解脱,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我心里不禁暗暗惊叹,这些巫师真是够阴险的。如果我失去知觉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灵魂被困在仇人的体内,那肯定是各种折腾,不弄个天塌地陷不罢休,反正做的坏事算不到我头上,被就地正法丢的也不是我的命。
越想我越心旷神怡,只恨没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来成全我,直到被女孩一巴掌拍醒。
“你一脸痴呆的在想什么呢?”她轻叱道,“被困在老鹰体内的鼠王想要弄死这个躯体,巫师折断它的一只翅膀和双爪,把它关进特制的灯罩里,用阴山的土壤和秘药混合制成的燃料,把灯放起来。它寻死不得,满心怨毒与怒火,便会发出让所有生物都难以承受的尖叫,这就是阿合台巫术中引魂灯的原理。”
我一边点头一边想,这些巫师绝对都是变态,估计创立这个巫术的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凡心理正常的人,绝对想不出这种阴毒的办法。我靠,这丫头说是要办事,不会是这个阿合台有什么牵扯吧,万一得罪了他们,把我伟岸光明的灵魂转移到什么奇怪的动物身上,那岂不是生不如死?
“你听懂了?”女孩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次你不怀疑我在胡说八道了?”
“信信信,我当然信!”我一边点头一边盘算,万一这位大姐真是个不怕死的勇士,我该怎么说才能让她回心转意,至少别让拖着我一起陪葬。
“那为什么之前我提到长脚的棺材时你不信呢?”她沉下了脸。
我的天啊,果然女人是最记仇的动物,她居然还对那件事耿耿于怀!
“当时咱们不熟,而且棺材长脚这事实在太玄了。”我绞尽脑汁地解释,“这个什么巫术你讲的很明白,我当然相信了。”
“现在咱们很熟么?”女孩冷冷地反问,突然她的脸色又变了,嫣然一笑,笑容纯洁甜美,看得我几乎呆了。
“实话跟你讲,那个长脚的棺材是千真万确的。”她柔声道,“阿合台巫术里的灵魂理论是假的,准确地说,我刚才和你讲的是那些巫师口中的说法,连我自己都不信你反倒信了。巫术的效果或许不假,但什么灵魂召唤转移却另有秘密。”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说我不想掐死你,连我自己也不信。
第10章 大围捕()
此时夜色更浓,风急了很多,身上寒意渐浓,我鼻子一痒,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年纪轻轻的这么不经冻,身体素质不行啊。”女孩鄙夷地撇撇嘴,“袋子里有件长袍,取出来穿上吧。对了,一直忘了问,你是干什么的,看你顶多二十出头,还是学生吗?”
我借着穿衣服的空隙,琢磨该如何回答。告诉她我是个高中毕业的无业游民?不行,之前已经被她嘲笑成半文盲,实话实说面子上挂不住。
这件长袍的式样很像蒙古式,跟女孩穿的那件如出一辙,同样是黑色布面,袖口和下摆缀了一圈兽毛,布面上有深灰色的兽形花纹,像是某种古老的图腾。
我身材瘦削,扎上束腰仍有些肥大,不过倒是立刻暖和了很多。
“我在研究心理学。”我把长袍拉整齐,一本正经地回答。
“哦?”她意外地扬起眉毛,“你是哪个大学的?”
“我正跟着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权威实习。”我清了清嗓子,“这位大姐,我看你见识广阔,谈吐不凡,不知道你在哪里高就?”
“什么大姐,干脆喊阿姨算了,我叫佘颖。”她神色不快,“你叫什么名字?”
“段续。”
“段续?还断断续续呢,什么破名字。”佘颖瘪了瘪嘴。
我听得直来气,心说我这名字是给老段家续香火的意思,你以为你的名字有多好听?蛇影,还杯弓呢!你爹给你起这么个名字是为了吓唬人么?
佘颖向四周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她思索片刻,招呼我继续向前走,走到一道一人多深,十几米长的土沟前,她停了下来,坐在沟边,招呼我也坐下。
“怎么不走了?”我问。
“不知道那帮人在打什么算盘,咱们在这里等天亮吧,那时就安全了。”
“那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巫师么?”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刚才我和你说到哪儿了?”佘颖无视我的问题,漫不经心道,“对了,阿合台巫术的秘密。我先组织一下语言,想想怎么说才能让你听得懂。”
我哭笑不得,心想你可真给我面子,不想回答的问题一律打岔。
“对了,你学了多久心理学,专攻哪方面?”佘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
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叫我怎么回答?我总不能告诉她,我只学了一天,看到二伯把一个压力山大的人弄神经了,把另一个从抑郁症转化成躁狂症,还没彻底弄清原理,就在睡觉时稀里糊涂地地到了这个鬼地方吧?
眉头一皱,我计上心来:“学的时间不长,只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专攻哪个方面倒不太好说,我就暂且举两个病例,你听完大概就明白了。”
然后我把火车上那个男人,以及张大师的情况讲给他听,当然,我把二伯的位置换成了自己。
好在二伯告诉了我治疗这两位仁兄的大概原理,佘颖追问起来,我连编带吹应该可以糊弄过去。
我添油加醋,口沫横飞地一顿吹嘘,本以为佘颖即便不满脸崇敬,至少也会高看自己一眼,不料她的神色越听越凝重,我意识到不对劲,赶紧住口时,她已经面色铁青。
“这些都是那个心理学权威传授给你的?”她厉声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瞠目结舌,看着深仇大恨的架势,二伯啊二伯,这位大小姐总不会是你始乱终弃留下的私生女吧?如果真的是,我说出二伯的名字,她热血澎湃地捅我一刀怎么办?
两个人正在大眼瞪小眼的僵持,远处的黑暗隐约传来一阵唿哨,紧接著响起了密密麻麻的马蹄声,犹如暴雨从远方迅速逼近。
佘颖的神情骤然变得僵硬:“快把袋子给我!”
我乖乖奉上,以为她又要掏出什么神奇的道具,却见她把灯笼扔在地上,一脚踩灭。毫无准备时被黑暗吞没的感觉令我很惶恐,刚想开口问她该如何是好,背后便重重地挨了一脚,向前一扑,摔进沟里,险些背过气去。
等我缓过神来,马蹄声已经到了附近,不知来的是什么人,万一要是那些巫师的手下可就糟糕透顶。我吓得趴在沟底,一动不敢动。
很快,周围策马扬鞭声响成一片,头顶也传来骑手策马跨越土沟的动静。一盏盏灯火的光亮在沟底如流星般掠过,明知不会被听到,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暗暗祈祷自己千万别被发现。
过了不知多久,马蹄声渐渐稀疏,我松了口气,发觉额头上全是冷汗,流到鼻子上很痒,但依然坚持着没去擦拭,生怕功亏一篑。
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响起,向这里接近,临近沟边时突然消失。
“车辆左行,绕过这道沟!”一个粗哑的嗓子大声指挥,“快!快!”
摩擦声再次响起,令人牙酸,不知这车上装载着什么重物,竟然能把轮子压得发出这种声音。
紧接着,一阵水声传进耳中,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劈头盖脸地被泼了一身水。
水很烫,非常烫,烫得我嗷得一声跳了起来。
我狼狈地把灌进脖子里的水抖出,双手在空中挥舞了几下,突然意识到觉得大事不妙。
抬头看去,坑边停了一辆巨大的马车,车上载着一个足有五六个水缸粗的木桶,木桶里挤满了胖得像肉球的女人,她们好像一点没觉得水烫,神情陶醉地用手掌把水浇在肩膀,头顶。
马车旁边立着一匹白马,马背上的中年大汉瞪着双眼端详着我。他的衣着和先前见到的那些骑手相差无几,但头上没有戴着三角皮帽,一条白色宽巾经额前束在脑后,凌乱的黑发随风飘舞,布满青筋的大手握住腰间的刀柄,浑身杀气腾腾。
这种情况,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于是我竭力挤出自以为最友善,最有魅力的笑容,慢慢地抬起手,对他挥了挥。
大汉的一张长脸上泛起怪异的微笑,鹰钩鼻上挤出几道细纹,他抬手摸了摸浓密的络腮胡子,歪头思忖了一下,开了口,语气竟然很温和:
“一看你的打扮,就知道是安分的老百姓,地地道道的好人,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