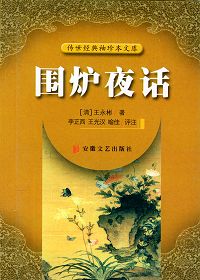夜话-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
丢下兔子还有柴火,天鹜风一样飞奔到门前,一把将那具冰冷的身子搂到怀里,飞快地将他抱起,踹开门,跑到生着炉火的房间,揽过床上所有的衣盖被褥将他包得严严实实,然后再紧紧地将他箍在怀里。
时间在剧烈的心跳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怀中的人那几近结冰的雪白脸『色』这才在炉火的温度中渐渐回转,缓缓张开眼睛,一眼看到天鹜脸上焦急地表情,齐文然这才长舒一口气,只是轻轻一声,却如卸下了心头千钧重担似地,漆黑的眼眸重归于寂静。
不知为何,他这样沉静的神态叫天鹜一阵心疼。
自从从魔界盗花那次以来,每次只要他一离开,哪怕只有一刻半刻,回来的时候都会在门前那看那抹独自等候的身影,表情和眼神一样黯然,默默望着远处,每次只是孤孤单单地站在那里,那身上孤零零的气质就已经够叫他不忍了。
怕他会等坏身体,特地在早晨他没有醒来的时候出去打猎,没想到一回来仍是看到他站立在风雪中的身影,若不是他回来地早,没准他就这么活活冻死了。
一想起这事发生的可能『性』,天鹜的就不禁自责万分,又是害怕又是担心,对他说话的语气也不免比以前带上了几分严肃:
“这么大的雪,你是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体情况还是怎么着?万一冻着了是那么好玩的事吗?你现在可是有了身孕的人……”
说到这里,还是有些尴尬,怕他会记恨自己偷偷将鲜血浇灌黑『色』曼陀罗花汁滴在『药』汁里骗他喝下去事,偷偷看了看齐文然,看到他还是和先前一样地面无表情,懒懒地缩在被子里,眼睛看向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就像完全没听见这句话似地。
天鹜眼神一黯,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悲哀。
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齐文然放平,掖了掖被角,抚『摸』着他如云的黑发,只有面对眼前这个人,他永远无法做到真正心硬,无论是小时候还是现在。
在他的眉心吻了一下,天鹜柔声嘱咐着:
“等了那么久,你一定累了吧?乖,好好睡一觉,我去去就回来。”
刚想离开他的床前,忽然被一双温软的手抓住,转过身,正对上齐文然犀利的眸子:
“有血腥味……你受伤了?”
听到他沙哑的嗓音,天鹜眼睛一亮:
“然,你终于肯对我说话了?!”
自从服下魔花,齐文然的身体就一日比一日无力,整日躺在床上下不了床,吃什么吐什么,去山下一连找了好几个大夫也查不出缘由来,齐文然胡思『乱』想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症,就此心灰意冷,终日不言不语,饭也吃不下。不忍见他意志消沉的样子,天鹜便只得将偷来魔花,并偷偷采集两人献血浇灌养大,将其汁『液』滴在『药』汁里让他喝下逆天受孕之事如实相告。
原以为依他一贯的『性』格,定不会接受以男子之身怀上一贯的宿敌兼妖孽的孽种,即使不气得一走了之也决计不会妥协,一开始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应对,结果没想到齐文然的反应很是平静,沉默不语,只是用刀子一般的眼神盯着他的脸,盯了好一会儿,这才低下头,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自从那天以后就再没有开口对他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和他在一起那么多天,天鹜的心里都没有底。这下听到他竟然又重新开口对自己说话,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立刻扑到床上把齐文然连人带被子抱了起来,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直到看到怀中人因为晕眩又开始苍白的脸『色』这才紧张地把他放回床上,用自己的脸贴着他的脸,高兴地说道:
“太好了!就知道然不会怪我,为了我们的孩子,然也一定会原谅我的,呵呵。”
就知道这家伙保持不了多久的稳重。被他紧紧扣在怀里勒得难受,齐文然推拒着他:
“你的腿还在流血,快去把热水和『毛』巾拿来。”
这时候齐文然有什么要求,天鹜哪有拒绝的份?答应地比谁都快,屁颠屁颠地去准备然要他准备的东西,就连伤口受了热又开始汩汩流血都像是完全忽略了一样,倒比个正常人跑得还快。
走到门口的时候这才想起了那只被扔在冰天雪地里的可怜兔子,跑到原地一看,哪还有什么兔子,别看瘦骨伶仃地,倒挺会逃的。
兀自懊恼了一会儿,想着然还在等着自己,于是这才没去追。
齐文然让天鹜把裤子撩起来,在一眼看到那被一片殷红浸染了的里衣之下那道从大腿蜿蜒到膝盖的狰狞伤口的同时,齐文然就皱起了眉头,一言不发地用『毛』巾沾了水,将伤口中溢出的血水擦洗干净,不一会儿,干净的盆里就满是鲜红的血水。
看到齐文然从头到尾表情严肃、沉默不语,天鹜还当是他为他的伤口而担心,想要逗弄逗弄他,于是就故意在擦洗伤口的时候装出很疼的样子嗷嗷『乱』叫,眼睛眉『毛』都夸张地挤在了一起,可怜兮兮地拉着齐文然的袖子撒着娇:
“然,我的好然然,你看看你相公我都痛成这样了,你行行好,亲我一下,肯定立马就不痛了。”
齐文然斜他一眼,默不作声地躺倒在床上,背过身去,只用一个冷冷的背影面对着他。
天鹜『摸』了『摸』后脑勺,也不知道自己又是哪里惹到他了,他家然的脾气他一向捉『摸』不透,但是似乎受孕之后,这脾气就更古怪了,时常看到他默默望着远处发呆的景象,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讲,偶尔也会听到他的叹气声,难道是因为怀了孩子容易胡思『乱』想吗?
想到这里,天鹜笑得贼贼地,趁齐文然不备,掀起被子一骨碌钻进被窝里,手脚立马像条八爪鱼似地缠上来,死死地扒住他的身体,用手掰,用脚踹都弄不下来,齐文然怒道:
“你快放开我!”
天鹜置若罔闻,笑嘻嘻地把他紧紧圈进自己怀里,无视他一脸怒容的表情,把自己的头枕在他的肩上,用懒懒地语调说着:
“然,我刚才流了那么多血,再加上在雪地里赶了那么久的路,又冷又累,你就让我抱着,暖一暖身体好不好?”
闻到他身上从外面带进来还未消散的风雪的气息,又听到他说又冷又累,想到他自从失了翅膀之后那总是回暖不了的体温,齐文然的心也软了,任他抱着、枕着,许久之后,这才轻声地说:
“你松开我一下。”
天鹜不依,把他抱得更紧了:
“不,我就要抱着你。你的身子比暖炉还暖和。”
齐文然心下羞赧,耳根子一红,用手肘顶了他一下,说道:
“松开!我要翻个身子。”
被他缠得筋骨生疼,好不容易翻了个身,又不得不面对他那满含笑意的蓝『色』眼睛,齐文然一阵无力。
这下,两个人面对面地睡在床上,大眼瞪小眼,从没在在那么安静的情况下和他那么亲近过,被他那双笑『吟』『吟』的蓝眸看得不自在,齐文然垂下眼睫,避开他毫不避讳的火热视线,呐呐道:
“有什么好看的?天天这样看,不厌么……”
“不厌!以后还要看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一万年,一万年,只要是我的然,我爱上的然,看一辈子就不会厌!”
对于他孩子气的话语,齐文然只是淡淡一笑,一辈子谈何容易,父子至亲尚且能互相离弃,他这么说,只是希望自己高兴罢了。
一眼又看出他眼睛里的黯然,摇摇头,心想着他的然怎么就这么多愁善感。
天鹜霸道地将眼前的人的脸转过来,腾出一只紧抱着他的手,缓缓放到他那还未凸起的腹部,强迫他的眼睛看着自己的眼睛,出口的声音不同于刚才的冲动孩子气,低沉沉地,分外柔情:
“然,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我已经不是血族,我现在是和你一样的人,你的一辈子就是我的一辈子。
我从不相信什么天什么地的,我在这里许下的诺言不用天地来作证,只要小天然来为我作证。”
“小天然?”
“恩,小天然,这是我为我们的孩子取的名字,天鹜的天,文然的然,你觉得怎么样?”
“……”
见他沉『吟』着不说话,天鹜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拍自己的脑袋,笑『吟』『吟』地从胸口的里衣里『摸』出了一块木牌,对他说着:
“这是我今天无意中在树林里发现的,竟然是香樟木,有香气,很稀有的,我心想你一定喜欢,所以从狼窝里了回来。”
“狼窝里?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东西……”
“没办法,谁叫它就掉在那地方,不过放心,你相公我勇猛,那几头狼也没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哈哈。”
看着他拍着胸脯一脸自豪的模样,齐文然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见到然闷闷不乐,天鹜只当他心情不好,绞尽脑汁想讨他欢心,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好主意。只见他拿起木牌,用长长的、尖利的指甲在上面刷刷刻出一个“然”字,再把他放到齐文然的手里,笑道:
“小天然还太小了,听不懂我的话,那么暂时就让他代替小天然,见证我对你的诺言吧。”
手里的木牌还带着那人心口的余温,沉默地将它捏在手心里,齐文然看着它,久久说不出话来。
后来又说了几句话,挨不过困意,天鹜慢慢睡着了,看来确实累到了。
齐文然坐在他的身边,借着窗外的月光静静注视着他的睡颜,想了很多,很多——
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与眼前这人有了肌肤之亲,现在竟然……竟然腹中都有了他的骨肉……
若是碰到以前的他,定然不会接受自己的尊严受到这样的践踏的,拼死也要把腹中的孽种除掉,男子逆天受孕,更何况还是人类与妖族结合生下的孽种,经由他的肚腹生下,简直要他死一样。
但是现在……
被自己的亲生父亲当作挟持的筹码毫不留情地重创,又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驱逐出了家族,犹如浮萍一般身无所依的时候又被这家伙带到这深山老林里。理智告诉自己眼前这人是曾经家族的仇人,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对手,是万万不能妥协的,一开始也坚持自己的原则,对他的柔情密语一概无视,甚至也许下了这辈子绝不会爱上他的誓言。
可是那天『迷』『迷』糊糊一夜缠绵之后,醒来的第一眼看到枕边空『荡』『荡』地,满意里只剩下徘徊不去的凉意的时候,心脏的绞痛比被家族遗弃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孤独感与失落感排山倒海地袭来,人生中从没有那般失态过,整个人失控般地跌跌撞撞跑到门外,傻傻地站在门口等了一天,从早上等到晚上,阴雨绵绵,感受着雨点不断打在身上,由外到内一点一点凉透的悲哀,就在以为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的时候,看到了他浑身是血,出现在雨幕中的身影。
从那以后,心底里的一处就像是破土发芽了一样,看到他那张一向桀骜不驯的脸上出现温柔的表情,听到他那张只会讽刺挖苦的嘴里吐出柔情的关怀,那颗冷硬的心就会软化一点,再软化一点,这种感觉让他无端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