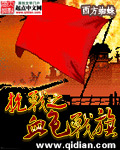抗战之谍海浮生-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尝你面前的茶水,滋味如何?”
羊脂玉色的茶杯,光洁玉润,在秋季奈绪的眼前随着烛影的起伏而晃动。
“义父,这次为何不用紫砂茶杯,而改用白盏?”秋津奈绪试图控制对话的节奏,他心里打鼓,没有底。
“这茶是我专程派人取来的惠山泉煎煮,味甘质轻。”东条英机道,“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苏轼的诗句虽美,终道不出茶水的韵味。”
“何以见得如此?”
“因这水澄澈见底,虽杯满而不溢出,人间绝无第二的泉水,能达到此中的况味。”
“义父似乎话中有话。”秋津奈绪觉察到话中的机锋,倒不如直接摆到台面上来说更妥帖。
“我素来是不喜欢与人翻脸。”东条英机语带迟缓,“张先生,要不要用手巾揩拭额角的汗珠。”
说毕,掷过一条天蓝色的手巾。
手巾躺在地上,死尸般,嘲笑着五味杂陈的秋津奈绪。
如果去捡起来,证明自己心里有鬼如果不去捡,自己则又显怠慢。
“义父,有话但说无妨。”秋津奈绪豁出去了,他静坐在原地,不动如山。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支那人的古训,放在今时今日,似乎仍旧适用。”
“此语大不契合今日的场景。”秋津奈绪道,“倘若适用,则帝国所宣称的共荣圈,更有何用?难道对于异族都要赶尽杀绝?”
“绝非此意。”
“始皇初年,摈弃六国游士,李斯以谏逐客令驳斥谬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秦能一统华夏,哪一干才出生秦地?”
“无忠心,有才何用?”
“忠心与否,要看主子是否值得追随?倘若毫无前景,纵然是金山银山,弃之如敝屐而若一派光明,便是饥餐渴饮,何妨视之若珍宝。”
“张先生语气过于偏激了。”东条英机听出了他话中的诚意,“既然如此,张先生何日启程,径直入虎穴,送假情报于第九战区程潜处。”
“择日不如撞日,天亮即行。”
“如若被程潜发现有假,何以对质?”东条英机步步紧逼,气势咄咄迫人。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军情讯息万变,我相信程潜也明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哪能全部照本宣科,而不做变通?况且我的情报也是有无关痛痒之真事,以小利诱之,不怕他不上钩。”秋季奈绪说出他的盘算。
“来人,给奈绪斟满!”东条英机大声嚷道。
从话语中,秋津奈绪听出了危机已经过去。
沸水的弧线划过凝滞的空气,倾倒入白瓷盏中,热气氤氲。
“那我以水带酒,温酒敬秋津课长。”东条英机远远地举起杯盏,一饮而尽。
今夜,东条英机本想试探秋津奈绪此人是否可靠,没想到他果然没有令自己失望。因为,送情报一举,事关全局,一招出错,满盘皆输。他输不起,他的败绩,只会让蒙羞。
“使不得,义父,理应是奈绪敬义父。”他也一饮而光,亮出杯底。
晨曦出现,旭日未升,又是一个朝霞满天。
窗内凝霜,白茫茫似雪花片片,蔓延在窗口内侧。
昨夜一宵惊魂,郑颐玹目睹史茜妮的潇洒干练,叹赏不已。
“茜妮,没看出,你这小小年纪,居然在那种情景下,敢于硬闯进去。”
“郑书记,其实我就像一个莽夫,硬着头皮闯进去的。”史茜妮飞红了脸颊。
刚才此处时,她甚为排斥组织的习性。“无自由”,她气愤地把自己最爱的琥珀色发梳扔向房门,郑颐玹刚巧路过门外。
“自由?”郑颐玹讥讽道,“你哪来的底气敢要自由?”
“一个人,只要可以自来自去,何须被拘禁于此。”史茜妮愤愤地说,“荒郊野岭,生不如死。”
“你想怎样?”
“为什么不派遣我上阵杀敌?”史茜妮目中怒火燃烧。
“杀敌?”郑颐玹重复了一遍,“你有这个胆量去做,我还没这个胆量派你去呢?以你的能力,只会葬送组织的生命,其他同志的生命,你敢拿枪吗?”
郑颐玹将自己腰下佩戴的驳壳枪解下,反手递到史茜妮的面前。
史茜妮夺过枪,在手中翻来覆去地把玩,一脸不屑地说“有何不敢?”
“拿枪对着我!”郑颐玹脱口而出。
“什么?”史茜妮说道。
“我叫你拿枪对着我!”郑颐玹大声吼道。
“我”史茜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举起枪,可是准星总是瞄不准,才一秒,她的手就颤颤巍巍起来。
“手抖什么?”郑颐玹质问道,“你不是挺自以为是吗?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是个豪门大小姐,出入要有仆人侍应。如今居然连一把枪都拿不稳。”
郑颐玹呵呵笑道,那笑声中透出了对史茜妮的鄙视和嘲讽。
史茜妮用尽了气力握住枪把,她愈是用力,愈是握不住。她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出汗,从她白净的肌肤毛孔中沁出。
她放弃了,把枪收了起来。
“你自己好好想想,自由二字,不是你能说的出的,你现如今还不配让别人给你自由,自由,是要自己争取得来,我能给你自由,也能随时剥夺。那样你得到的不是真的自由,是奴役。”郑颐玹声如裂帛,摔门而出。
史茜妮趴在床铺上失声痛哭,孟芳蕤闻讯前来安慰,可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
史茜妮的心已死,她把人生想得太过于简单,离开了离开了父亲的庇佑,她一文不值。
此后数日,她都一人沉浸在悲痛中,闭门不出。
经过几日撕心裂肺的剧痛,她走出了自己的房间。细雨绵绵,湿冷地浇灌在身上,从她的头顶冲泻而下。
她自己何曾失去自由,是她把自己的心蒙蔽了。让滩的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目迷五色,这里有杀戮,有牺牲,有山河破碎,有生离死别,就是没有儿女情长,也没有莺莺燕语,没有花天酒地,,没有摩登时尚。
是时候同自己的过去道别了,她把过去的所有记忆一概抹杀。
“咔嚓”一声,闪电劈倒了不远处高冈上的一株巨木。
忽喇喇,巨木倒在原野上。
第三十八回 断情思荒城古渡 敞心扉泪眼迷离()
人就是那么奇怪,昨日的伤痛,在当时是撕心裂肺的呼喊,日后隔着岁月的空间回望,怎么都触及不到内心的敏感。许多情感,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快的如春梦一般毫无痕迹,如秋草枯槁一般立时枯黄。然而,心一旦死寂,怎么也唤不回当初的悸动。
史茜妮涕泣涟涟地俯身痛哭,她弯着腰,猫在地上,失魂落魄地待在滂沱冷雨中,眼神中夹杂着一丝伤感和痛楚,然而这伤感,着痛楚倘若剔除不掉,便会如蝮蛇嗤手,牵连着心脏。
是时候该壮士断腕了。
她仍旧记得,孩提时代,妈妈的一位好姐妹卫诺兰因为情人在白色恐怖中命丧黄泉,而痛哭不已,素白的锦帕,浸湿了泪水,泪眼中仍旧止不住的从指缝间,从锦帕地下,悄无声息地滴落在地上。
“吧嗒”,溅起了一圈泪花。
“妈妈,诺兰阿姨为什么一直在哭鼻子。”小茜妮摇着妈妈的手臂,黑黝黝的眸子里尽是好奇。
“黄叔叔离开了,阿姨心里挺难受,接受不了。”妈妈俯下身,闲闲地说。
“如果有一天,妈妈离开了你,你会怎么办?”妈妈咳嗽着,身子一颤一颤,如风中残烛。
“我不要妈妈离开我!”小茜妮紧紧地环抱着妈妈,她幼小的手臂怎么也绕不过妈妈的身子,她静静地贴在妈妈身上,谛听着妈妈的心跳,和血液在血管中跳动的韵律。
一年多后,妈妈在贫病交加中故去,临死前,躺在病房里的妈妈把小茜妮交给了站在一侧的卫诺兰。
“诺兰”,妈妈气若游丝地说,“你一定要把茜妮交到她爸爸的手里!”
“璟茹,我答应你的事,就说到做到,你就放心地去吧。”卫诺兰哭嗓着,她已经泣不成声。
妈妈望着卫诺兰的眼眸,孱弱的身子里积蓄了最后一股力量,她伸出枯瘪的手指,想拉一下卫诺兰手,表示感激,然而她挣扎了一番,倒在了床头上。
妈妈就是这般凄凉的故去,剩下在床前没命地哭喊着地小茜妮。
这是史茜妮最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狂风暴雨中这段记忆再次浮现在脑海,还是那么的清晰可见,历历在目,让她后怕。
“茜妮,你在哪里?”恍恍惚惚中,史茜妮仿佛听见一声声妈妈的召唤。
妈妈在湍急的河流对面,暴涨的河水在不停地咆哮,怒吼,把妈妈的呼喊声冲散在空气里。背后遥遥可见是坍圮的城墙,影影绰绰。
“我在这里。”茜妮想喊出来,可是喉咙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只有嘶嘶的若若的声息,压根没有周围的雨声大,更别提能越过河床传递到对面。她愈是焦急,愈是撕心裂肺地呼喊,愈是没有声音。
雨愈下愈大,遮住了视线,一切都朦朦胧胧起来,妈妈的轮廓已经辨别不出,湮没在漫无边际的淡灰色的天地之间。
“茜妮!”有人在用力地晃动着她的臂膀。
“芳蕤。”史茜妮缓缓地睁开眼睛,孟芳蕤撑着雨伞,雨水顺着伞边入注地浇在她身上。
史茜妮一头栽入她的怀里,昏睡过去。
等到史茜妮再度睁开眼睛,郑颐玹、孟芳蕤等一干人围绕她的四围。
“茜妮,你醒了。”郑颐玹悄声细语地说。
“郑书记,我”史茜妮感觉嘴唇发干,声音嘶哑。
“你先不要说话,耐心调养身子。”郑颐玹如一个母亲般安抚道,她的手摩挲着史茜妮的发梢,“傻孩子,这么大的雨,你怎么一个人跑出去,出了事怎么办?”
刹那间,史茜妮发现眼前这个曾经声严厉色、高高在上的郑书记,转换了一副爱意融融的慈母模样。她胳膊环抱着郑颐玹的腰肢,这一刻,她的心中有万千委屈,似千万个躁动的脱兔,紧绷着她的神经,撕扯着,拉拽着,她在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郑颐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示意其他人都退下。
“孩子,人最怕的是做傻事。我年轻的时候,也傻痴痴的,以为人世间只要自己愿意的事,哪怕是山高路远,哪怕是地角天边,没有做不到的。当时正值革命的低潮,我从一个热血青年,冲破了家庭的羁绊,打破了世俗的缰锁,可是最后,目睹着一个个的好友头颅落地,昨天那个人还在冲你微笑,今天已赴黄泉。在那段沉沉暗夜的岁月,我还在襁褓中的孩子,也凄凉地死去,就在我的怀里,我那时候歇斯底里如同鲁迅先生在祝福中的祥林嫂。”郑颐玹说道伤心处,不禁黯然泪下,“好一阵子,我才缓过神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史茜妮抽搐着说。
“我凑巧路过一座寺庙,听一位长老讲经说法,他讲到一条偈语人世有八苦,皆作茧自缚。来所从处来,归所从处去。”
“是什么意思?”史茜妮渐渐缓过神来,娇滴滴地躺在郑颐玹的怀里。
“人世的八苦是,生、老、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