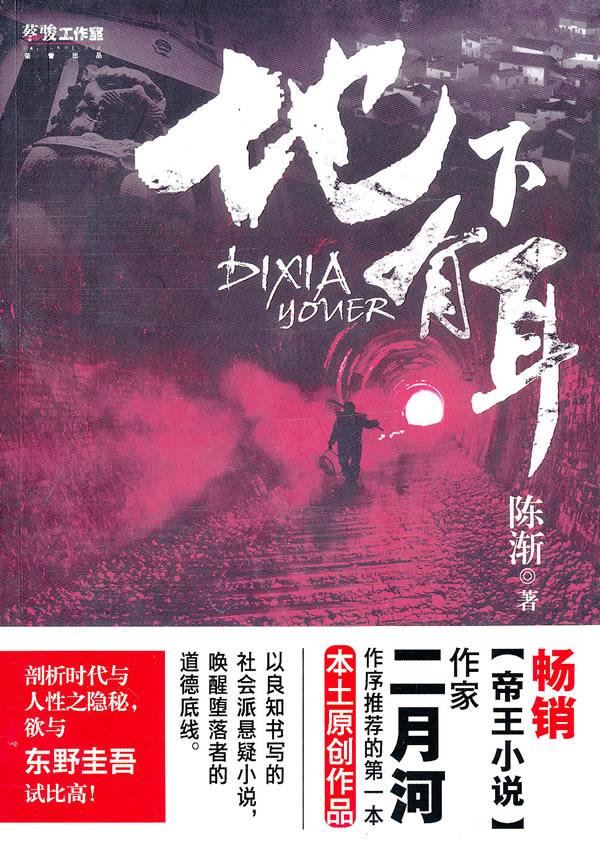地下有耳-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话音未落,只见奥迪车猛地蹿了出去。在众人的惊呼中,黑色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甲虫凌空飞了起来,飞出山道的依托投向虚无的悬崖上空。警察们目瞪口呆地望着奥迪车略微倾斜地在空中平平抛出,越过近十米宽的山涧,就在即将坠入悬崖的刹那,车前轮搭上了对岸的石壁,横着一滑,车身的一半挂在了悬崖上,两只后轮悬在了虚空。
车门开了,李澳中转了出来,绕到另一侧拉开车门,把白思茵拽出来。人一出来,车子前半部顿时轻了,车头翘了起来,晃了晃,带着一团碎石栽近了断崖深处。久久不见回响。
两岸的人隔着深渊面面相对,沉默无语。涧底的流水浅浅可闻,带来似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山间的归鸟寂寞地鸣叫,在浓烈的夕阳里拖出孤独的痕迹……众人沉默着。
李澳中摘下枪抛了过来,何顺生接在手中。
“我赢了。”他说,然后看了白思茵一眼,“是你赢了。”拉着她的手隐入山坳中。
金副政委举起了微冲,郭念孙握住枪管压了下去。
“为什么不开枪?”他恼怒地问。
“他说的对。”郭念孙黯然说,“他的确赢了。”他苦笑一声,“上帝判了他无罪。”
“那么……就撤?”叶扬问。
“不能撤。”金副政委慢慢地摇头,“他有罪没罪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一旦让个罪犯进了北京城,丹邑县大大小小的乌纱帽只怕会落下一大片。追吧!”
“追?怎么追?”杨队长嗤地一笑,“像他一样飞过去?只怕上帝未必会判你无罪。”
“你?”金副政委对他怒目而视。
“算啦!”何顺生摆摆手,“吵什么!杨明义!”
“到!”杨队长立正。
“你和老金各自带一批手下绕过悬崖继续追捕。老郭,咱俩回去写报告吧!”何顺生苦笑,“他妈的李澳中,有种!不愧是咱公安局出来的。好了,回去给他擦屁股吧!”
看守所武警和刑警队都隶属于公安局,两帮人马一听都笑了:“他妈的全国几十万公安,有几个能像咱们局的敢玩儿命!”
何顺生钻进了汽车又探出头交待:“老金、小杨你们听着,现在李澳中交了武器,你们没有受到致命的攻击时绝不能开枪,懂吗?”
“明白!”两人频频点头。
3
又回到了大山。母亲死后,已经有三年没有回过那个贫困的山村了。李澳中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十几年来,山林的印象早已淡漠,仿佛妻子衣柜角经年不用的旧纱巾。查案、蹲点、追捕、通缉,在茫茫的人世间东躲西藏,亡命天涯,连惟一证明自己存在的下一代都养不活。这一生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眼前的山岭绵绵不绝,像凝固的海浪,寂静地翻腾。童年时期,他在山中放羊、打猪、挖草药,他无时不刻不在呼吸着,他感到它搏动的生命在眼前伸展,然而离开之后又回来,它沉默了,死亡了,像一座亘古不变的的化石,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任他的皮鞋在自己的躯体上践踏。
他知道,这是一种拒绝。山以外的人是无法感觉山的,就像何局长无法感觉自己那把被没收的手枪。它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联系,一种血与根的对话。
大山又活了。
他感到无比的平静,一种被容纳的幸福。这里是太行山的主脉,从东北而来,向西南而去。他们顺着山谷往西,头顶的天空被切成一条丝带。谷中低凹阴湿,土层丰厚,松、栎之类的乔木很少,到处是与人胸腹齐平的荆棘、酸枣之类的灌木,它们伸出一只只小手勾着李澳中的棉囚衣,撕裂棉布,把棉絮掏出来挂在枝头炫耀。
谷中转眼就黑,像猛然给人掩盖的地牢,阴冷可怖,不辨方向。这里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方才循着走的兽道也遮在灌木丛下找不到了。李澳中折了根粗大的荆条在前面探路,披荆斩棘,打得枝叶乱飞,惊起归巢的宿鸟东一头西一头的乱窜。
白思茵猛然想起一件事:“这山上有蛇没有?”
“山上怎会没有蛇呢?菜花蛇、黄条蛇、白条蛇……”
白思茵牙齿打颤,紧紧抱住他胳膊。他觉醒了,连忙改口:“现在天冷,蛇类大概还在冬眠吧?”
虽然语气不太肯定,白思茵也大松了口气,放开了他。
前面是一座横岭,他们攀着裸露的岩石上了岭,明月挂在东山,照见了巍峨的山势,山头在明月的照耀下亮晶晶的,其下皆是无底的黑暗。白思茵一上山顶便呆了,只见岭脊突兀,两侧是陡峭的断崖,一条小道歪歪扭扭攀了开去,道上山石狰狞,三三两两的油松从石缝里探出,树冠庞大,或是到向悬崖,或是遮断了道路,实在险极。野兽的吼声凄厉悲怆,一声声震动山野,暗处的夜枭发出冷笑似的长鸣,远远近近,不知何处,更增添了难言的阴森和诡秘。
“咱们往哪儿走?”她胆怯了。
“往西。”李澳中简短地回答,似在侧耳倾听,神情颇为紧张。
“你认得路么?”
“不认识。”李澳中不走了,戒备地望着前方。
“那咱们去哪儿?”白思茵心里害怕,不停地说着。
“去我家。”他双手握紧了荆条,“我老家离这了大概二十里,叫黄岩嘴。小心——”
白思茵吓得一呆,隔着他的肩头望去,前面的松树下闪起两粒绿茵茵的东西。一只野狼。
那只野狼显得又累又饿,吐着血红的舌头吁吁直喘,两只前爪不停刨着地面,在白思茵惊叫的同时已腾空扑了上来,直奔李澳中的咽喉。李澳中大喝一声,粗大的荆条准确地劈在它的脸上,力量强劲之极,把它劈得横着摔了出去。
“这是一只老狼。”李澳中冷笑一声,“来吧!”
那狼咆哮着,嘴里咕咕有声,愤怒地盯着,却不进攻。一人一狼就这么对峙着。凄冷的峰岭,幽暗的松林,明月斑斑驳驳照彻着人与兽的战场,一个少女瑟瑟而立……李澳中注视着老狼那瘦长的脸。它确实老了,皱纹横生,眼屎挂满眼角。他看见了它内心的恐惧和渴望。一种深深的悲哀。狼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袭击人的,它们凶残而胆怯。人是直立的动物,在它们眼里很高大,手里又有能喷火的毁灭性武器,是极其可怕的。一般情况下敢于袭击人类及其村落的极少有捕猎能力强的壮年狼,它们知道,一旦冒犯人类,将会导致残酷的报复。铤而走险的都是一些老狼,为了生存,为了填饱肚子,它们甚至敢向虎豹挑战。它老了,已经被山林遗弃。就像自己一样。
对峙中老狼突然放了个响屁,仿佛肚里最后的东西也给放了出来,它不再犹豫,迅急无伦地扑向李澳中的咽喉。李澳中一棍又击中它头颅,摔倒之后它一翻身又扑了上来。山道狭窄,它无法发挥动物灵活的特长,只能笨拙地往前扑咬。一次次给劈倒,又一次次爬起来,它的脸被劈中七八棍,满头满脸都是血,但它决不退让,把李澳中逼得连连后腿。混战中,他的棍子被狼牙咬住,嘎巴一声,在利齿下断成两截。老狼趁势向他怀里拱了过来,惶急之中李澳中伸手掐住它脖子,一人一狼抱在了一起。狼的后腿直立,前照拼命地抓它他胸腹,转眼间棉衣尽破,臂上给抓出道道血痕。李澳中大喝一声,双臂使劲一提,把它提离了地面,拼命地向外抛去,老狼撞到崖边一块岩石上,发出一声惨叫,翻滚几下,掉进黑暗的深渊。哀鸣声久久不绝。
两人精神紧张,怔怔的望着悬崖半天喘不过起来。白思茵扶着胸口,脸色煞白:“吓……吓死我了!”
李澳中坐到了地上,喘着气:“幸亏是一只孤狼,要来了一群,今天就完蛋了。”
“你很早就看见它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白思茵脑他。
“我们同时发现了对方,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李澳中站了起来,“它怕人,我又何尝不怕它。我十五六岁时在黄岩嘴打过狼,不过都拿着火铳,徒手……从来没有过,一跟你说,吓坏了你我就分心了。”
白思茵轻快的扑进他怀里,红唇封住了他的嘴:“我喜欢,这样的男人才值得我依靠。”
李澳中沉默了:“这是在深山。你的力量在外面的世界,在那里,你根本不需要我保护,我任何事也帮不上你。”
“我的内心永远在这孤独的山林里。”白思茵深情的注视着他,“手里的金钱无法带给我安宁。”
李澳中捧起她的脸:“在驱车跳崖之前,你要留下来陪我赌一把。我说过,赌赢了我就抛开一切,和你结婚。我说到做到。”
白思茵忘情地点头。
又翻了几座山岭,渐渐走不动了。山间月光晶莹,织出一种非人间的意境,阴风呼号,松摇影动,远远近近鸟啼兽哭,似乎走进了幽冥鬼域。白思茵的体力接近虚脱,几乎要崩溃,一路全赖李澳中搀扶。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天色渐渐发亮的时候,大山忽然活了。成群结队的野鸡鸽子噗噜噜的从岩石中飞出,咕咕叫着盘旋在林野上空。凤头白灵三三两两的窜上枝头,清脆婉转,相对而鸣。滚圆的山鹑肉弹般在树梢林间突突乱射……他们深知听见了野山羊的咩咩叫声。
李澳中露出痴醉的神情,喃喃地说:“这里就是黄岩嘴。”
4
黄岩嘴村位于一个半山坳里,仅有七八户人家,一座大山小平的山峰透气这座村子,三座大山翠屏峰一样聚在四周,山腰是一层层的人共开垦的题梯田,只能中一些生命力强的玉米、谷子、豆类和鼠类。田头村周满山都是核桃树、柿子树、和苹果树之类。村前一条小河顺着出山的唯一山道弯弯蜒蜒向南淌去。
李澳中和白思茵趟过小河,一进村便惊起了密集的狗吠。李澳中解释,山了狼、獾、野猪之类很多,家家户户都养有四五条狗。狗吠声中,有人出来了。一个老人,过这一件破夹袄,提着一管旱烟,一见李澳中,征了,瞅了半天,忽然叫了起来:“狗娃!你是狗娃!老根!羊倌!他婶子!土丁!来福!快来,你们看谁来了!”
他刚设下一个悬念,还没等人出来问,自己忍不住又叫:“狗娃回来啦!”
李澳中瞥见白思茵惊讶的表情,老脸一红:“别笑,咱就这名字。”
白思茵一呆,咯咯咯笑得直不起腰。笑声中,各家各户老人小孩男人妇女纷纷跑了出来,围住它们七嘴八舌说个不停。说的一快,白思茵一句也没听懂。李澳中也操着一种怪异的腔调和他们交谈。
众人七手八脚把两人往自己屋里拽,李澳中摇摇头:“板儿爷,根叔,土丁叔,来福哥,我先跟你们说清楚,这回我是落难了。被人陷害,进了监狱,我逃了出来,没地方去。”
众人一呆,纷纷破口大骂。骂山下的人。“娘个头,上下没个好东西,咱狗娃给他们抓贼,挨刀挨枪,死了多少回!咋恁不讲良心!”
土丁也骂:“去年我挑了两筐柿子到神农镇,还没换东西,县塘我叫啥费!我哪有钱?我穷山沟里要钱有个屁用,都他娘换盐换火柴,谁卖?他娘的不交钱就不让我换,不换我有个屁钱!好说歹说非要扣我一筐柿子。”
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