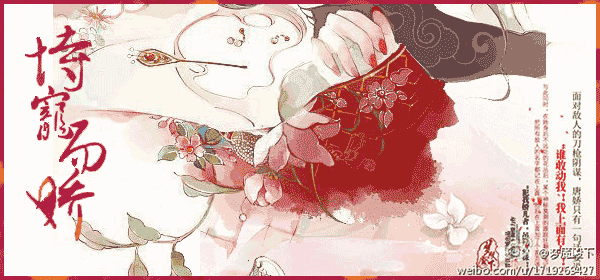好姑娘恃宠而娇-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知道傅攸宁自那样高的位置摔下来,定是伤得不轻。
见梁锦棠已飞身到了傅攸宁身边,却始终未下达撤退的指令,孟无忧眼中泛起热泪,却又笑着,大声喊:“不用管我!”反正他去年也是被抬着回京的,呵。
梁大人至此也仍未想要丢下他,哪怕他此刻名义上已是一具尸体。
这就足够了。
他是堂堂光禄羽林左将孟无忧。
不过是场春猎。他输得起。这是羽林男儿的骨气!
季达终于忍不住恼了,右手一拳朝他挥过去:“就跟你说尸体不许说话!”
乍然被击倒在地,孟无忧侧眼看着梁锦棠远远对自己点了点头,终于做出撤退的手势,这才长吁一口气。
确定他们几人已全部撤走,孟无忧抬手擦掉唇角的血迹,就地躺着,笑得眯起了眼睛:“季将军,你今年多大了?”笑音里有些哽咽。
季达也是又累又痛,一时又沮丧,便跌坐在地,诧异地低头扫他一眼:“二十二。怎么了?”
“只较我长两岁啊……”孟无忧低喃,忽然笑了,“你是赢不过他的,永远也赢不过的。”
季达以为自己下手没轻重,把人脑子给打伤了,赶紧让被拔掉信号焰火后一直在装尸体的小兵们过来,要抬他去送医。
“他十六岁御敌于国门之前,二十一岁统领帝京城防。从军无败绩,追凶不落空……”孟无忧早已累极痛极,自是乐得由他们处置,只闭目坚定低喃。
“他在军中,是将星;他在帝京,是武首。不论身在何处,他都达到了那个位置最顶尖的辉煌。”
“便是你将来有一日,不懈努力达到了他那样辉煌,也绝无可能如他那般少年得志。”
“这世间,只会有一个这样耀眼夺目的梁锦棠啊!”
季达在铺天盖地的震撼中,忽地被一把雁翎刀击中。照规则,他死了。
孟无忧见状,原也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梁锦棠并未现身,只有声音穿林而来。
“剩下的几个,若这是真的战场,你们都死了。”
季达一双眼睛气得血红,大吼:“凭什么?”
“你确定,在两军对垒之时,已撤走的敌军绝不会去而复返吗?”梁锦棠的声音忽地寒意凛凛,“你们,当真战至最后一人了吗?”
季达被梁锦棠的话惊出一身冷汗,如梦初醒。
春猎,是光禄府的春猎。可对河西军来说,哪怕只是一场合兵演武,也该当做真正的战场。
他蓦地想起自己的主将萧擎苍曾讲过,梁将军当年有训:
素日练兵、武训诸多艰难,为的是在战场能少死人。
哪怕打到只剩一人,也绝不可后退半步,这是与敌对垒时的义务。
时刻警醒,枕戈待旦,这是沙场铁血里为人将帅的人道。
“回去转告萧擎苍,西境才安稳不过五年,河西军斗志就已低迷至此,等着被成羌的铁蹄再踏回来,才会重新警醒是吗?!”
虽不知梁锦棠此刻藏身何处,但他们都知,他的目光此刻一定正看着这里。
季达与整队河西军顿时肃立,齐整、徐缓地,行了极其庄严的军中之礼。
“梁将军,范阳见!”
原来传言诚不欺人,他果真是不可战胜的梁锦棠。
这世间,只会有一个这样耀眼夺目的梁锦棠。
25。第二十五章
当梁锦棠拿了索月萝的一把雁翎刀; 又独自反身折回去时,索月萝、百里束音与程正则皆是惊愕地望着他的背影; 困惑到久久不能动弹。
但傅攸宁却不及多想,趁众人的目光尚未回到自己身上,赶紧偷偷从腰间暗袋中取出一颗丸药胡乱塞进嘴里。
丸药渐融,满口全是苦。心中更是苦到气血翻涌。
一身狼狈的索月萝捂住肩上的伤口; 望着梁锦棠消失的方向,莫名其妙地转头向百里束音道:“他拿我刀干嘛?”
百里束音被问得也是一愣:“去……‘抢尸’?”嗯; 大约还是想将孟无忧那具尸体带走吧。梁大人果真义薄云天。
索月萝本想翻个白眼,却扯痛了颊边伤口; 忍不住龇牙痛嘶一声:“怎么可能,这儿还有一个差不多被摔废了的傅攸宁呢!”
照春猎规矩; 若要带着已被拔掉信号焰火的同僚一同前行,“尸体”是不能自己走的。这儿眼瞅着一堆伤员; 孟无忧那具“尸体”抢回来谁背?以索月萝对梁锦棠的认知; 他不会冲动到做这样傻的事。
说到傅攸宁,三人这才赶紧回身去瞧她。
此刻她脸色惨白; 唇上毫无血色。见众人看过来,也只是安静地笑笑。
索月萝关切地打量她:“站得起来吗?待会儿搀着你走能行吗?”
离范阳城还有约五里多的路程,踏过这最后一段路的人; 便是胜者了。
傅攸宁缓缓点头,表示自己可以。
“素日里不是话挺多?摔着舌头了?”索月萝虽瞧着她那样子挺惨; 却也忍不住好笑。这傅攸宁也真是怪; 分明不经打; 却又挺能扛。
她一向看人极准,如今对傅攸宁倒是说不上该如何评价了。
百里束音见傅攸宁那样子,心中有些担忧,却还是笑意勉强道:“算了,还是别叫她讲话了,说不得一张口就吐出一盆子血来。”这梁锦棠咋还不回来?得赶紧将傅大人送到范阳城让大夫瞧瞧呀。
旁边一直闷不吭声的程正则大惊:“一盆子血?那她还不给吓死啊?”
百里束音仿佛这才想起新添了个人,定了定神,回身看向他,顺手拍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年轻人,你要知道,这世间很少有哪个姑娘会被血吓死。否则,每个月且得吓死好几日呢。懂?”
“这位大姐,”程正则黝黑的面庞神色霎时僵硬,细细瞧去颧骨还有诡异的红,“我是个男人。”
“看得出来,怎么了?”百里束音双臂抱在胸前,上下打量他。
程正则已是满脸的生无可恋:“那我为何要懂这种事?”
索月萝在一旁笑得伤口都快飙血了。
傅攸宁只想抬手扶额,却发现自己右手掌心上全是血迹,只得暗暗将手放下,满面无奈,轻叹。
“我怎么,总遇见你们这种……乱七八糟的人物。”傅攸宁苦笑慨叹后,还是为这初次见面的二人引荐。
“百里束音,东都分院副指挥使。”她以下巴指指百里束音,对程正则道。
又转头看向百里束音:“程正则,总院候补旗小旗。”
两人静静以目光相持良久,最终并未按各自职级行武官礼,而是抬手向对方抱拳,行了江湖礼。
“有病啊。”索月萝一头雾水,身上几处伤口又痛着,便缓缓跌在傅攸宁身旁,与她抵肩而坐。
傅攸宁顾自忍着胸中翻涌的气血,努力维持着面上平静的微笑。
百里束音与程正则却是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
他俩相互不行武官礼,全因彼此都自对方的眼神里确认了一件事。
他们分明有同一个向往的心愿——
愿为傅大人门下走狗!
在这两人莫名其妙的惺惺相惜中,梁锦棠已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索月萝一见他是空手回来的,顿时瞠目结舌:“梁锦棠,我刀呢?”
“拿去将季达干/掉了。”
索月萝傻眼。她使的是雁翎双刀,这下变单刀了!真是要命,跟衣裳都配不起来了!
梁锦棠懒得搭理她,神情冷肃地直直走到傅攸宁身前蹲下:“伤处检查过了吗?”
傅攸宁没敢答话,双唇闭得紧紧的。倒是索月萝带嘲轻嚷:“梁锦棠你差不多得了啊!眼下这儿除了你,谁身上没伤啊?”检查个鬼,又没大夫在。
果然是关心则乱么?
“手怎么了?”梁锦棠对索月萝的叫嚣充耳不闻,瞪着傅攸宁还想将右手藏到身后,便抓住她的手拉过来。
他手上的力道倒是温柔的,可一张口就开始喷火:“先前为何走神?朝季达发出第一箭后就该换地方,没人教过吗?!还有,没箭了就没箭了,学人炫什么技?!”全然忘记刚刚还在前头教季达做人,失望于河西军没有战至全力。
傅攸宁被他吼到发懵,喉头止不住泛起甜腥,只拿一对梨花眸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不许骂她!”百里束音与程正则不约而同地喝止。
“我那叫骂啊?!”梁锦棠气不打一处来,转头瞪向他俩,回头又见傅攸宁满眼委屈和忍耐,声量顿时就下去了,“我只是吼……”
他话音未落,傅攸宁当真再忍不住,一口血喷了出来。
众人傻眼。
梁锦棠又急又气,手上放得极轻,将她抱起,向其他三人迁怒道:“还不走,等着被人追上来砍啊?”
心下却是止不住咕囔,这个家伙,竟连吼都吼不得。
x的!他还是头一回将人吼到吐血。
他能怎么办?他也很绝望啊!
************************
四月初五未时,这一行五人率先抵达范阳城东门外的集结地,由梁锦棠黑着脸敲响了鸣金锣。
他们的春猎之行结束了,可他们的前路,仍长。
傅攸宁醒来时脑中有些发懵,抬眼打量四周,见房内陈设的样子像是范阳城内的官舍客馆,便稍在铺上赖了片刻,才缓缓坐起身来。
瞧见坐在窗下花几旁的梁锦棠时,她有些恍惚,觉着自己尚在梦中。
他斜斜靠在椅背上,闭目浅憩。也不知打从哪变出来一身干净齐整的衣袍,月白冰纨绮深衣迎着透窗而入的夕阳,已是一派俊逸清贵的模样。
春猎以来的许多画面与年少时的记忆在傅攸宁眼前交叠浮现。
她曾反复看着父亲的家书,假装自己有一个叫“齐光”的朋友。哪怕真正的傅攸宁是那样无能,那样软弱,时常狼狈,时常失败,他也从不嫌弃,从不远离。
她曾看过许多话本、著述,听过许多说书先生口中相似又略有不同的故事。与许多人一样,心中崇敬地致礼过,那个雪夜月下的玄铁银枪,千军万马前的单骑白甲,那个国境西门最耀眼的少年。
从前她无半点奢想,从未料到有朝一日,这两个身影会合二为一,穿过漫长时光,褪/去想象中少年的青/涩模样,不经意地,就来到眼前。
范阳春猎,与子同袍,并成败,共进退。有此一程,不虚此行,不枉此生。
这真是她所有想象中从未有过的,最好的后来。
傅攸宁无声轻笑,掀被就要下地,右掌却一阵钻心的疼,她咬牙皱脸,到底还是没发出声响。
许是她这细小的动静惊了窗前闭目小憩的人,梁锦棠倏地睁眼,满眸清明地直直看着她。
房内静谧无声,四目相对,双双无言,场面有些尴尬。
傅攸宁避开他的直视,垂眸假装镇定,笑道:“你……还真警觉。”她以为,自己的手脚已算放得很轻了。
梁锦棠随口嗯了一声,蹙眉看着她要下床,忍不住沉声道:“动什么动?回去躺好!”
平空一声喝斥吓得傅攸宁如惊弓之兔,立马缩回铺中,疾如闪电地将自己团成球。
见她仿佛吓到,梁锦棠正懊恼想着怎么找补,却见她一脸“咦我为什么要怕你”的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