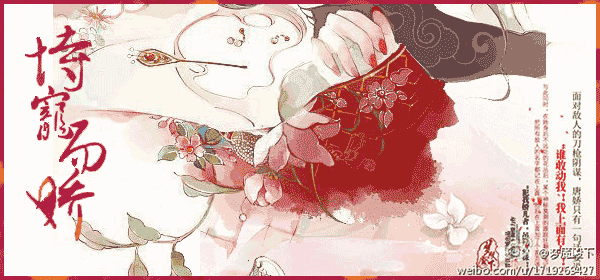好姑娘恃宠而娇-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两尊皆是出了名脾气不大好的瘟神,孟无忧生怕同时惊出他俩的起床气来,赶紧闭嘴,轻手轻脚地上去,自觉在他俩对面一侧的位置上坐好。
不多会儿,孟无忧见最后一个上来的人是傅攸宁,而马车内眼下仅余的一个空位正好在自己身旁,当即警觉地想起少卿大人的阴谋。
他略镇定了一下,鼓起勇气向对面的人道:“索大人,我能……同你换个位置么?”
索月萝睡得迷迷瞪瞪,眼皮都没抬一下,又冷又凶地应道:“不能!滚!”
此情此景,傅攸宁也是尴尬的。
以往孟无忧对她本就算不得友善,如今又加上傅靖遥无端作的那个梗……她是很乐意配合孟无忧的嫌弃,互相绕着走的啊!可鬼知道自己为何会跟他分在同一辆马车上啊!
孟无忧以抗拒无比的目光与她僵持半晌,正在即将妥协时,闭目养神的梁锦棠忽然开口:“我跟你换吧。”
孟无忧惊呆,回头想朝梁锦棠使眼色,却见他仍是闭目靠坐在那里,并未睁眼。
许是等了半晌没听见动静,梁锦棠忽然起身,不耐烦地一把将孟无忧扯过来,扔到自己先前坐的位置上,瞬间换到对座,继续闭目养神。
乍然被扔的孟无忧默默调整坐姿,自不敢反抗梁大人的决定,只心中暗暗含恨,誓言定将梁大人的名声捍卫到底,绝不让少卿大人知道,傅攸宁是坐在梁大人身旁去的范阳!
其实……孟大人你可以再坐过去,我坐索大人旁边就很完美的。
不知为何,直觉告诉傅攸宁,这句话还是别说的好。
于是硬着头皮上了马车,在梁锦棠身旁的空位坐下。
一路无话,孟无忧与索月萝几乎就渐渐睡实了。
傅攸宁本想保持清醒,可见整个车厢内就自己一个睁着眼的,这感觉太傻了,于是她也拢了外衫闭目小憩。谁知眼睛一合上,竟就当真困意袭来,昏昏欲睡。
四下沉静,只有马蹄踏过春泥的徐缓轻响。
梁锦棠缓缓睁开眼,眸如墨玉,澄澈清明。
不动声色地转头看过去,见傅攸宁安静地靠坐在自己身旁,那颗被困意主宰的脑袋钓鱼似的,略纤薄的身形随着马车的跃动轻晃,像是随时会倒过来。
梁锦棠收回视线,只觉自己整个右肩没来由地就僵住了。心道也罢,她要靠过来就靠过来吧,自己大人有大量,不骂她。
结果这家伙睡姿神奇,看着摇摇晃晃,却一直也没倒过来。梁锦棠心中轻嗤,兀自又闭目。
一车昏睡中,不知行至何处,像是车轮碾上了石块,马车忽地颠簸一下,半梦半醒的傅攸宁只觉自己差点被甩飞起来。
惊慌睁眼,正与梁锦棠四目相对。
见鬼了!有没有这么准啊刚好就甩到他怀里!
傅攸宁吓得想跳车。
赶紧红着脸坐正,尴尬低头又拢了拢自己的衣衫。好在梁锦棠没说什么,若无其事地又闭上了眼。
那头的孟无忧与索月萝也同时惨叫一声痛,各自捂住自己的头睁开眼。
许是没睡饱带来的起床气,加之又被撞了头,索月萝没好气地看了看孟无忧那一身金光闪闪的盔甲,张口头一句话就是:“孟无忧你有病吧,穿盔甲?!”
孟无忧揉着脑袋,困倦回嘴:“索大人,你几年没参加过春猎了,大概已经不记得那有多残忍。我对去年被打到躺着回家的经历,至今仍是记忆犹新呢。”
“你这盔甲,它还反光!到了山上你可离我远点,我不想陪你挨揍,”索月萝坐正,细细理平自己衣衫上的褶皱,没好气地瞪着孟无忧,“显眼成这鬼样子,八百里外都能瞧见你。”
她敢断言,这家伙的下场定是今年伤胜去年肿,年年大不同。
“用你说啊?我肯定离你远远的,我就跟着梁大人。”孟无忧一向不大敢与索月萝正面扛,最多就这样低声碎嘴两句。
他又笑得极其狗腿地看向对面的梁锦棠:“梁大人,河西军毕竟是你的故旧同袍,见你自该畏三分,总是得要手下留情的,对吧?”
梁锦棠根本懒得搭理他,睫毛都不动一下。
“就算河西军看在梁锦棠面上略为放水,你可别忘了,”索月萝毫不留情地戳穿孟无忧畅想中的美好明天,“还有北军呢。”
孟无忧瞬间被她这话噎住,如鲠在喉。
是啊,河西军凶猛,北军也不是省油的啊!
对面的傅攸宁却忽然笑着看向索月萝,小声说:“正因河西军是梁大人的故旧同袍,这回才更不会放水,倒会盯着梁大人往死里追,你信不信?”
这个说法让孟无忧倍觉魔性,又惊又恼地瞪大了眼睛:“凭什么?凭什么?你不要乱讲话!”不要吓我!
“因为,‘少年名将梁锦棠’是河西军的‘战神之魂’啊,故旧同袍若对他放水,那对他来说绝不叫尊敬。谁若敢明目张胆对他放水,说不得梁大人一火大起来,才不管什么春猎规则,直接拉出来打断狗腿。”傅攸宁笑得很愉悦,声音尽量轻轻的,不想吵到身旁打盹的人。
“所以啊,除非他们想被梁大人一掌拍死,否则只能盯死了他。对上梁锦棠这样的人物,只有全力以赴,他才会感受到你虔诚的敬重之心。”
孟无忧闻听此言,当即陷入深深的绝望与迷茫,缩在原地瑟瑟发抖。
索月萝见他一脸衰样,幸灾乐祸地低笑,又转头问傅攸宁:“你弩机带了吗?”
傅攸宁指指腰间用黑色布条细细裹住的弩机,轻声笑道:“带了。多谢索大人昨日提点,我连夜用木条削了没有箭头的弩/箭。”说着摸出一支来,请她帮忙鉴定是否符合规则。
“木的?怎不用竹子呢?”索月萝好奇地接箭形的细木条看看。
傅攸宁无奈苦笑:“一开始是做了几支竹/箭的,可我试了试,能伤人。”她都没好意思说,这弩机太猛,竹/箭扎进门板差不多有寸许,她自己都吓一跳。
索月萝笑着直摇头,感慨不已:“你这个人也真有意思啊。明明金玉其内,却总透着一股草台班子似的气息。”
傅攸宁那支弩机本是涂银的,许是怕夜里在山上银色打眼,她竟用黑色布条细细缠了起来。再看看旁边一身盔甲亮瞎人眼的蠢货孟无忧……
真是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
况且,看昨日她旗下人在演武场上的表现,说明她对下是有约束力的;她能立刻判断出河西军绝不会对梁锦棠放水,说明她有脑子,够冷静;连夜赶制竹/箭,竟还记得先试试,说明看重规则,做事也细致。
究竟是这家伙太能藏了?还是大家都眼瞎了?除了近攻不经打,以及遇事总畏人三分之外,这家伙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啊。
“你在说谁?”瑟瑟发抖的孟无忧不可思议地插嘴,瞪大眼看向索月萝。他隐隐有些忧心,索大人会不会是先前在自己的盔甲上将脑袋撞坏了。
索月萝并不搭理他,只朝满脸“啊?发生了什么事”的傅攸宁一径笑,两人便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起闲话。
傅攸宁此前从未参加过春猎,便向索月萝打听:“何时算开始呢?”
“等马车停住,咱们脚一沾地,就算开始。”索月萝苦笑。
人嫌狗憎的孟无忧持续瑟瑟发抖,间或插两句嘴。
谁也没注意到,傅攸宁身旁原本闭目养神的梁锦棠,唇角无声扬起。
原来,她懂他。
*******************
春猎规则是自行组队,也可单独行动。为保障公平,将官们组队不能超过五人,兵卒组队人数不限。但面对十打一的局面,相信今年应当无人敢托大落单。
黄昏时分,紧张了一路的孟无忧撩起车帘瞧瞧窗外:“快到了。”
一路闭眼不说话的梁锦棠终于开口,眼下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孟无忧,把你那愚蠢的盔甲剥下来,立刻。”
第二件事:
“各自带的东西都拿出来,清点物资。”
梁大人行伍出身,自然深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
第三件事:
“目标都清楚吗?”
索月萝与孟无忧齐声低应道:“穿过屏东山脉,于三月初五日落前,赶到范阳城外的集结地。”
傅攸宁只是跟着点头,半晌说不出句整话。
心跳得很快,不似毒发时那样紊乱无章,而是热血上涌的莫名豪情。那是她许多年未生出过的争胜之心。
能跟着赫赫威名的梁将军,冲破河西军与北军联手的围堵,站在范阳城头端起一碗庆功酒。这是她做梦都想要的光荣。
悄悄抬手按住藏在腰间暗袋里的小药瓶,她太向往这段征程了。
“卖呆呢?”
傅攸宁捂住额头,疑惑地看着梁锦棠:“为啥打我?”
“我那叫打啊?”梁锦棠瞪她。他只是敲了一下!
孟无忧幸灾乐祸地补刀:“在梁大人交代事情的时候发呆,没吐血的都不算被打。”
捂着额头的傅攸宁与同样不可思议的索月萝面面相觑,喃喃道:“贵羽林的日常,未免也过于……血雨腥风。”
不多会儿,车夫递进来四支信号焰火。
若自己的信号焰火被人拔掉引信燃起,就算被猎获了。
四人各自领一支后,梁锦棠开始布阵。“记清楚,若与‘猎手’正面相持,始终都是我主攻。你们两个,”他拿信号焰火隔空指了指孟无忧与索月萝,“护好各自的信号焰火,别被人按住了。在有余力的前提下,策应我,助攻。”
“你,”他忍不住又拿信号焰火去敲傅攸宁的头,这回她没走神,敏捷地闪过,“第一要务是找到最佳位置,藏好别露头。用弩机远程掩护,如有人试图趁乱拔掉我们三人的信号焰火,干掉他,同时示警。”
每个人的长项与短处皆被纳入考量,因此每个人被分派的走位都十分重要。
傅攸宁忽然明白梁锦棠为何至今仍是河西军的“战神之魂”。
因为在他手上,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也没有人会被放弃。
只要与他并肩共行,在他眼中即是同袍。
在他手底下没有谁是无用的,哪怕你并不是那么强,他也不会丢下。
这,正是她一直以来的,求而不得。
19。第十九章
春猎的马车队在屏东山脚下绵延十数里,待一辆辆马车渐次停稳,天色已近黄昏。
自车帘掀起,春猎的残酷便名不虚传地露出恶意森森的奸笑。
睡眼惺忪的猎物们刚踏出马车,就正正迎上第一份见面礼。
没有箭头的弓/箭自四面八方汹涌扑来,像漫天炸开的素木繁花。那些箭虽无铁簇/箭头,却有刻意削整出的棱角,全无半点放水的意思。
显然今年的“猎手”们并不安于温良恭谦、其乐融融的互动。
他们珞珞如英,靡坚不摧;他们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漫天箭啸声秉雷霆之势而下,涤荡着光禄府武官武将们在城墙之内因安逸祥和而渐趋麻木的心魂,立时激生出许多人久违的胜负之心。
屏东山下,日落黄昏。
漫天箭雨中逐渐现出一副副原本飒爽豪情的铮铮铁骨。
梁锦棠玄铁/枪开道,索月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