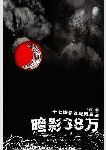影帝重回十八岁-第1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后,又有不少人再次钻进影院买票,准备看第二遍,或者第三遍。
而去的晚的人,根本连票都买不到了,只能期待明天全面上映。
经济发展、文化差异和家庭观念的不同,让华夏人看起来平淡,或者只能说不难看的电影,却让无数霓虹人感动。
其实霓虹国的亲情文化跟华夏相近,跟欧美相悖,但到了现在,无数年轻人享受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可当他们父母老了之后,又想要欧美那种疏远,不愿意承担赡养的责任。
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诩这是进步,是自由——你们为什么不能像欧美老人那样,老了不麻烦儿女,而是去旅游,去住养老院?
可他们根本没想过,钱都拿来支援你们了,哪儿来的钱去做这些?
因为很多人生活中这种情感缺失,未来越来越多的啃老族,这时候已经有了征兆。
而对老人的疏离,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那部大受欢迎的《江户物语》就有了深刻的揭露——
住在乡村的平山夫妇年龄大了,开始感到孤独,于是他们前往首都江户,探望已经成家立室的儿女。
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抵达后,却受到颇为冷淡的招待: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因生活的重压而相当忙碌,无暇招呼两老,因此建议他们去热海渡假,表面上是让他们有个松弛和游览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希望摆脱他们。
只有年轻守寡的儿媳纪子,对他们比较关怀和体贴。
但就在两老返回老家不久,儿女们便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于是他们回去探望病势危殆的母亲,但这时母亲已经无法辨认他们。
在葬礼之后,儿女们又匆匆忙忙地赶着回江户,只有儿媳纪子多留数天,陪伴暮年丧偶的公公。
纪子承认守寡对她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事,老人便劝她改嫁。然后,平山老先生孤独地守在屋里,渡过他将要孤苦伶仃的最后时光。
这部电影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触动,但人永远是善忘的,尤其是热点过去之后,一切照旧。或者说,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无暇顾及。
其实未来的华夏,也慢慢走上这条路,尤其是乡下,幼无所养的留守儿童、老无所依的孤独老人,而中生代,为了生活只能背井离乡,仅过年才能回去几天,而且即使这几天,也到处应酬聚会。
但现实也无能为力,留在老家的,也只有少数人有出路,就像那句话:“我搬起砖头没法抱你,放下砖头又没法养你。”
可能,这就是时代的阵痛。
而现在,霓虹国的人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这种亲情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那山那人那狗》才让他们感动,里面的父子情,村民和邮递员之间的融洽,都让他们羡慕。
第二天上午,宁远他们到机场接小说原作者彭建明,毕竟这次有签售会,电影宣传他露面也更好。
因为昨天他有事耽误,所以今天上午才一个人过来,而有东宝公司的提前交代,这次彭建明依然走的VIP通道,很顺利就见到了宁远他们。
这是在买版权后,宁远第二次见到他,倒是康健民,因为同是湘省人,跟他颇为熟络。
当时买版权的时候,别说康健民,连彭建明自己都觉得宁远出的价格太高了,尽管没谁嫌挣得钱少,但他是个老实人,对于那个价格还是感到不安。
因为宁远可是给了足足十万。
“83年,我第一次把这个中篇小说发表在《萌芽》上,稿费也就90块钱,而这已经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
听着彭建明的话,宁远点了点头,他记得后来看过报道,说莫言81年还在当兵的时候,写出他的出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在冀省保市的文学双月刊《莲池》,稿费只有72块钱。
彭建明继续道:“即使到了85年,我那时候已经有一定名气,湘省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山那人那狗》小说合集,尽管按照比较高的价格,每千字40元,但总计将近13万字的小说集,也才拿到五千块钱。”
彭建明笑道:“不过在那时候,可是一笔巨款,在单位都能引起轰动,身边人争相让我请客。”
康健民也笑道:“是啊,别说你那时候,98年我找你买下这个中篇小说的改编权,也才一万块钱。”
康健民之所以也这么说,就是提醒宁远这个价格高了。
毕竟宁远买的只是霓虹语的出版权,关键那时候国内的电影拷贝都没卖掉,更何况霓虹国的,前景未明,风险太大。
而宁远购买的版本,正是85年出版的小说合集,包括《那山那人那狗》在内总共六篇中篇小说,但宁远给出的价格,却比那时候翻了二十倍。
这些年的物价增速倒没有未来那么快,所以即使隔了十来年,这个价格依然很高,用彭建明的话说:
“这些钱,都够我在老家湘省岳市买一套房子了。”
正因为此,彭建明一开始还有些不安,要不是宁远是明星,又是康健民牵桥搭线,他都要怀疑是不是骗子了。
直到他们一起去银行,宁远把钱转进他的存折里,他还有些没太回过神。
接完彭建明后,宁远他们就被随行的车拉到东宝总部,参加正式举行的新片发布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在霓虹国,已经被翻译成《山の邮便配达》发行,再翻译回来,就是‘山的邮递员’,或者‘山区邮递员’。
“我宣布,山の邮便配达正式登陆各家院线,谢谢各位媒体。”
在松岗功宣布之后,中午12点,各家影院的售票窗口中,已经可以买到电影票了。
因为早就上映将近两个月,又被报道了这么长时间,还有发行的相关小说、小册子之类的周边,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观影期待。
而且前些天就报道过今天正式上映,所以中午很多人连午饭没吃,都跑到电影院了,只为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把电影看完——今天还是工作日。
而下午,因为工作的原因,人流量减少,但相较于其他影片,依然非常火爆。
这个时间,宁远和彭建明在讲谈社旗下书店进行签售,短短时间排队就超过百米,可见热度。
媒体也没有闲着,这一天,很多报纸的头版,都是相关新闻,而电视报道也更加密集起来,无数人就算没看过,但也早就知道这部电影。
而下午下班后,霓虹国的黄金周正式开始,晚上各家影院也都热闹起来。
第214章 发财了!
电影在霓虹国叫《山の邮便配达》,而出版的小说,也叫这个名字,不过下面还有副标题——彭建明小说合集。
整个书籍封面是用绿到黄的渐变色,朦胧中有戴着斗笠的父子两人影像,又像是水彩晕染出来的效果,挺漂亮的。
而在书的腰封上,则是电影的剧照——父子俩走过那座桥,上面印着显眼的“映画【山の邮便配达】原作”。
映画,在霓虹语里就是电影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和小说在华夏获奖的记录,比如金雉奖最佳影片、主演和配角,以及全国小说优秀奖的噱头。
说到腰封,宁远挺不喜欢这东西的,跟鸡肋没什么区别,而且跟黄金周一样,也是从霓虹国传到华夏的。
这本书定价1280霓虹币。
不过,跟电影票一样,霓虹国的书籍售卖时也都有折扣,从六折到八折不等。
而在宁远跟讲谈社签的合约,里面清楚写着:售价1280,报单价830。
按照这个价格,基本也就是六五折。
版税在霓虹国叫印税,当然并不是交税,而是出版社销售金额返给作者的部分,是作者的收益。
版税无论在哪里都是按销售册数计算,但在霓虹国,印税单价并不是售价,而是报单价,相当于华夏的建议零售价。
换算成华夏币,打完折一本59块钱,而宁远拿8%的版税,等于卖一本他就能赚4块7左右。
而在宁远他们来的时候,这本书第一次印刷的三万本已经卖完,现在卖的是第二次加印的五万本。
单单三万本的销售,就能给宁远带来14万的收益,当然,还得交13%左右的税。
关于这方面,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在跟彭建明购买版权的时候,宁远就了解过——
华夏的法规是,如果在国外交税超过国内,那在华夏就不需要另交,年底申报就行了,如果低于国内,那就还需要年底申报时补交差额。
而国内的稿税标准,超过四千基本都是11。2%的税率,霓虹国的明显高于国内,到时候也就不需要多补,但也让宁远不得不吐槽:果然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税都更高。
当然,霓虹国的书籍价格也更高,比如彭建明的那本小说集在国内的单本价格,才16块钱,跟霓虹国这边打完折的价格59比,三倍多的差距。
这么看的话,嗯,资本主义也挺香的。
现在那三万册的钱,已经被他们代扣税后,转进宁远来之前在华夏银行开的账户中,而华夏银行早在八十年代就在江户有分行,虽然跨境但是同行转账,手续费很低,讲谈社也没提这件事。
收入12万多,除掉买版权的费用,还有两万多的盈余,至于后续的版税,都是宁远的。
好开心啊,宁远拿到他们的汇款回执后,心里也跟现在的阳光一样灿烂。
想当年,这本小说集在霓虹国一年时间卖了将近二十万册。
而现在比当年更火,肯定只多不少。即使二十万册,扣掉买版权的十万和税,宁远也能挣超过七十万!
爆赚!
尽管宁远利用先机占了不少便宜,但放到当年,集英社——前世出版小说的出版社,他们给彭建明的价格肯定不如自己。
虽说宁远不清楚他们从彭建明手里买来的价格,但按照宁远之前跟讲谈社谈的合同时了解到的,霓虹国出版界对新人的买断价一般是千字一万,换算成华夏币就是七百出头。
但有一点,这是对霓虹国的新人,但商人逐利,虽然这个时间段的彭建明在华夏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但在华夏他也只是小众,并不是畅销作者,出版价格千字三百顶天了。
而到了霓虹国,彭建明依然是新人的范畴,没有丁点号召力,至于电影——那时候发行方在筹备中,谁也不清楚票房会爆,出版社更不可能给高价。
一个海外版权,别说三百,就算一百、二百,对彭建明来说都是意外之喜,而对于商人来说,能用两三百买断,干嘛要花七百?
这样一来,即使按照13万字算,也就是三四万块钱,否则当初宁远开口十万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彭建明给惊着了。
毕竟宁远是中间商,还得赚差价。
所以在当初,宁远也跟彭建明笑言:“如果电影在霓虹国大卖,带动小说集的销售,你可别说我占你便宜啊。”
本来就是白纸黑字的合约,买断霓虹语版权,即使彭建明再不忿也没用,所以宁远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就用这种口吻给他打个防疫针。
而彭建明则笑着摇头:“即使你卖再高我也不会眼红,你给的这价格已经高的超出我想象,就是担心你别亏了。”
下午的签售会,让彭建明惊了,虽然他也知道电影在霓虹国卖爆了,但依然一个劲儿的惊呼:“怎么这么多人?”
宁远笑而不语。
晚上结束的时候,彭建明连筷子都夹不住了,只能用勺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