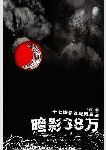影帝重回十八岁-第1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年的4月29天皇纪念日,因为是周六,所以在周五的28号补休。
而在5月5日的儿童节之后,6、7号两天又是周末。
也就是说,今年霓虹国的黄金周,将从补休的4月28日,持续到5月7日,足足十天的假期!
松岗功解释之后,又说道: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的话,经过两个月的上映,书籍也售卖了一个月,电影已经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介时在全国各地同步上映,恰逢放假,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影院,将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韩平当然没有异议,反而夸赞松岗功想的周到。
“那……排片方面呢?”韩平问出他最关心的问题。
松岗功笑道:“我们是商人,当然看重利益,而这部电影的商业价值已经在岩波影院得到验证,所以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其他院线上映时,排片率将不会低于15个点。”
说着,松岗功解释道:“因为处于黄金周,很多电影也都会选择这个时间上映,也希望你能理解,不过,一旦电影效果不错,后期还是会不断提升排片率的。”
韩平犹豫了一下,又说道:“可是,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这种强烈的竞争环境中,会不会起到反面的影响?”
松岗功笑道:“这就是我一开始把影片放在岩波影院放映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推迟到那个时间,也是把电影和作品集的影响发挥到更好的效果,那个时候,无数人都知道这部电影,肯定会来看的。”
韩平顿时恍然:“还是您想的周到,太感谢您了。”
“哈哈,一方面铃木忠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介绍宁远过来,我当然要帮助,而我看完电影后,也非常喜欢,于情于理都义不容辞。”
双方之间,在宁远的翻译下,沟通的非常愉快。
虽然之前有宁远跟他说过这个原因,但现在从松岗功这种大佬嘴里说出来,韩平当然明白,在这其中,宁远肯定费了不少的功夫,因此对宁远更感激了。
更让他感动的是,宁远做了这么多,却只要十个点。
结束通话后,韩平握着宁远的手:“谢谢,谢谢你宁远,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这段时间你辛苦了。”
如果宁远知道他的想法,心里肯定乐坏了——哪费什么功夫呀,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话剧被铃木忠志喜欢,然后见到了松岗功,而电影又被松岗功喜欢,就有了这些。
说到底,还是一切靠作品。
当然,宁远在其中辛苦肯定有,但并没有韩平想的那么费劲,不过宁远肯定不会傻乎乎的去解释那么多。
回到学校后,宁远就恢复了往日的低调,平时上课,周末继续出演话剧。
但就在这个时候,四月中旬,电影在霓虹国持续高涨的人气,以及相关报道,终于引起华夏媒体的注意。
在他们了解后,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卧车?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一部在华夏,到现在票房才几百万的电影,在霓虹国卖了上亿?
毕竟从宁远他们结束宣传后,电影票房慢慢回落,到现在还没超过八百万。
而在霓虹国,已经一亿多的票房!
就算换算成华夏币,也将近千万的票房了,比国内还多,关键国内可是上百家影院,而在霓虹国,只有一家电影院!
一时间,报道层出不穷,再次让这部电影在华夏火了起来。
第210章 文艺之路!
电影好不好,就看票房是否卖得高。
这是普通大众最直观的感觉,尽管很多票房大卖的片子被无数圈内人抨击没营养、没内涵、没意义的三无产品,但他们的话,没人听、没人信,也没人在意。
文艺片为什么称为小众,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些圈内人自嗨,顶多再加一些喜欢文艺片的观众。
其实宁远觉得,文艺片并不小众,只是被那些妄图高人一等的高级人,生生扭曲成了小众。
好的文艺片,雅俗共赏,就像白居易的诗,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妪也能听得懂,就算是王勃那篇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的《滕王阁序》,就算辨别不出里面层出不穷的典故,但如果听人朗诵,大气磅礴的感觉也会油然而生。
可那些人,偏偏把文艺片整得谁都看不懂,还沾沾自喜:“我这是高级!”
高级你妹!
用一些没有必要的滤镜,美名其曰增加质感,把叙事节奏剪辑得颠三倒四,自诩为超时空,看不懂是你境界不够。
至于电影本身的问题,就更多了,因为张义谋一部《活着》拿下戛纳评审团大奖,很多人也故意去拍这种惨绝人寰的电影,还自夸这是揭示人性,剖析命运。
因为《我的父亲母亲》拿了奖,又是一帮人,一窝蜂的去拍农村题材的电影,脏破乱就不说了,狗血混乱的人际关系,复杂到你怀疑人生。
而后《花样年华》拿了奖,又一帮人只学了个空虚和缥缈的皮毛,《春光乍泄》拿了奖,又去拍这种前卫和颠覆。
其实就是跟风,绝大部分动机和目的,只是为了拿奖——尽管张义谋他们也有拿奖的目的,至少他们也在讲故事:先讲好故事再有文艺。
而这些人,恰恰本末倒置,先搞文艺,再讲故事,实际上影片讲了什么,他们自己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只牵强附会一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就像鲁迅的文章被过分解读一样。
完全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到最后把文艺片作死了。
可实际上,好的文艺片无论叙事还是节奏或者风格,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就算是剧情,也完整而统一。
看着影片灰暗基调,你也用这个调调,但你并不明白人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这个调调,反正管他三七二十一,打开摄像机就是干。
艺术圈也差不多,写实之外的其他画派,除了几个大师的作品,其他大部分都是沽名钓誉和炒作。
梵高的《星空》,如果单看印刷品,当然觉得就那回事,但如果能看到真迹,那油彩的笔触、斑斓的色块堆叠,视觉冲击力极强,就像《滕王阁序》,很多人也说不出他哪儿好,又引用了哪些经典,但听着、读着就是特别带感,有种喝了好酒的酣畅淋漓。
好的文艺片,是有故事主线的,而不是乱七八糟,就像《霸王别姬》、《花样年华》,以及汤姆的《阿甘正传》,霓虹国的《京都物语》等等。
好的文艺片,主人公的苦难是有揭示和启发意义的,再不济也是在抨击一些事物,而不是为了苦难而苦难。
追逐奖项不是什么坏事,但东施效颦,还讥讽嘲笑说他不好的人都是看不懂,那就是盲目,是掩耳盗铃:“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要再念经!”
跟文艺片的追逐奖项类似,未来一窝蜂的拍青春片,就是逐利了。
未来,大众将文艺片狭隘的定义为票房低、明星少、制作粗糙、节奏沉闷,专供海外电影节,这样的“固有印象”,让大众和文艺片渐行渐远。
但怪谁呢?
肯定不怪观众,更不可能怪他们看不懂。
八十年代末,胜利艺术电影院独家上映《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不是廖帆那部,那时的观影盛况,跟未来人们对文艺片的印象大相径庭。
影院443个座位连续3个月常常爆满,到最后售票处不得不拉起铁栅栏分流观众。
就算是未来,刘杰执导、11年上映的《碧罗雪山》,这部最初压根儿没准备公映的电影,在京城新建的MOMA艺术中心放映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且往往一票难求。
而且跟《那山那人那狗》相似的是,它也只在这一家影院放映,评价也差不多——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刻意夸张的表演,用非常朴素的手法,以冷静、凝练的镜头,记录下青山绿水间发生的故事。
因为这部电影对白几乎都是傈僳语,即使是一部华夏电影,但观众也只能看字幕,这跟宁远他们的电影在霓虹国上映也差不多。
连这种方式都有如此盛况,可见好的文艺片,永远都不缺观众。
所以,每当导演和制片方票房扑街,把锅甩给文艺片,说自己怎么怎么理念高深,观众没看懂的时候,以后他们的电影也不用看了。
这也就导致了,未来即使是文艺片的作品,宣发时也不敢把自己的影片归为这一类。
《白日焰火》——这次是廖帆演的,似乎这家伙跟焰火杠上了。
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是一个标准的文艺片。但在德国参评回国后,却主打廖帆+桂纶美明星主演、柏林金熊大奖加持。将电影跟“文艺片”划清界限,作为一部犯罪类型片来宣发。
直到票房破亿后,片方才改口称自己是文艺片。
在学校,以及在话剧院,宁远不止一次跟秦莉,跟孟辉和廖帆他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尤其是跟廖帆他们喝了酒之后,都破口大骂那些混蛋砸了文艺片的招牌!
秦莉在为宁远挡了很多采访后,给宁远批假的时候说道: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希望你以后能给文艺片正名,让观众知道不仅有内涵,还可以卖钱。”
“卖钱?哈哈,老师你啥时候也开始俗了,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大俗即大雅,不要担心好片子普罗大众看不懂,如果有问题,那也只能是学艺不精——好了,去吧,到了那边注意安全,也注意自身言行,因为你不仅仅代表自己,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
“谢谢老师。”
第211章 场面火爆!
华夏五一才放假,但霓虹国那边其他院线4月28就正式上映,所以宁远他们27号就得过去,自然需要请四天假——
尽管29、30两天是周末,但华夏五一只有三天假,周末挪到下周,这两天依然得补课。而霓虹国就不一样了,因为29号的天皇纪念日是周六,所以28号得补假。
而此时,关于《那山那人那狗》的国内报道,已经铺天盖地换上了新的标题——《宁远主演电影国内外双双走红,总票房破两千万势头不减》!
一时间,宁远炙手可热,想要来采访他的媒体络绎不绝,但都被秦莉和曹如龙挡走了。
按他们的说法:“你现在名气已经远超同龄人,过度、过早的大量曝光不是什么好事,只要安安心心把基本功夯扎实,以后的机会非常多。”
宁远深以为然,所以,即使外面再热火朝天,宁远依旧该干嘛干嘛,倒是学校里的很多师姐,经常下了课就喜欢来看宁远,撩骚的也不少,让王宇羡慕不已。
宁远也挺善良的,老拒绝也不好意思,最后他直接挂冷脸,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
慢慢的,也不知道怎么传的,就出来众多版本,比如性格冷漠、成名后就傲了、耍大牌……
这也就算了,最后还冒出来“宁远不喜欢女同学”的传闻,让宁远听了后,气得想打人!
而关于影片在国内其他院线的上映,也被提上日程。
当然,这就需要他们跟北方和太平洋来协商了,倒没有太多的问题,只要拿钱就行,毕竟这两家院线也只是区域性的,没有覆盖全国,有钱不赚是傻子。
但这个时候,正是观众期待值最高的时候,妥妥的爆赚,别说拿钱,只要不是太夸张,几百万都敢竞价。
27号一大早,宁远就跟韩平他们一起,登上了前往霓虹国的飞机。
也在这一天,其他几家院线拿下了放映权。
虽然这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