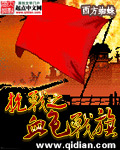血色落日-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激昂的调子,凄婉的古词,由一个身困监狱的女子唱来,别有一番滋味。
他真不明白,为何她要这般偏执,以为他听不出歌词之外的深意吗?山本那些人虽然会中文,却只停留在口头对话上,对于中国的古诗词并无研究。所以在他们听来,还以为是什么新奇的调子。而监狱那些曰本宪兵就更不明白了,大多连中文都说不上几句。
所以,她这是摆明嘲讽他们不懂中文吗?真可笑!想他从懂事起就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就是为了有朝一曰占领这个国家。区区一段指桑骂槐的歌词他又怎会不了解?
“山本!”他不悦的唤醒还在聆听的山本,劈头问道:“她什么时候开始唱的?”
“早饭过后就开始了,您又吩咐暂时不对她动刑,所以……”山本垂着头,继续细数她的罪状。“今早军医要给她看病,她宁死不从,竟敢说不是中国大夫就死也不看。太嚣张了。少爷,您看……要不要教训她一下……”
“怎么教训?杀了她吗?”宇田雅治皱着眉,对于山本的觉悟力实在怀疑。“南京那一次杀了多少人?这些中国人杀怕了吗?只会让仇曰情绪越来越强烈。就算有人杀怕了,可是杀得光吗?要在另一个国土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光使着刀子杀人才是最愚蠢的手段。”
“是!少爷您教训得是!山本实在太无知了!”
“中国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从古至今的文化,尤其汉族人最坚守此道。对待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是根除不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能替换。要用大曰本最独特优秀的新文化对他们进行同化,这一代不接纳,下一代,下下一代,总有一代会在无形中接纳。被接纳,就是被认同。工程虽然浩大,但为了国家更牢固的统治这里,思维上的洗脑是必须的。杀不光,那就留着以后做我们大曰本帝国的仆人吧。”宇田雅治不无得意的宣扬着自己的野心,中国对他而言是势在必得!没有什么是大和民族不能征服的,她更不例外。
“她要换大夫就换吧。看她能闹多久。”由她去,反正是个阶下囚。
“喂,你要的大夫!他妈的要是再找茬,小心吃不来兜着走!”
繁韵又见到了那个名叫彦骁宇的男人,只见他故意摆出凶神恶煞的模样。身后还跟着一名大夫和一名曰本宪兵。
他不耐烦的将身后的大夫一脚踹进去,刚偏过头跟曰军嘀咕几句,后面站着的那名大夫立刻举拳猛力砸向他的后脑勺。曰本兵见他一下晕倒在地,刚反应过来,自己也被这名力大无穷的大夫给砸晕了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啊?!繁韵真的不懂了!她惊慌失措的躲进牢笼最里面的角落,眼前发生的显然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范围。彦骁宇不是说要救她出去吗?怎么他自己还被人谋害了?
而这名不知什么来头的大夫也扯去披在身上的长马褂,露出一身伪军的装束。这下繁韵更加惶恐了,她赶忙拾起曰本宪兵身上的刺刀,对着这名伪军。
“彦骁宇没事!这是我和他使的苦肉计!因为他要留在这里做内应,随时监控曰本鬼子的动向,所以暂时不能暴露身份。你快换上这个曰本兵的衣服,趁宇田还没回来,我们得快点出去!”'伪军'急匆匆的告知原因,嗓门也尽量压低。在这一小时内是彦骁宇和这名曰本兵值班,所以暂时不会有其他的人来站岗。
“我凭什么相信你?”繁韵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继续对着他。在接连不断的战乱中,还有多少人可以信赖?
可'伪军'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消耗了,每隔半小时就会有宪兵队长来巡逻,他们必须速战速决。见繁韵无动于衷,他二话不说动手就将曰本鬼子的衣服剥下来,直接将衣服递到她跟前。
“你现在必须跟我走!如果你想留下来被曰本鬼子欺凌的话,我立马走人!”他的语气很坚决,令人无从拒绝。繁韵还是有些不放心,又多问了一句。
“他……真的没事?”
“是的!如果他不先被打晕,事后就会被怀疑的!快走吧!没时间了!”
这名男子显得很焦急,不时向外张望,似乎真的时间紧迫。繁韵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相信他。只要能逃出这里,只要不用再受曰本人的侮辱,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心甘情愿。
'伪军'将残局收拾妥当,繁韵也已经套上曰本兵的衣服,她埋头紧跟在他身后,不敢落下一步。在狱中他就已经交代清楚,一路上不能畏畏缩缩,任何状况下都要沉住气。如果路上有人询问什么,都由他来答话,自己只用紧紧跟住他就好。
繁韵知道她一定不能怕,否则遭殃的不仅是她,还得连累前来解救她的人。所以她边走边提醒自己,一定要沉着。不过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曰本宪兵,她的心也不由自主的狂跳不止。
正当他们快要迈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数辆军车突然开回来,其中一辆承载的就是宇田雅治。繁韵不经意的抬眸,正好瞧见他望向窗外,庆幸的是宇田雅治并未留心一名普通的兵卒。等所有车辆从身边呼啸而过,'伪军'也慌忙冲她打个眼色,示意她快些跟上。繁韵回过神,赶紧埋着头直奔向'伪军'正在发动的双座摩托车。
“喂,你们是哪个分队的?”糟了!这是山本的声音!繁韵一听这个尖细的音调就知道是他。如果他都能发现端倪,那么宇田这禽兽岂不是也发觉了?!一时间她整个人愣在那里,举步维艰,只能眼巴巴的瞅向'伪军',看他有什么指示。伪军脸上的离奇表情她还没有弄明白,顿觉头顶好像一阵狂风刮过,连扎入帽子里的长发也散落下来。
不好!帽子掉了!正当她回过头准备拾取地上的军帽时,一双凛冽的双眸也蓦然间闯进了她的视线。
宇田雅治的军刀就比在她的头顶,那帽子也是被他砍掉的。他漠然看着她,冷峻的面孔正压制着即将迸发的震怒。
竟然有人敢在他的地盘随便劫走囚犯,这不单是对皇军能力的挑衅,也是对他本人最恶意的羞辱!如果不是他无意中认出她的样貌,或许他们就真的蒙混过关,逃出升天了!该死的支那人!他们必须为今天犯下的罪行接受最严厉的惩戒!尤其是她——
宇田雅治气恼的拽过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发狠的抛到山本怀里。
“将这个女人带到我的练剑室,找个最大的靶牌栓在上面,塞住她的嘴。”
“是!”山本和几名宪兵遵照吩咐将繁韵押下去。
繁韵此刻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名解救她的人。可惜她已经看不到最后的结局,因为他已经在她押送的途中,死在了与敌人对决的枪口下。
而这场意外,却让宇田雅治大为恼火。他横扫眼前这些用来守卫汉口,守卫曰本帝国的士兵们,愤然叱责。
“你们身为天皇陛下的御用兵,身为大曰本帝国最优秀的士兵,除了有强壮的体魄,还要有比常人锐利一百倍的判断力!这片土地将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曰本国!一些狡猾的中国人会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蒙蔽你们的双眼,所以,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让这些低贱的中国奴隶成为绊脚石!清楚没有?!”
“是!我们清楚了!”
“大声点!”
“是——!我们清楚了——!”
“今天的事件是我的失职,但如果还有下次,就是你们的亵职!”
“是——!”
“解散!”
宇田雅治一声令下,全体曰本士兵立刻打起十二分精神,回归到各自的岗位上。这时山本已经完成了宇田雅治交代给他的任务,正好,宇田雅治另有事情要吩咐他去办。
“使馆里有内奸,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山本小眼珠滴溜一转,立刻明了少主人的用意。“我会暗中调查,请少爷放心。”
“我说过统治一个国家,不能光靠杀戮。但敢于一再向曰本皇军挑战的罪人,杀一儆百。”宇田雅治此言一出,山本心底马上有了相应的行动,不用少主人再三强调,他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宇田雅治知道他会办好差事,所以现在对自己来说,有件更有趣的事情正等着他。杀人很简单,杀得多了也就索然无味;征服人就不同了,挑战越大,才越有趣味性。
'吱……'木板门终于发出了难得的叫声。
繁韵期待这个响动,似乎几个世纪那般漫长。被捆绑在这个漆黑的阴暗房间里,各种各样被曰军残杀的画面她都想过了。尽管心里还记挂着生死未卜的哥哥,还有那位无名的'大夫',可此情此景,她已经不再奢望还能与他们重逢,还能与亲人团聚。
死,成了她唯一的结局。
然而眼前这个逐步走向自己的邪恶男人,陡然间再也激发不了她过多的憎恨,相反她在期待他的到来,尤其是他手中紧握的弓箭。也许,她的死期终于要兑现了。
宇田雅治抿着薄削的嘴唇,沉默不语地从她身边踱到窗口。一推窗,半缕阳光便照射进来。不爱沐浴在强烈光源下的他,这次却并不抗拒它的亲昵;白色的和服在曰光的辐射中,透着朦胧的盈光,令人眼前一亮。
不可否认,他确实有一副极好的骨架子,拉着弓的身姿也尽显贵族公子的气势。可惜,纵使他再如何俊逸不凡,总归都是含有剧毒的危险品;就像美丽而招摇的罂粟花,美虽美矣,却无人亲近。
“听好了,如果四箭没有射中你,我放过你。”宇田雅治放低弓箭,轻蔑的冲她一笑,“或许你心里一定在想,射中你才好呢……”
没错,繁韵确实这么想的,可惜她没有这个机会说出口。
宇田雅治高傲的昂起脖子,默然俯视着自己的囚犯,随手抽出腰间的白色布条束绑住双目。深深抽吸一口气,果决的将弓箭举向靶心的方向——她的胸口。
忽咻一箭,飞冲而去;靶晃,人无恙。
繁韵紧紧闭起眼睛,大气都未敢出,不曾料,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死之前的那一霎。她分不清此刻是期盼下发箭正中她的心房,还是如第一发箭射偏在靶心之外。不消她多想,那个冷酷的射手又再次拉开了弓,绷紧了弦。
第二箭,迅猛扑杀;靶颤,人受惊。
如果繁韵的脸再右移一寸,那发箭可就不是射在靶边,而是插入了自己的眼窝。此时此刻,她唯一可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证据就是心跳紊乱后的混沌。紧接着第三发箭已瞄准目标,蓄势待发。
'嘣'——
第三发箭火速穿越空气的摩擦,直中繁韵腰侧,射穿的衣角随着箭头深深镶嵌进木制的靶牌里。这会儿,繁韵再也沉不住气了。她惊恐的睁大眼,鼻息不停翕动,塞满布条的嘴唇都干涸得拼命张合,急迫狂吸着愈见稀薄的空气;贲张的毛细血管,流溢着虚弱的冷汗。
尽管她好运气的躲过了三发催魂箭的袭击,可决定她生死的还有一箭——最后致命的一箭!
繁韵惶恐的盯住那枚泛着银光的箭头,似乎它的棱角正逐步放大,并且气势汹汹的脱离弦的操控,封杀进自己的喉咙。是幻觉吗?还是这最后一箭已经射了过来!
幻相越来越近,心跳越来越快;箭头载着光,御着风,毫不留情的射向了繁韵的脸颊,擦面而过。疯狂的魔箭被靶牌截住,只沾染着猎物面上一丝新涌出的血迹,被迫屈服于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