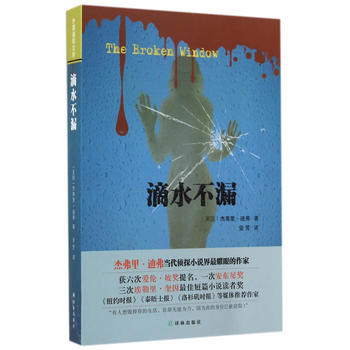滴水不漏-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修长苗条,戴着隐形牙套,绒线衫和大喇叭牛仔裤包裹着她那迷人的身材。她的笑容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性感诱人。很快他们就开始约会了。两人都是初涉爱河。他们参加彼此的运动会,去参观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索恩画室,去古城的爵士乐俱乐部,有时会到她的雪佛兰蒙扎的后座上缠绵,其实已经算不上后座了,却也正合二人心意。以田径赛的标准,从他家小跑一段就能到阿德里安娜的家,但是跑步是绝对不行的,不能大汗淋漓地出现在她面前。所以他只要能借到家里的车,就开过去见她。
他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就像和亨利伯伯相处时一样,他和阿德里安娜针锋相对。
障碍还是有的。他第二年就要去波士顿上大学,她则要去圣地亚哥学习生物学,到动物园工作。这些不过是节外生枝而已,但是莱姆从不把节外生枝作为借口,那时如此,现在依旧。
后来,在那次事故之后,在他和布莱恩离婚之后,莱姆常常会想,假如他和阿德里安娜在一起,将爱情进行到底的话,会有怎样的故事。其实那个平安夜,林肯差一点就求婚了。他考虑着送给她“一个与众不同的石块”(这句话他清晰地背诵过)而不是一枚戒指。那是在他伯伯举办的科学小竞赛上得来的奖品。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他还是放弃了。他们在一条长椅上相拥而坐时,雪花开始从中西部寂静的夜空争先恐后地飘落下来。几分钟后,他们的头发和大衣上就落了一层湿漉漉的白雪。趁冰雪还没有把路封上,他们就各自回家了。是夜,他躺在床上,装着水泥块的塑料盒放在身边,他还在演练求婚台词。
但是从未说出口。意外事件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各奔东西。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微小得一如在寒冷的体育馆被诱发裂变的、看不见的原子,但却永远地改变了世界。
一切将会不同……
这时,莱姆无意中看到萨克斯在梳理她红色的长发。他注视了她片刻,很高兴今晚她留下来过夜,比平时还要高兴。莱姆和萨克斯并非难舍难分。他们都是极其独立的人,往往更愿意独处。但是今晚他想让她留下。喜欢她的身体紧贴着他的,正因为很少肌肤相亲,这种感觉才更加强烈——他的身体有几个地方尚有知觉。
他每天坚持在计算机控制的踏车和电疗脚踏车上锻炼。他对她的爱是激励他锻炼养生的动力之一。如果医学能创造奇迹,能让他走路,他的肌肉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时机成熟,他还在考虑接受一种新的手术来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即改变末梢神经的路线。该手术是实验性的,而且引起了争议。曾经有人谈起过,偶尔也尝试过,但是几年过去了,术后有积极效果的例子不多。但是近来国外的医生一直在做这种手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尽管美国的医学界对此持保留态度。其操作过程是把受伤位置上方的神经和下方的神经通过外科手术连接起来,相当于避开被洪水冲蚀的桥梁,绕道而行。
大部分手术成功者身体上所受的伤害都比莱姆的要轻些,但是效果是显著的。膀胱能自控了,四肢能活动了,甚至会走路了。虽然以莱姆的病情,术后他也不能走路。但是他和一位日本的医生谈论过,这名医生是该手术的先驱者,也和一位在常春藤大学教授医疗的同事谈起过,他们说可能会得到改善。手臂、双手和膀胱可能会有感觉,也会活动。
也能唤起性欲。
瘫痪的人,哪怕是四肢麻痹的人,也完全能够做爱。如果刺激因素是心理上的,比如被一个男人或女人所吸引,这时,不,该信息不会穿过被损坏的脊髓。但是人体是一个卓越非凡的系统,在创伤之下,有一个神奇的神经体系在独立运行。只要有一点局部的刺激,哪怕是伤残得再重的人,也能经常做爱。
浴室的灯啪嗒一声灭了,他看着她爬上床,身体的轮廓和他的融为一体。她很久以前说过这是全世界最舒适的一张床。
“我——”他刚一开口,立刻就被她热烈的吻堵上了,声音变得含糊不清。
“你说什么?”她低语着,嘴唇移到他的下巴上,又滑到他的脖颈上。
他已经忘了,就说:“我忘了。”
她又开始吻他,他也热烈地回应她。
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啊啊。”她小声说,“我没听见。”手机铃响了四遍后,可敬的语音邮件接管了任务。但是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起来。
“可能是你母亲。”莱姆提醒道。
罗斯·萨克斯的心脏有问题,正在接受治疗。预后良好,但是最近又有了反复。
她嘟囔着开了灯,两个人的身体都沐浴在蓝色的光晕里。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说:“是帕米。我最好接电话。”
“当然。”
“嘿,是我。怎么啦?”
从她们一对一的谈话中,莱姆推断出了事。
“好的,当然可以。但是我在林肯这儿。你想过来吗?”她扫了一眼莱姆,莱姆点头同意。“好,亲爱的。我们不会睡着的,没问题。”她啪地关上手机。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她不愿意讲,只是说丹和伊妮德今天晚上要紧急加班,所以大点的孩子都要睡一个屋。她想出去,又不想独自住我那儿。”
“我不介意,这你知道。”
萨克斯躺下来,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她悄悄地说:“我刚才计算了一下。她要打个包,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赶到这里足足要花45分钟。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她凑上前去,又开始吻他。
就在这时,刺耳的门铃声响了,内部对讲机里传来嘈杂的声音:“莱姆先生?艾米莉亚?嘿,我是帕米。能打个电话让我进来吗?”
莱姆笑了,“或许她就是在门前的台阶上打的。”
帕米和萨克斯坐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只有她们俩。
这间卧室随时欢迎这个女孩入住。隔板上放着一两个制成标本的小动物,无人理睬(假如你的父母是从联邦调查局跑出来的,那么玩具在你的童年时就不那么重要)。但是她有几百本书和CD。多亏了托马斯,衣柜里总是有干净的运动衫、T恤和袜子,足够换洗。有一台天狼星卫星收音机,一台唱片机,还有她的跑鞋。帕米喜欢沿着环绕中央公园水库的1。6英里人行道快跑。她跑步是出于对跑步的热爱和内心的渴望。
现在这个女孩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用棉花球蘸着指甲油,把她的脚指甲涂成金色,她母亲不准她涂指甲,也不准她化妆(“出于对上帝的尊重”,也不管这话到底有没有用)。她一从右翼地下组织脱离出来,就开始对自己略加修饰,看上去让人很舒服。比如涂指甲油,头发挑染成淡红色,穿三枚耳钉。看到她没有走极端,萨克斯放了心。没有谁比帕梅拉·威洛比更有理由走荒诞怪异的路线。
萨克斯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双脚朝上,脚指甲上什么都没有涂。一阵微风吹进小屋,带来了春天的中央公园里混杂的气息:覆盖层、泥土、被露水打湿的树叶和汽车尾气。她啜了一口热巧克力说:“哎唷,先吹一吹。”
帕米对着杯子吹吹气,喝了一口说:“好喝。嗯,很热。”她继续涂指甲。和今天早些时候的脸色相比,此时这个女孩显得困惑不安。
“你知道它们叫什么吗?”萨克斯指着问。
“脚?脚趾?”
“不,是底下。”
“知道了,是脚底下和脚趾底下。”她俩都笑了起来。
“是足底。它们也有印记,和指纹一样。曾经有个凶手用光脚丫子把一个人踢昏了,但是有一次他没踢中,一脚踹到了门上,留下了足印。林肯由此断定他有罪。”
“真厉害。他应该再写一本书。”
“我在敦促他写。”萨克斯说,“你最近怎么样?”
“斯图尔特。”
“往下说。”
“也许我不该来。我太傻了。”
“说吧。别忘了我是警察,我会帮你摆平的。”
“就是,我的同学埃米莉打来了电话,星期天接到她的电话很奇怪,她从来没在星期天打过。我就想,好嘛,出事儿了。刚开始她好像不愿意说,后来还是说了。她说她看见斯图尔特和学校里的另一个女孩在一起。在足球比赛结束后。可是他对我说的是他直接回家了。”
“那么,有事实依据吗?他们只是在说话?那也没什么不对。”
“她说她也不确定,但是看上去他好像搂着她。他一看到有人看他,就匆匆地和她走掉了。像要躲起来。”涂脚指甲的工程进行了一半就停止了,“我真的很喜欢他。要是他不想见我,我会难受死的。”
萨克斯和帕米曾经一起去看过一名法律顾问。征得帕米的同意后,萨克斯单独和她谈过话。帕米将会遭受长期的创伤后精神压力,不仅是因为长期受到反社会的父母的控制,还因为曾有一度,她的继父险些牺牲她的生命企图谋杀警察。和斯图尔特生出的这些枝节,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但是在这个女孩的心中却被放大了,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顾问告诫萨克斯既不能增加她的忧虑,也不能对此轻描淡写,而要仔细考虑每一种忧虑的情绪,试着去分析它。
“你们俩有没有说过和其他人约会?”
“他说……这个嘛,一个月前他说他只和我约会。我也没有和别人约会。我跟他说过。”
“还有其他情报吗?”萨克斯问。
“情报?”
“我是说,别的朋友还说过什么吗?”
“没有。”
“你认识他的朋友吗?”
“算是认识吧。但是不会因为这件事去问他们什么。那就太没劲了。”
萨克斯微笑着说:“这么说暗中侦查没用了。那好,你就去问他好了。直截了当。”
“你觉得这样好?”
“对。”
“假如他说他是在和她约会呢?”
“那你应该感谢他对你很坦诚。这是个好兆头。然后你就说服他甩了那个荡妇。”她俩笑了起来,“你就说你只想和一个人约会。”一股母性的力量油然而生,萨克斯立刻补充道,“我们不是要谈婚论嫁,也不是要同居,只是约会。”
帕米立刻点点头,“哦,当然。”
萨克斯松了一口气,接着说:“而且他是你唯一想约会的人。但是你希望他和你的想法一样。你们之间出现了问题,那就相互说出来。你们可以好好谈的,你们俩心有灵犀,只是你没怎么看出来。”
“就像你和莱姆一样。”
“对,和我们一样。但是如果他不愿意,那就算了。”
“不,不行。”帕米皱起眉头。
“不,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说。另外,告诉他你也会和别的男孩子约会。他不能占两头。”
“我也这么想。可他要是说可以呢?”一想到这个,她的脸色就黯淡下来。
萨克斯笑着摇摇头,“对,他要是学你的样,也虚张声势,那就完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会。”
“好吧。我明天下了课就去找他。我会跟他谈一谈。”
“给我打个电话说一声。”萨克斯站起身,拿起指甲油,盖上盖子,“睡一觉吧。不早了。”
“可是我的脚指甲,我还没涂完呢。”
“别穿露脚趾的鞋子。”
“艾米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