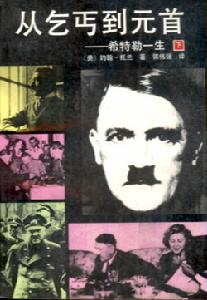从乞丐到元首上-第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娘“为犹太人弗兰肯伯格工作时生下了一个儿子。19世纪30年代末,弗兰肯伯格代表他
19岁的儿子给姓施克尔格鲁勃的女人的儿子支付了一笔从生日起至14岁止的‘父道津贴
费’”。弗兰肯伯格与厨娘(希特勒的祖母)还长期通信,“通信中谈的大致是,当事人心
里都明白,施克尔格鲁勃怀这个孩子的时间、地点,使弗兰肯伯格不能不付出这笔津贴。”
弗兰克的报告得出了遗憾的结论:希特勒的父亲是半犹太人的可能性无法排除。
元首激烈地对弗兰克的推论提出了挑战。他狼狈地解释说,他祖父贫困不堪,伪称弗兰
肯伯格有父道之嫌,成功地敲诈了一笔津贴。希特勒发誓,这情况是他父亲和祖母亲口告诉
他的。弗兰克的证据肯定使希特勒胆战心惊,否则,他怎会撒出这个弥天大谎来:他出生时
他祖母已去世40年。更重要的是,他承认祖母确曾收过犹太人的钱,这样一来,他的血统
不纯便大大有可能了。阿道夫·希特勒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机会是极小的。格拉茨大学的尼古
拉·普里拉多维奇所作的研究对弗兰克的证据提出了某些怀疑。在格拉茨(奥地利)的犹太
人会员登记册中,他未找到有弗兰肯伯格或弗兰肯雷德的记载。这些登记册由1856年,
即希特勒的父亲出生后19年开始记载。但,那是因为犹太人于1496年被逐出斯苔尔马
克,于1856年才获准返回该地之故。据普里拉多维奇说,在此之前,格拉茨“无一犹太
人”。重要的是,他自己生怕有犹太血统;为了确信,他此后曾至少调查了两次。据从19
17年起便认识希特勒的内科医生舒赫回忆,他“一生都在痛苦地怀疑:他有还是没有犹太
血统?他常与我们谈及此事。”希特勒要求别人拿出雅利安人的证明文件来,而自己却拿不
出。这便可说明他为何要对威廉·帕特里克说:“切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是什
么家庭出身。”
尽管私事如此烦恼,希特勒1931年的预兆是好的。他一夜之间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作
者。自出版以来,《我的奋斗》年销量不过6,000余本,到了前一年,销量猛增至54
,086本。这给他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似乎未有尽期。另外,党的新总部“褐色大
厦”又于新年的第一天开放。这座用特种捐款、希特勒集会的收入、赠款及党费购买和装修
的大厦,代表了纳粹党的实体和义务。希特勒、赫斯、戈培尔,斯特拉塞尔和党卫军的办公
室设在二楼。元首的办公室很宽敞,红棕色,相当漂亮。窗户通至天花板,俯瞰科尼希广场
。办公室内有一墨索里尼的半身大塑像,墙上挂着许多画,其中之一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
是元首所在的兵团首次进攻弗兰德时的情景。“希特勒不常在办公室”,弗兰克回忆说。他
的工作方法是毫无系统的。他可能“像一阵风似的进来”,但还没有坐下,“又像一阵风似
的出去了”。若被堵在办公室里,他会仓促地把事办完,然后便会“来上一小时的长篇大论
”。
他喜欢在楼下的小餐室的角落里消磨他的时间。那里有张“元首”台,上边挂着一幅狄
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厦”里坐办公室的生活对他是不适合
的。他的欲望是动,是为自己和为党取得人民的支持,或与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支持他的人们
进行高级谈话。1931年希特勒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艰巨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由于党的队
伍迅速扩大所致。党的发展,使党的官僚机构的每个部门也膨胀起来。其结果是,各部门互
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头痛的是党卫军,因为许多党卫军的成员对希特勒要守法之说不以为然。他们常将暴
力传统引为自豪,不明白为什么要对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贴耳。这些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许多
人心里想的是社会主义,与他们的共产党对手一样,具有革命热情——这正是使元首难堪的
。从一开始,他便与冲锋队的领导人意见不和;前者要把冲锋队变成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而
他却坚持己见,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群众集会,以及宣传政治忠诚。首先闹别扭的是罗
姆上尉。他因为与希特勒意见不和,自愿流放到南美去了;后来是普腓弗·萨洛门——他也
提出要加强冲锋队的要求,因得不到满足,不久也洗手不干了。
领导之间的不和使下边的士兵也产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党徒造反,理由是,他
们挨饿,工作负担过重,在与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殴斗中,常常受伤或被逮捕。他们不愿只为
党的集会站岗放哨,在他们的7条要求中,包括增加经费的合理要求,被戈培尔否决后,这
一支部队气得发疯,袭击了由冲锋队把守的地方党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后,叛乱才告平
息。在武装的冲锋队员陪同下,他视察了党卫军的各个开会据点,号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
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亲那样,又是恳求,又是许诺,又是斥责。他很少谈到褐衫党徒的7项
要求,只把它当作个人问题处理,号召人们忠诚于他。然后他便宣布,他自己是党卫军的总
指挥。这一宣布博得了党卫军的高声喝彩,同时也象征着这次短暂的叛乱业已结束,希特勒
可以回到竞选上去了。
他答应领导党卫军,但这却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承担这一职务
。时至1931年初,党卫军仍缺乏有效的领导。1月4日,党宣布,罗姆上尉(新近才从
玻利维亚召回,在那里,他曾协助共和国与巴拉圭作战)将出任党卫军的参谋长。由于希特
勒同意让罗姆在拥有6万名士兵的党卫军组织内部自由行事,他才答应返回德国。在同意暂
时将冲锋队只作为受纪律约束的游行部队后,这位能干的组织家和干练的领袖便着手按自己
的形象去重建党卫军。
然而,效能并不是解决积怨已久的组织的灵丹妙药。不久,首都便酝酿着另一次严重的
叛乱。柏林褐衫党徒的困苦境况基本依然如故。组织内部的不平等令他们的领导人瓦尔
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组织系统应以“知识”而不是“人事”为基础。他公
开抱怨说,希特勒“每隔几个月便改变主意,发布新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行动
。斯登尼斯的手下对此迷惑不解,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们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却又不可
抗拒地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冲锋队和党卫军停止在街头殴打赤色分子和犹太
人后,这个问题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们为何伤心和愤怒”,他对褐衫党徒说,“但你们
绝不可携带武器。”他们不满地嘟囔不休,却未采取行动,及至次月希特勒屈从于魏玛政府
的法令……该法令规定,未来的集会必须获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
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
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
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
不到24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
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
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
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4月4日,《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
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
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
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
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写道:“希特勒
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
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
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
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
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
—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
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
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
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
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
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动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
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
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其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
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
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
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
——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
替。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
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
:“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
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
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
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
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