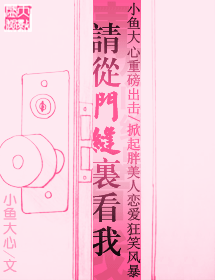请从门缝里看我-第9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虽然吃惊他突然间的邀请,但仍旧很认真地回道:“谢谢你的好意,但我并不想去。”
华骆忙转过身,问:“为什么?”
我用脚踢着桌角:“不喜欢那个地方而已。”
华骆微愣,随即眼睛一亮,分外真诚道:“那我们去法国巴黎吧。”
我心有所动,但骨子里似乎并不想离开这里,甚至觉得只要不出国,就不会断了某些联系。而这种联系,到底是谁与谁之间的联系,就无法清楚地指出了。
华骆见我不语,更加卖力地游说,最后竟独自定论说,只出去半年,去感受一下巴黎地艺术氛围,为创作找寻新的灵感。并由他联系一家知名的艺术大学,两人一同进修雕塑系。
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但我并不想拖欠华骆人情。我既还不起,也觉得累。
然而,华骆实在是太热情了。
他就仿佛是不容拒绝的前进机器,兴致匆匆地一锤定音,然后掏出手机就找人给为我们办理出国手续。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只能坚守着最后的底线,说:“所有费用我们AA制。”
华骆点头:“好,都听你的。”
我又说:“学校先不要定下来,等去了巴黎后,我们自己找找看。我语言不通,很有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看个热闹。再说,旅游签证的有效期不是只有三个月嘛?”
华骆说:“签证的事儿你放心,我来办就好。你好久都没有出去走走,是应该休息休息了。”
于是,这么一个比较重要地决定,就这么被拍板订钉了。
本来是很繁琐地巴黎一游,却因为有华氏集团做后盾,很快就被提到了日程上。
我特意与老馆长打好招呼,并郑重地感谢他对我的照顾。老馆长却愁眉不展,拉着我地手不肯放行。我问老馆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和我说。老馆长却并不承认,只是连声叹气,让我早点儿回来。我觉得老馆长话里有话,却追问不出究竟,只能作罢。
当我将一切工作都交代稳妥了后,却又开始犹豫,不晓得要怎么和十八说。我觉得这种犹豫很危险,就像是一种被埋藏在骨子里的牵绊,是由每个紧密地拥抱所换来的不舍。
心烦意乱中,我决定还是先给老妈和白婉挂个电话,将自己最新的动向报告一下,免得她们惦念。
我先给老妈挂得电话,告诉她我很好,要出国去转转,等回来后就回去看她。然后又跟白婉调侃着最近状况,让她不要为我担心,等回国后也去看她。
电话里,白婉说着自己的儿子有多么可爱,让我也赶快努力制造出一个宝贝儿,去和她家的两个小祖宗一起玩。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异常火热时,白婉突然没有了声音。
我疑惑地问:“喂,你怎么了?不是被你老公强行拖去行使夫妻义务了吧?”
半晌,白婉才试探着说道:“何必,银毛……回来了。”
我手一抖,电话差点儿掉落地上。原本很想警告白婉不许将我的任何信息告诉他,可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是自作多情了。曾经他可以不辞而别,就是没将我放在心口的位置上,我又何必自取其辱,将自己往死胡同里赶?
强装作镇定地笑了笑,用无所谓的调调说:“是吗。”
白婉轻叹一口气,问:“你不想问问他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透过玻璃窗仰视天空,笑道:“世界上总有太多的为什么,可惜我并不是一个好学之人。我宁愿躲在安全的缝隙里,做一只愚蠢的刺猬,也不想再跳出去遭遇大型动物的搏杀。
“再说,当初他离开的原因我知道,不就是什么狗屁继承权,什么出国深造,什么后妈与儿子的身份差吗?没劲儿,真得挺没劲儿的。你今天要是不和我提起他,我几乎都要忘记自己曾经认识过这么一号人物。”
白婉咋呼道:“何必,我也甭跟我装蒜,装作什么都不在乎。你要是心里还有气,咱姐妹就找人按住他,几脚踩爆他的小**,看他以后还能怎么猖狂!”
我颤抖着肩膀笑道:“你怎么当妈了还这么火爆?”
白婉嗤鼻道:“谁像你啊,一天到晚玩老成。你现在是要事业有事业,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要男人那更是一打打的,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没有以前欢实了呢?喂,不是我说你,你要是走冷感路线,最起码个头还得拔高一些。不然,就赶快给我撒欢儿地活着,继续彪悍可爱的风格。”
我心中感动,鼻子一酸,深深吸着气,努力平复道:“谢谢你。白婉,我会努力快乐的。”只是,已经不晓得快乐的定义了。
白婉吵嚷道:“好啦、好啦,不和你说了,我得防电话辐射。”
我点头:“好,你照顾好自己。”
白婉却突然大喝道:“何必!你赶快去买个电话。我要二十四小时随时能找到你!别去了巴黎就石沉大海了!”
我含糊地应道:“好啦。有电话时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像是从何然被山蛇精带走后。我就一直没有买过电话。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人赠送得电话。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只在固定地地方出现。却不会让人随时找到。
挂下电话后。我浅浅笑着。不让自己看起来慌张。不让自己为那个人地归来而躁动不安。既然已经成为了过去。何必纠结着不放呢?
还是将一切都放下。去巴黎转转吧。也许等我回来地时候。会发现十八也是值得相爱地那个人。打定注意后。我开始默默准备必备用品。也在静静等着十八地到来。
十八来得那天下起了小雨。整个世界都弥漫在一种伤感地调子中。让我想说出口地辞行变得有些暗哑和苦涩。
我拿起毛巾轻轻地将他身上地水渍擦干。动作温柔而用心。却始终不敢去看他地眼睛。
十八是个好情人,总会顾及我的感受。他不说也不问,只是低下头轻柔地吻着我。
我眼眶潮湿。踮起脚尖,努力回应着他的温柔。
衣服散落。发丝凌乱,十指相交。濡湿的吻,温热的唾液,沿着身体最敏感地位置游离,在轻吟与狂野间,让快感一**袭来。
直到两个人气喘吁吁累得无法继续,十八才将我抱入怀里,沙哑地问:“什么时候走?”
我知道他一定会看见我收拾起来的行李,却没想到他问得如此直接。心跳随着他沙哑地声音变得异常,仿佛在阵阵刺痛着,不仅信口道:“我……我不一定走。”
十八呵呵一笑,伸手捏了捏我的脸,说:“出去散散心也好。”
听十八如此轻松的语言,我才恍然觉得,我们只是床伴的关系,并非爱人,并非长相思守,做什么依依不舍?偷偷吸着气,扬起笑脸问:“十八,你想去巴黎转转吗?”
十八望着我,说:“我暂时走不开。”
我哦了一声,转开头,没有再问。
半晌,十八极轻地声音在头顶传来。他说:“你不问我为什么走不开?”
咋听十八此话,我突然想起了银毛。曾经他也问过我,为什么不问他为什么。我的理由一直很简单,若他想说,自然会说。若不想说,我问了,也只是为他徒增烦恼。
然而今天十八依旧如此问我,让我变得有些疑惑、有些心惊,不晓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抬眼望向十八,想从他脸上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十八伸手抚上我眼,轻声道:“何必,你不懂男人,所以别这么看我。你不懂一个男人的悸动,也不懂一个男人隐匿的伤口,更不懂……你这么看我,我会不想让你走。”
我的眼泪流出他的手指缝,就像血液的奔流,无法停止。
十八突然紧紧抱住我,在我地颈项间低吼道:“我不可以吗?不可以吗?!”
没有根由地话,但我却听得懂。
爱情是场角逐,不到最后关头就不知道鹿死谁手。然而,两只相互取暖的刺猬,是否可以在不伤害彼此地情况下相爱,真得是个未知数。
只是,我心疼十八,真得心疼。心疼他每个星期的往来,心疼他装作地不在乎,心疼他此刻的低吼,心疼他缠绵时地温柔。只不过,谁还敢轻言爱情?何其自私的我啊,始终不敢给予的,便是承诺。
也不知自己是抽得哪阵疯,在十八的拥抱中,我竟然放声大哭,就仿佛要哭尽所有的委屈那般用力。实则,我并不委屈,也不想哭,只是单纯地想要发泄一下情绪。
十八被我哭得有些发懵,只得哄道:“不哭了、不哭了,都成花脸猫了。”
我等自己哭够了,才哽咽着停了下来,抽搭道:“十八,我曾经很讨厌出国的人,但我现在要去巴黎,你会不会讨厌我?”
十八擦着我的眼泪,笑道:“不会,我会为你祝福。”
听十八这么说,我心里瞬间舒服多了。就仿佛是朋友之间的告别,而不是情人之间的分离。我瞧着十八,在心里寻思着,没准儿他也定位不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只是他众多床伴中的一个,比别人近些,却无关爱情。
十八是谁,一个游离花丛的红馆人物。他虽然有自己的感情,但却和我一样小心谨慎得不会轻易付出。即使爱了,也会掺杂几分防备,不会让自己完全沦陷。
我们太一样了,所以总没有进展,甚至缺少一种无畏的勇气。只能在不受伤的前提下,爱别人,更爱自己。
而我,唯一一次全然不顾自己的飞蛾扑火,竟是为了何然将自己卖给了冰棺材。没有犹豫,没有计较,甚至到现在,我都不承认那是脑袋一热的产物。尽管偶尔还是会埋怨自己干了件没有脑袋的事儿,但若时光倒退,我仍旧如此。
轻声抽搭着,钻进十八的怀里,用手挠了挠他的小果实,喃喃道:“我可能要在巴黎住半年之久,你照顾好自己。”
十八拉住我的手,放到唇边亲吻着:“但愿你回来后,能看见我的努力。”
我抬头。询问道:“你说有事情走不开,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十八眯起狭长地眼。笑道:“哦。终于问了。”
我脸一红。觉得自己这个弯绕得太过明显。伸手掐了下他精窄柔韧地腰肢。表示自己地发窘与不满。
十八闷哼一声。听在我耳朵里还真是充满诱惑力。
他笑睨着我。说:“小花猫。真够暴力地。”
我张开牙齿。作势咬他:“最近馋肉。想用牙齿逼供。你且速速招来!否则……嘿嘿……”
十八告饶道:“马上招。马上招。小人准备自己开家夜总会。正在筹备当中。”
我大喜:“真得?恭喜啊,十八老板。”
十八低头亲我一口,戏谑道:“要不要来当老板娘啊?”
我撇嘴:“我跳不了艳舞,撑不了场子。”
十八低低地笑着,不再说其他。
我打个哈气使自己看起来似乎要马上入睡,但实际上心里却为他地提议而开始思考。虽然我们开始的起点不好,让我很难相信彼此之间会有美好的结局。但在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中,十八的种种体贴仍旧在不知不觉间渗入到我的生活。在我地感情中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痕迹。而且。我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喜欢他的陪伴,喜欢枕着他地手臂入睡。喜欢闻着他胸口淡淡的香水味道。
窝在十八的怀里,我真得开始认真考虑。如果我从巴黎回来后,仍旧不陌生彼此的味道。去当老板娘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