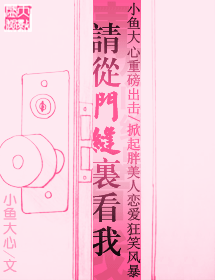请从门缝里看我-第1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的血可以这么多,多得仿佛要将我淹没溺毙!
我抬起手,闻着手指上何然鲜血的味道,想着他的样子。伸出濡湿的舌头,轻轻舔舐着手指上的血液,想要记住何然的味道,不想让感觉变得模糊。
玻璃窗中,银毛就站在我的身后。他穿着绣着银色图腾的黑色燕尾服,就倚靠在冰冷的墙面上看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咧着被鲜血染红的唇畔对他笑着。
他却突然暴怒,大步向我走来,一把扯下我的手指,将我狠狠地钳在双手中,大吼道:“你给我清醒点!”
我仰头,沙哑道:“我很清醒,只是在等待。”
银毛微愣,再次仔细地看向我,试图找出我哪里不太一样。
我轻轻依偎进他的怀中,尽显疲惫地说:“放心吧,我的心脏被你锻炼得足够强悍。”只是……经受不起一次次的自杀式碰撞。
银毛揉了揉我的头,缓缓放掉一口气,低头用下巴摩擦着我的鬓角,故意逗弄道:“刺猬,你如果想哭,就在我怀里哭,我保证不笑话你。
“
我摇头:“不哭。你做手术时我都没有哭。何然现在做手术,我也不哭,所以他也一定会活着出来骂我是混蛋。”
银毛点头:“好,我们等那小子出来,然后狠狠地踢他屁股!看看他为什么满身是血地跑来破坏我的婚礼。”
我重重点头:“好,踢他屁股。”
银毛用双手环住我的腰肢,形成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港湾。我依偎在他的怀中,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就好像一切有他,我就可以不用担心,只要放心地去依赖。
呼吸间,我喃喃道:“银毛,我发现我比以前脆弱了。”
银毛低沉而温柔地应了声:“嗯?”
我抬头,认真道:“你做手术时,我还可以硬撑着和冰棺材开玩笑。现在面对何然做手术时,我只觉得疲惫而紧张,想在你怀里睡一觉。然后等我醒来时,你就可以告诉我,他很好。”
银毛抱起我,坐到椅子上,用柔软的唇畔摩擦着我的额头,温柔道:“睡吧,那小子死不要脸的精神很强悍,不会这么轻易死的。”
我相信银毛,点了点头,安静地窝在了他的颈窝,嗅着属于他的味道,在满怀希望中闭上了疲惫的眼睛。并努力弯起了轻柔的唇角,为何然祈祷祝福。
半寐半醒中,我仿佛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梦里,火红的嫁衣,骑着雪白的高头大马,在沙漠中向着银毛的方向奔去。
银毛穿着黑色的晚礼服,就站在不远处望着我,既不向我靠近,也不闪身躲开。他好像对我笑着,但那笑容却非常模糊。我觉得有些害怕,怕他会突然转身离开,于是使劲拍打着身下的白马,想尽快赶到他的身边,看清楚他的脸,拥抱住他的身体。
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身下的白马就仿佛是在兜圈。以银毛为点,保持着永远的距离,一圈圈地奔跑着。
我急了,狠狠踢打着白马。
白马长鸣一声,突然回过头,望向我。红色的血液从它的七窍里流出,如同扭开的水龙头般向下哗哗流淌,与它白色的皮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得人触目惊心。
我吓得猛倒吸了一口凉气,惊恐地想要跳下马背跑开。
然而,那匹七孔流血的白马却在此时开口说话。那声音包含了怨念与不舍,愤恨与纠葛,恰巧就如同何然的声音一样!它说:“何必,看见我为你流得血了吗?”话音未落,白马的身上突然暴起无数血洞,向我喷射出滚烫而猩红的鲜血!
我非常害怕,既想要逃跑,又想捂住白马身上的血洞。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挣扎中,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仿佛都要崩溃了!我想求救,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在心里哭喊着不要!
就在这时,我感觉有人用力摇晃着我,大声唤着我的名。我大叫一声惊醒,终于从噩梦中摆脱了出来。胸口在大幅度地起伏着,就连身上的衣服也已经被汗水浸透。
银毛轻拍着我的脸,哄道:“没事儿了、没事儿了,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喘息着点头,却是急声问道:“怎么样了?何然怎么样了?”
银毛地眸子变得幽暗而深沉。仿佛是深不见底地古井。吸去了我所有地勇气。只剩下恐惧与战栗。
我疯了般想要冲进手术室。想要去看看何然最后地样子。想要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到底是想恨我一辈子。还是想惩罚我一辈子?!如果说。他想在我生命里雕刻下无法磨灭地痕迹。那么。他做到了。残忍地做到了!
银毛试图控制住我地身体。我却歇斯底里地失声大叫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去弄死他!我要一刀刀活剐了他!他不是人!不是人!他诅咒了我。不让我幸福!我要杀了他!杀了他!”我从心里无法相信何然已经死了。无论怎样。我都无法相信!
面对我地狂乱。银毛使劲一扯。将我紧紧地困入怀中。低吼道:“好了!好了!他没有死。没有死。你听见了没有?!”
我身体瞬间僵硬。抬头看向银毛。眼中闪烁着非常极端地光束。
银毛对我点了点头。认真沙哑道:“他没死。但……”
我心脏豁然一紧,手指甲也抠进了银毛的手腕上。
银毛望进我的眼底,缓声道:“他的腿骨和脊椎严重受损,下半身暂时失去了知觉,能恢复的几率只有一半。”
银毛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见去,当即如同无头苍蝇般四处寻找着何然。
银毛叹息,用大手握紧我的小手,领着我走向特殊观察室的病房,看见了那个躺在医疗器械中的何然。他苍白得仿佛是一片洁白的花瓣,很轻,很轻……
……
……
等待一个人醒来需要怎样的心情?
我相信,这世界上最磨练人耐性的事儿,便是等待。至于等待中的心情,则寄托在患得患失间,需要用强大的意志力来鼓励自己
心怀希望的等下去。所以,我要说,能禁得起等待都是坚强的人。
我这么说并非想要标榜自己的坚强,但在经历过一系列的事情后,我无法做到不坚强。
当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落到何然身上,他依旧如同最纯洁的婴儿般熟睡着,不曾睁开眼睛,不曾开口埋怨,也不曾自怨自怜,或者找借口欺骗。
我虽然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但并不觉得匮乏,就仿佛是一个飞贼,眼巴巴守望着即将盛开的雪莲宝贝,想在第一时间得到那绝世无双的精华。
是的,我希望何然张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那个人……是我。
我相信,也只有我,才可以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他暂时不能走路的事实。至于这个暂时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来计算,我想会很快。只因为,我有信心!
想着要对何然说得好,我一遍遍在心里默念,并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我要让何然和我一样有信心!
望着何然的睡颜,用手轻轻抚摸着他苍白的脸颊。他的头发已经被光,额头上缝合着一道狰狞的伤口。这道伤口很深,也许会在数月中张合,也许会留下痕迹。但这些都不重要,我只希望他能忘记曾经的不愉快,仍旧可以对我撒娇,口口声声唤着我的名,说我是个混蛋。然而,不要再爱我。我相信只有这样,他才会快乐。
爱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真得是半面天使,半面恶魔,就像何然一样。
我相信人的一生里,会有很多种情感。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等,但又绝对不止这些。虽然我无法总结自己对何然的感情,但我相信,这种感情是存在的。也许因为这种感情的特殊,所以它总会被人硬性地归纳到爱情或者亲情里,从而忽视了这种感情本身的弥足珍贵。尽管我无法准确地叫出这种感情的名字,但我知道,它是如此鲜活地存在,就存活在我的心口,历久而弥新。
伸出食指,沿着他的眉眼勾画过他的鼻梁,最后来到那苍白的唇畔上轻轻地摩擦着。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却不想让它掉落到何然的身上。我望着他,轻颤着声音呢喃道:“死小子,你到底要怎样?真想让我陪葬你的爱情吗?”
何然不语,只是睫毛微微颤抖。
我以为他要醒来,小心得连呼吸都统统收起。然而,长长的等待中他仍旧沉睡着,不顾我遍遍期盼着的心情。颓败地笑了笑,喃喃道:“多睡睡也好,这样就不会感觉到痛了。”
轻轻的呼吸间,我望着何然柔美的面孔失神,视线渐渐模糊,终是趴在他的身边睡去。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拉扯我的耳垂。那冰凉的触觉就仿佛是一声声的呼喊,也似情人间暧昧地把玩儿。
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从带着消毒水味道的被褥中抬起头,迎着被拉扯耳朵的方向,望向了近乎透明的何然。
当我饱含感情的目光和他清澈见底的眸子相撞,我全身的毛孔似乎都在叫嚣,想要将他狠狠地抱入怀中,用痛来确定这份真实!
然而,我必须忍下这份念头,只能轻轻地靠近,缓缓地勾起唇角,生怕一个大力呼吸惊扰了他的神经,让他惶恐不安地消失在我的世界。
何然望着我,眼波柔柔亮亮,也缓缓扬起了唇角,用沙哑着嗓子说得第一句却是:“何必,你穿婚纱的样子真丑。”
低头看向自己那一身染了干涸血液的婚纱,确实邋遢T'子,于是笑了笑,说:“确实很丑,不过没有你的光头丑。”
何然费力地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确定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时轻轻闭上了眼睛。
我心中一紧,忙攥住他冰凉的手指,语无伦次地说:“不丑、不丑,我的何然最好看!”
何然的眼睛没有睁开,却有一滴清泪沿着微微颤抖的睫毛滑落。
我慌了,六神无主,更不晓得要如何告诉他,他的腿……暂时无法行走。对,只是暂时无法行走!
病房里,死一般沉寂着,没有人开口说话,但两个人相握的手指却在微微地颤抖着,分不清到底是谁的恐慌传染给了谁。
我心痛何然此刻的沉默,费力地将口水咽下红肿发炎的喉咙,想着要将话题引向轻松的方向。
然而,就在这时,何然睁开了眼睛,用那双微微颤抖的眸子望向我,伪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道:“何必,是麻药没过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腿痛?”
我的手指豁然收紧,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语言匮乏,竟然如鲠在喉,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何然的问话。
何然望着我,眼底渐渐变得不同,仿佛是一块纯净之地慢慢被痛苦席卷覆盖,失去了原有的清透色彩。
他的手指在我的手中慢慢抽回,就仿佛要退出鲜活的生命。
我一把拉住他冰凉地手指。紧紧攥住。鼓足力气。瞪大双眼。大声吼道:“逃什么?!只不过暂时无法行走。终有一天会重新站起来!”
何然被我吼住。不再退缩。却是面如单薄地白纸。仿佛要在顷刻间变成纸屑。何然没有闹。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痛哭流涕。更没有瑟缩不安。他就如同一个漂亮地木偶。轻轻闭上眼睛。静静躺着。
我曾想过很多种他醒来后地样子。却独独忽略了他地沉默。然而这种无言沉默却让我打心眼儿里变得毛躁不安。不知道要从何下手开导他。
病房里再次陷入死一般地寂静。就连空气都仿佛被蒸发掉了。